|
清明七日行
三之一▲西湖懷古

接受了浙江大學的邀請,在清明節前六天由高雄直飛杭州,開始一周的訪問。聯絡人是浙大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的江弱水教授。早在八○年代末期,弱水就以卞之琳先生弟子的身分和我通信,後來我又參加過他的博士論文評審。他寫詩,也嫻於詩學
,有《古典詩的現代性》與《中西同步與位移》兩書,可以印證其博涉與圓覽。非但如此,他的小品文也寫得風趣生動。去年五月他來台學術訪問兩月,事後出版了隨筆集《陸客台灣》,對此行所見的世情與人物,正敘側寫,均有可觀。
浙江大學的邀請,我很快就接受了,原因是多重的。首先,聯絡人是弱水,此行一定會妥善安排,他的品味我當然放心。其次,我上回去杭州,是在2004年五月,先在同濟和復旦兩校演講,然後由喻大翔教授陪我們夫妻去遊杭州,那頭也由弱水接待
。不過比這一切更早的,是小時候住在南京,就曾隨父母來過這風雅的錢塘古都。那時我究竟幾歲,已不記得,倒是後來常聽父母提起;總之這件事久成我孺慕的一幕。
但是我去杭州,另有一個動機,就是成全吾妻我存的尋根之旅。我存的父親范賚先生,也就是我從未見面的岳父,在抗日戰爭爆發的第三年春天,因肺疾歿於四川的樂山。時為1939年3月28日,他才三十九歲,留下哀傷而無助的三個女人,我存的外婆、母親與八歲的我存,去面對不知該如何應變的國破家亡。後來的情形,只有在我存和她母親的零星回憶和當年僅存的一本相簿裡去拼湊梗概:她的父親籍貫江蘇武進,南京東南大學畢業,留學法國,回國後在浙大任教,抗戰初期帶家人一路逃難去大後方,終因肺病惡化而滯於樂山。
1996年十一月,我去四川大學訪問,事後與我存專程南下樂山,憑著當年葬後留下的兩張地圖,想去按圖索墓。畢竟事隔半個多世紀了,「再回頭已百年身」,物是人非麼,不但人非,抑且物非了,瞻峨門外,大渡河邊,整座胡家山上早已變得滄桑難認,哪裡找得到那個孤墳?
但是回過頭來,浙江大學幸而猶在,不但猶在,而且校譽更隆,全國排名,長在前列。趁我前去訪問,一定會發現可貴的資料,可助拼圖。此意向弱水提出,他說那是當然。
3月30日的黃昏,弱水在蕭山機場接機,把我們安置在西湖北山路的「新新飯店」。七年前我們也是下榻這裡,但這回住的卻是別館的「秋水山莊」,即三十年代著名報人史量才為愛妻沈秋水所築的別墅。夜色蒼茫,寬大的陽台上只見隔水的長堤
,柳影不絕,燈光如練。我們果然置身杭州了。
次晨弱水和他的太太楊嶺來帶我們去遊湖。這才發現,昨夜所見的柳堤原來是白堤,而所隔的煙水只是北裡湖,還不是西湖的主湖。四人沿著北山路東行,弱水背湖仰面,為我們指點山上矗立的保俶塔。終於去到白堤東端的斷橋殘雪,弱水說,相傳《白蛇傳》中許仙就是在這裡邂逅了白娘子。橋上有一木亭,匾書「雲水光中」,十多年前簡錦松遊湖,見題詞含有我名,曾攝影相贈。那天遊客不少,更多晨運的市民
,就在亭前相擁起舞,一片太平盛世氣象。不知當年父母帶我來遊,是否也這般旖旎風光。杭州人得天獨厚,傳統特長,一道堤上有多少故事,一聲櫓裡有多少興亡,真令我不勝豔羨。去夏我和家人遊佛羅倫斯,也不勝低迴,但是杭州的風流儒雅,似乎更令我神往。蘇堤與白堤,岳墓與秋瑾墓,靈隱寺與香積寺,雷峰塔與六和塔,這一切牽人心腸的地標,甚至是引人夢遊的座標,又何遜於佛羅倫斯與威尼斯?
正是春分已過,清明待來,柳曳翠煙,桃綻絳霞,令人不由想起袁宏道讚嘆的「斷橋至蘇公堤一帶,綠煙紅霧,瀰漫二十餘里;歌吹為風,粉汗如雨,羅紈之盛,多於堤畔之草,豔冶極矣!」那天春晴料峭,日色淡薄,白堤上遊人雖多,卻無什麼歌吹,近午時倒是令人有些出汗。天上不時可見老鷹盤旋,遊人卻不怎麼在意,後來越飛越低,才發現是有人在堤上收線,原來竟是風箏。於是彩蝶翩翩,也會降落到女孩子手上來,我也接到一隻,只有巴掌大小,竟能曼舞湖上的風雲。弱水說這季節西湖的風勢正好放風箏,否則不可能這樣收放自如。
弱水又說:「走累了吧,不如上船。」四人便上了一條白帆布棚遮頂的遊船,相對而坐,遊起湖來。船夫興致很好,帶有本地鄉音的普通話也斯文親切。記得他只是撐篙,並不搖槳,過了張岱的湖心亭,過了詩心禪意的三潭印月,把我們放在小瀛洲滸。小船再來接渡,就把我們撐回堤上去了。
這就是我三月底的杭州之行:西湖之緣雖得以續,也只能淺嘗即止,步堤倚舷,不滿一天。湖上風平浪靜,岸上歲月悠悠,我的深心卻不得安寧。那麼長遠的記憶啊
,民族的,家族的,童年的,悲壯的,倜儻的,纏綿的,方寸的此心怎麼容得下理得清呢?湖邊一宿,別說杭州通判的「水光瀲灩晴方好」了,就鑑湖女俠的一句「秋風秋雨愁煞人」,都令我客枕難安。
當天晚上,我在浙大紫金港校區的蒙民偉國際會議中心演講,題目是「美感經驗之互通──靈感從何而來」。我用不少投影來印證,講了一個多小時。開場白就以我與杭州和浙大的因緣切入,說明小時候就隨父母來過此城,又說不但杭州是我存的出生地,而且浙大是我岳父任教的學府。六百多師生報以熱烈掌聲。由於聽眾太擠,向隅的百多位只能另闢一室以螢幕聽取。所以我事先還特別去另室致意一番。
我的講座是以「東方論壇」的名義舉行,並由羅衛東副校長主持,胡志毅教授介紹。講前有一簡短儀式,把客座教授的聘書頒贈給我。這麼一來,我不是有幸成為岳父范賚教授的同仁了嗎?
更高興的,是浙大事先已蒐到有關我岳父的資料,也在那場合一併相贈。我存的尋根之旅遂不虛此行了。根據那些信史,我岳父短暫的一生乃有了這樣的輪廓:
范賚,字肖岩,江蘇武進人,1900年出生。東南大學畢業,留學法國,卒業於巴黎大學理科植物系。1928年起任教於浙江大學,為農學院園藝副教授,每月薪資由160大洋調整為240大洋。1929年至1931年曾代園藝系主任。長女我存1931年生於杭州刀茅巷。當時浙大的農藝場、園藝場、林場、植物園等占地多達七千多畝。范教授帶學生臨場生物實習,曾遠至舟山群島東北端的小島嵊山。
三之二▲皖南問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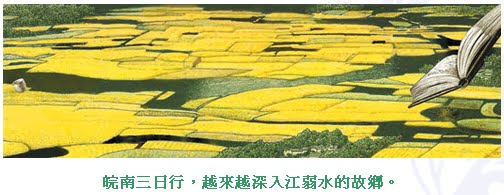
九華後山青黛連綿的陣式,倚老兼而倚天,莊重得令人起敬,
但是山麓的平疇上,一望無邊,黃豔豔令人目眩……
皖南三日行,越來越深入江弱水的故鄉。他是青陽人,對皖南一帶的地理、人文十分熟悉,一路為我們指點名勝古蹟,並佐以歷史的背景,涉及朱元璋與太平天國的種種尤其生動。他對古典詩詞的記性不下於李元洛,歷數皖南滄桑之際,更常引詩為證,真是難得的導遊。
4 月4日,我們駛入了青陽縣朱備鄉的龍口小村,到了一條清溪的橋邊。弱水請晨虎停下車來,並逕自按下車窗,向臨街店鋪叫了一聲「表嫂」。我只道皖南民風淳厚,招呼親切。那婦人教我們把車開到西邊的院子裡,不久就來我們圍坐的白石圓桌
,擺滿花生瓜子之類,泡上今春第一杯明前茶,態度之親切自然,儼若家人。原來她真是弱水的表嫂!我們鬆了一口氣,就在樹下悠悠享受茶點,一面聆聽小溪的急湍清流潺潺漱石而去。
我們再度上路,轉晴的陽光在九華山下的平原上迎接我們。昨天下午,參加池州杏花村詩會的各地詩人,在九華山中困於陰濕的雨霧,更苦於腳下的滑泥,對於黃山之行實在難寄厚望。此時的九華山——不,我們已轉到了九華後山——在轉晴的遠景之中,巨幅的石壁半露筋骨,半掩在蒼鬱的林木之下,筆墨豐沛,令人想到黃賓虹蓬勃的畫面。九華後山青黛連綿的陣式,倚老兼而倚天,莊重得令人起敬,但是山麓的平疇上,一望無邊,黃豔豔令人目眩,一排排密密麻麻的隊伍,黃旌黃旗擎得那麼整齊的,卻是生氣鮮活的油菜花田。對比之下,很像肅容端坐的老輩膝下,嬉戲著,囂鬧著那麼一大群孩童。
弱水領著我們越陌度阡,步入菜花深處,近前嗅時,一片花香襲人如潮,飽飫肺腑。我存和我不禁懷念四川田疇的土埂,縱橫交錯,蜂忙蝶亂的情景。九華山迤邐青陽縣境,弱水引我們深入這一片魔幻的花香,等於不落言詮地帶我們探入他童年的夢境。細圓柱形的綠莖,像精靈世界的廊柱,把盛開四瓣的黃花托到高齊人胸,滿田的活力與生機,把春天鬧得不可收拾,誰說皖南就不是江南呢?至少施閏章、黃賓虹、胡適之,一定不會甘心吧。
花已如此,人豈不然。皖南的三日車程,這樣的油菜花田不斷拍人臉頰,令我們左顧右盼,簡直應接不暇,更想起當年自己做村童的時候,也曾經坐擁一畝畝的黃金
,富可敵城。那天正是清明節前一日,繽紛的春色倒也不讓菜花獨占。嫣然羞赧的桃花,白得患潔癖的玉蘭,纓絡成串的櫻枝,加上山茶、迎春和海棠,而只要近水,更嫋娜著翠霧一般的倩柳。童年的記憶在都市的塵灰中久已失色,那幾天竟又甦醒了過來。
車過九子岩景區大門,我們停下來稍息。弱水正為大家指點風物,忽見簷影燕尾之下,襯著九華山披麻皴法的遠景,有一塊米色整石,長近三丈,像剖成一半的不規則橢圓,覆蓋在青草場上。石上坐著幾個女孩,約莫十三、四歲,正在談笑。後來又有一個女孩,似乎更小,卻領著一個四、五歲的小童爬上石頂。我們覺得有趣,便向巨石走去。這才看清原先的四個女孩一律短髮垂頸,額前全留著瀏海,半蔽的臉蛋都圓渾飽滿,兩頰紅潤,眼神靈活。顯然都是住在附近的中學生,在星期天的下午,泡在一起,懶懶地享受著彼此的活力和稚氣。弱水和她們搭訕起來,又問她們讀幾年級
,原來都是「朱備中學」的初中學生。
這些逍遙的村姑,問答之間毫不矜持,也略無羞怯。弱水終於問她們,課本上有未讀過〈鄉愁〉?回答是有。弱水指著我說:「作者就在這裡。」她們笑得有點不信
。弱水說:「不信,你們就下來合照張相,去問老師好了。」她們果然動搖了,一起溜下石坡,來跟我們合影。
我們重新上路,我卻十分感動。真羨慕這些無憂的孩子,後有九華巍巍的靠山,前有春色無際的油菜花田,功課壓力顯然還輕,青春的活力一時還揮霍不盡,夢的翅膀還沒有長齊,鄉愁更無從說起。弱水告訴我,這一帶曾經是朱元璋大將常遇春備兵之地,後來又跑過長毛,躲過日寇。但目前皖南這一帶,包括宣州、池州、徽州等地
,顯然都安寧而且小康:九子岩那幾個女孩的一幕,給我的保證勝過整本宣傳的小冊子。
滄桑感當然還是有的。抵達杭州的次晨,弱水和他的太太楊嶺帶我們遊西湖,只說他們是長干同里。之後在皖南的三日車程,他倒是講了不少故鄉的事。在龍口見過了他的表親,終於在一泓清冽的湖邊停車,他介紹該地叫牛橋,令人不禁聯想到牛津
、劍橋。接著他若有所思,說當年他就是在這水底和未來的妻子相會。怕我們不解,他又說這一帶原是山坳間的村墟田疇,後來築湖,便落到波下去了。這真是寫詩的好題目,也可見所謂鄉愁不全來自地理,也是歲月的滄桑造成。
皖南三日,活動很多,難以細說。池州的詩會上見到不少大陸的詩人,見到舒婷和陳仲義尤其高興。媒體訪問,總愛問我以前去過安徽沒有。我差點要說沒有,卻記起了一件事情,證明和安徽還是有緣的。那是1946
年仲夏,抗戰勝利次年,我才十八歲,和母親搭了一艘小火輪,從重慶順流東下,出三峽,泊武漢,回南京的途中,也曾在安慶上岸。後來在〈塔〉一文中,我如此追敘:「艤泊安慶,母子同登佛寺的高塔,俯視江面的密檣和城中的萬戶灰甍。塔高風烈。迷濛的空間暈眩的空間在腳下下,令他感覺塔尖晃動如巨桅,而他只是一隻鷹,一展翅一切雲都讓路。」
我告訴記者,那佛寺正是迎江寺,而塔,正是振風塔。
三之三▲黃山詫異

索道有如天梯,再陡的斜坡也可以凌空而起,全無阻礙,再高傲的峰頭也會為我們轉過頭來,再孤絕的絕頂也可以親近……
徐霞客,華山夏水的第一知音,造化大觀的頭號密探,早就嘆道:「薄海內外無如徽之黃山,登黃山天下無山,觀止矣!」他是最有資格講這句絕話的,因為千岩萬壑,寒暑不阻,他是一步步親身丈量過來的,有時困於天時或地勢,甚至是一踵踵、一趾趾,踉踉蹌蹌,顛顛躓躓,跼躅探險而跋涉過來的。
黃山不但魁偉雄奇,而且繁富多變,前海深藏,後海瘦削,三十六峰之盛,不要說遍登了,就算大致周覽而不錯認,恐怕也不可能。既然如此,淺遊者或為省時間,或限於體力而選擇索道的捷徑,也就情有可原了。何況索道有如天梯,再陡的斜坡也可以凌空而起,全無阻礙,再高傲的峰頭也會為我們轉過頭來,再孤絕的絕頂也可以親近,不但讓我們左顧右盼,驚喜不斷,而且憑虛御風,有羽化登仙的快意。騎鶴上揚州,有這麼平穩流暢嗎?古人遊仙詩的幻境也不過如此了吧?
一切旅程,愈便捷的所見愈少。親身拾級而上迂迴而下的步行,體會當然最多也最深,正是巡禮膜拜最「踏實」的方式。所以清明節前一天,我們終於進入黃山風景區的後門,亦即所謂「西海」景區丹霞峰下。此地的海是指雲海,正是黃山動態的一大特色。我們夫妻二人,浙大江弱水教授,弱水的朋友楊晨虎先生(此行全靠他親駕自用的轎車),都是黃山管委會的客人,由程亞星女士陪同遊山。
車停山下,我們在太平索道站上了纜車,坐滿人後,車升景移,遠近的峰巒依次向我們扭轉過來,連天外的遠峰,本來不屑理會我們的,竟也競相來迎,從俯視到平視,終於落到腳底去了。萬山的秩序,尊卑的地位,竟繞著渺小的我們重新調整。靠著纜索的牽引,我們變成了鳥或仙,用天眼下覷人寰。李白靠靈感召致的,我們靠力學辦到了。
三點七公里的天梯,十分鐘後就到丹霞站了。再下車時,氣候變了,空氣清暢而冷冽,驟降了十度。這才發現山上來了許多遊客。午餐後我們住進了排雲樓賓館,準備多休息一會,在太陽西下時才去行山,也許能一賞晚霞。
山深峰峻,松影蟠蟠,天當然暗得較快。迎光的一面,山色猶歷歷映頰。背光的一面,山和樹都失色了。真像杜甫所言:「陰陽割昏曉」。折騰了一天,又山行了一兩里路,是有些累了。回到排雲樓,剛才喧嚷的旅客,不在山上過夜的,終於紛紛散去,把偌大一整列空山留給了我們。我們繼承了茫茫九州最莊嚴的遺產,哪怕只是一夜。「空山松子落」,靜態中至小的動態,反而更添靜趣、禪趣。
真像歌德所言:「在一切的絕頂。」萬籟俱寂,只有我的脈搏,不甘吾生之須臾
,還兀自在跳著。那麼,河漢永恆的脈搏,不也在跳著麼?不逝者如斯乎,不舍晝夜
。我悄悄起床,輕輕推門,避開路燈,舉頭一看,原來九霄無際的星斗,眾目睽睽,眼神灼灼,也正在向我聚焦俯視。猝不及防,驟然與造化打一個照面,能算是天人合一麼,我怎麼承受得起,除了深深吸一口大氣。太清、太虛仍然是透明的,礙眼的只是塵世的濁氣。此福不甘獨享,回房把我存叫起來讀夜。
第二天四人起個大早,在程亞星的引導之下,準備把黃山,至少是後海的一隅半角,瞻仰個夠。程亞星在黃山風景區管委會已經任職十七年,她的丈夫更是屢為黃山造像的攝影家。有她在一旁指點說明,我們(不包括弱水)對黃山的見識才能夠免於過分膚淺。她把自己在1999年出版的一本文集《黃山情韻》送了給我:事後我不斷翻閱,得益頗多。
導遊黃山的任何小冊子,都必會告訴遊客,此中有四絕:奇松、怪石、雲海、溫泉。此行在山中未睹雲海,也未訪溫泉,所見者只有黃山之靜。儘管如此,所見也十分有限,但另一方面印象又十分深刻,不忍不記。
語云:看山忌平。不過如果山太不平,太不平凡了,卻又難盡其妙。世上許多名山勝景,往往都在看台上設置銅牌,用箭頭來標示景點的方向與距離,有時更附設可以調整的望遠鏡。在黃山上卻未見這些:也許是不便,但更是優點。因為名峰已多達七十二座了,備圖識山,將不勝其煩,設置太多,更會妨礙自然景色。黃山廣達
154平方公里,山徑長70公里,石階有六萬多級,管理處的原則是儘量維持原貌,不讓人工干擾神功。我去過英國西北部的湖區,也是如此。
黃山之富,僅其靜態已難盡述,至於風起雲湧,雪落冰封,就更變化萬殊。就算只看靜態,也要嘆為觀止。黃山的千岩萬壑,雖然博大,卻是立體的雕刻,用的是億年的風霜冰雪,而非平面的壁畫,一覽可全。陡徑攀登,不敢分心看山,就算站穩了看,也不能只是左顧右盼,還得瞻前顧後,甚至上下求索,到了盪胸決眥的地步。那麼鬼斧神工的一件件超巨雕刻,怎能只求一面之緣呢?可是要繞行以觀,卻全無可能
:真是人不如鳥,甚至不如猿猴。所以啊爾等凡人,最多不過是矮子看戲,而且是站在後排,當然難窺項背,更不容見識真面目了。所以連嶂疊嶺,岩上加岩,有的久仰大名,更多的是不識、初識,就算都交給相機去備忘,也還是理不出什麼頭緒。山已如此,更別提松了。
我存拍了許多照片,但是很難對出山名來。這許多石中貴冑,地質世家,又像兄弟,又像表親,將信將疑,實在難分。可以確定的,是從排雲樓沿著丹霞峰腰向西去到排雲亭,面對所謂「夢幻景區」,就可縱覽仙人曬靴與飛來石。前者像一隻倒立的方頭短靴,放在一方方淡赭相疊的積木上,任午日久曬。後者狀似瘦削的碑石,比薩斜塔般危傾在懸崖之上,但是從光明頂西眺,卻變形為一隻仙桃。此石高12米,重365噸,傳說女媧煉石補天,這是剩下的兩塊之一。它和基座的接觸,僅似以趾點地
,疑是天外飛來,但是主客的質地卻又一致,所以存疑迄今。
從排雲樓沿陡坡南下,再拾級攀向東北,始信峰嵯峨的青蒼就赫然天際了,但可望而不可即,要跟土地公的引力抗拒好一陣,才走近一座像方尖塔而不規則的獨立危岩。可驚的是就在塔尖上,無憑無據地竟長出一株古松來。黃山上蟠蜿的無數勁松,一般都是幹短頂齊,虯枝橫出,但這株塔頂奇松卻枝柯聳舉,獨據一峰。於是就名為夢筆生花。弱水免不了要我遙遙和它合影,我也就拔出胸口的筆作出和它相應的姿勢
,令弱水、晨虎、亞星都笑了。
到了始信峰,石筍矼和十八羅漢朝南海的簇簇鋒芒,就都在望中了。所謂十八羅漢,也只是約數,不必落實指認,其中有的危岩瘦削得如針如刺,尤其襯著晴空,輪廓之奇詭簡直無理可喻。上了黃山,我的心理十分矛盾。一面是神仙吐納的空氣,芬多精的負離子是城市十多倍,松谷景區負離子之濃,可達每立方公分五萬到七萬個,簡直要令凡人脫胎換骨。加上山靜如太古,更令人完全放鬆,放心。但另一方面,超凡入聖,得來何等不易,四周正有那麼多奇松、怪石等你去恣賞,怎麼能夠老僧入定
,不及時去巡禮膜拜呢?
奇松與怪石相依,構成黃山的靜態。石而無松,就失之單調無趣。松而無石,就失去依靠。黃山之松,學名就稱「黃山松」,為狀枝幹粗韌,葉色濃綠,樹冠扁平,松針短硬。黃山多松,因為松根意志堅強,得寸進尺,能與頑石爭地。原來黃山的花崗石中含鉀,雷雨過後空中的氮氣變成了氮鹽,能被岩層和泥土吸收,進而滲入松根
,松根不斷分泌出有機酸,能溶解岩石,更能分解岩中的礦物與鹽分,為己所用。因此黃山松之根,當地人叫作「水風鑽」,為了它像穿山甲一樣,能尋隙攻堅,相剋相生,把頑石化敵為友。所以800米以上的絕壁陡坡,到處都迸出了松樹,有的昂然挺立,有的迴旋生姿,有的枝柯橫出,有的匍匐而進,有的貼壁求存,更有的自崖縫中水平抽長,與削壁互成垂直,像一面綠旗。
這一切怪石磊磊,奇松盤盤,古來的文人高士,參拜之餘,不知寫了多少驚詫的詩篇,據說是超過了兩萬首,那就已將近全唐詩的半數了。我也是一位石奴松癡,每次遇見了超凡的石狀松姿,都不免要恣意瞻仰,所以一入黃山就逸興高舉,徘徊難去
。尤其是古松槎枒糾虯,就像風霜造就的書法,更令人觀之不足。下面且就此行有緣一認的,略加記述。
鳳凰松主幹徑30公分,高齡200載,有四股平整枝枒,狀如鳳凰展翅,十分祥瑞,其位置正當黃山的圓心,近於天海的海心亭。黑虎松正對著夢筆生花,雄踞在去始信峰的半途,望之黛綠成陰,虎威懾人,據說壽高已450歲。連理松一根雙幹,幾乎是平行共上,相對發枝,翠蓋綢繆,宛如交臂共傘的情侶;弱水為我們攝了好幾張
。豎琴松的主幹彎腰下探,枝柯斜曳俯伸,似乎等仙人或高士去撥弄,奏出滿山低調的松濤。
送客松和迎客松在玉屏峰下,遙相對望,成了遊客爭攝的雙焦點。送客松側伸一枝,狀如揮別遠客的背影。迎客松立於玉屏樓南,東望崢崢的天都,位據前海通後海的要衝,簡直像代表黃山之靈的一尊知客僧。他的身世歷劫成謎,據說本尊早被風雪壓毀,枝已不全,今日殘存的古樹高約十米,胸徑64公分,從1983年起派了專人守護。第十位守樹人謝宏衛自1994年任職迄今,就住在此樹附近的陋屋之中,每天都得細察枝枒、樹皮、松針的狀況,並注意有無病蟲為害。嚴冬時期他更得及時掃雪敲冰
,解其重負。他曾經一連四、五年沒回家過年:松而有知,恐怕要向他的家人道歉了
。此樹名滿華夏,幾已神化。程亞星告訴我們:1981年有挑夫歇於其下,一時興起,在樹身去皮刻字,因此坐牢。
黃山之松,成名者少而無名者多,有名者多在道旁,無名者鬱鬱蒼蒼,或遠在遙峰,可望而不可即,或高據絕頂,拒人於險峻之上,總之,無論你如何博覽遍尋,都只能自恨此身非仙,不能乘雲逐一拜訪。松之為樹實在值得一拜:松針簇天,松果滿地,松香若有若無,松濤隱隱在耳,而最能滿足觀松癖者的美感的,仍是松幹發為松枝的蟠蜿之勢,迴旋之姿,加上松針的蒼翠成蔭,簡直是墨瀋淋漓的大手筆書法,令人目隨筆轉,氣走胸臆。
2011.0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