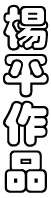
|
再從顧彬的一席話談起
今早意外在聯合報上(A13兩岸版),看到此一頭條報導: 「顧彬北京放炮:「沒有當代詩歌•••僅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 而標題更赫然印著斗大的字眼:「德國漢學家:中國作家被稱為 嫖客」,果然再一次的令人側目。
但若細看內文方知,斗大的字眼出自一位中國大學生的口中,顧彬的 反應則是「十分難過」,還說:「作家被形容為嫖客,這是多麼可怕啊!」 完全與標題相左。 可見儘管像「聯合報」這樣有水準的大報,也不免隨著時尚以聳動為 能事,實在可歎!
顧彬此次在北京「踢館」,應邀參加「世界漢學大會」,並在一場「漢學 視野下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除了再次質疑當代中國文學的價值, 更「不畏眾多大陸學者、作家的環伺,勇敢回應『當代中國文學都是 垃圾』的話題」,其場面的熱烈是可以想見的。
有趣的是,就一位對大陸當代詩歌曾說過「其中有一些了不起的作家」 的學者而言,這次根本否認了:「他認為中國沒有當代詩歌,也沒有 好的話劇,」「所謂的當代詩歌,僅是外國文學的一部分。」這對研究 漢學、以此為志職的他而言,「工作壓力也特別大」。 這些話聽來,有點像得了便宜還賣乖,令人不快;若靜下心自省,像 大學教授定期要交論文,可以體會箇中壓力;有心的我輩可以一笑, 也可以視為「諍友」的善意挑戰!
除此,他還很直接尖銳的表達了很多個人看法。 就報導的內文標題順序來說,如「經常」有人問他金庸是否「二十世紀 中國最好的小說家?」 他的回題雖然粗魯:「胡說八道,他根本不是,」基本上反映了問的人 有問題。
當然,以他對「當代中國文學」的看法,答案很可能是「二十世紀中國 文學沒有偉大的小說家」,若有,也只有他曾稱許過的魯迅還不錯,但 就算是「中國最好的小說家」,可能也夠不上「偉大」。
當年,俄文豪高爾基來訪,如同徐志摩是泰戈爾的翻譯,魯迅是他的 翻譯;兩人在散步時,高爾基問這位一向以言詞辛辣稱著的思想型作家 :「人們說你是中國高爾基,你覺得你是嗎?」 魯迅聞言,一身是汗。答案可想而知。 幸運的是,由於魯迅死在四九前,被後來的毛澤東大大稱譽,享有 「文藝之神」的稱號。
再說一個我親身體會的例子。 八九年春,我有緣會見了冰心、錢鍾書、艾青等一些尚在世的名家; 當時,年高望重的艾青是中共國家級桂冠詩人;在我與他相談的二三十 分鐘裡,至少有三四次提到了聶魯達,並像胡適那樣的說,我與「我的 朋友聶魯達」如何如何--這固然可視為他懷念老友,也不免(讓現場 的我)感覺怪怪的:你若是大師,又何必「挾洋」自重呢?
這兩個例子,似乎說明了,就算五四後,四九前,中國出現的世界級 人物雖多(先父在其回憶錄裡就曾提到,他當時唸的「北大哲學系」, 就有十位國際聞名的學者),「文學」(正確說法該是「新文學」)方面, 也有魯迅、沈從文、周作人、張愛玲、林語堂•••等等,或聞名國際或有相當 成就的優秀作家,卻沒有一位在世界文壇稱得上「大師」。
若我們同意這是不爭的事實,對顧彬以近乎中國通的口吻形容,二十 世紀中國文學,「四九年以前是五糧液,四九年以後是二鍋頭」 (五糧液是大陸的一級名酒,每每是在中南海用以招待國賓的,二鍋頭 雖然衝,卻是民間一般人喝的)。 又說:「四九年以前的文學,基本上屬於世界文學;四九年以後,除中國 史外,外國人基本上都不談」--可能就會心平氣和,並很高興他對 四九前的中國文學還高估了。
事實上,這位現年六十二歲、自己也寫詩、也創作、已出版五十多種 漢學題材的書,目前任教波昂大學的德國漢學家論點,只是很不幸的 證實了我長久以來的看法: 即是我在「文學是永遠的,創作是一輩子的」一文裡寫的: 「直到現今,國際上仍有不少研究華文學的漢學家,視「當代中國文學」 為當代在「中國大陸」創作的文學,「當代中國文學家」也只限於我們 口中的「大陸作家」」。
這個偏見多少說明了,相較於「大陸作家」的我輩,半世紀以來,一直 如何輸在起跑點上。 加上缺少在歐美日等已專業化的推廣行銷技巧--這部分,政府不重視 固然是一個原因,民間財團不支持是另一個原因,真正重要的,還是 整個社會沒有形成重視藝文的大環境!
以日本為例,在已故作家井上靖任作協主席的那幾年,幾乎每到秋冬 「諾貝爾文學獎」開獎前,他家門口都擠滿了各大媒體。起初我不了解 何以如此?只能驚嘆日本大眾重視文學、文學家、以及「諾貝爾文學獎」; 日後漸漸得知,這根本是日本創造「經濟奇蹟」之後,開始邁入重視 文化層面的一個普遍現象。 他們對井上靖的重視和肯定,其實反映了整個國家(加上若干財團)的 「用心」與「信心」;井上靖雖未及得,大川健三郎畢竟得了--雖然, 我總認為,寫「沙丘之女」的安部公房才更有資格。
撇開其它的華文地區不談,今日台灣,顯然距此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而無論是一大段一小段,都得靠自己邁出每一步。
就單純的創作者而言,類似的偏見可能並非全是壞事--畢竟在國片 萎縮的今日,我們也能成就李安這等重量級國際導演。 就重視名利、講究速食效果的創作者而言,可能就頭大了。
其次,顧彬對當代中國作家的寫作態度也不以為然,他說:「在德國, 當一個作家開始寫作,他會寫上一輩子;而中國好多作家像是蜉蝣, 是個短暫現象,很多很紅的作家,一心賺錢去了。」 這當然又是一個真實的片面之見。難道其它國家就沒這類情況嗎?
中國如此,很大一個因素是窩囊百年的這個民族,直到近十餘年, 才由黑翻紅,漸漸脫離窮困貧苦所致,人人都不顧一切的想賺錢,
讓自己活得好一點、有點尊嚴一些。前年去上海,我住在一位 今日中國正值一個「市場經濟」的開發點上,顧彬指的就是這個屬於 部份人的一時現象;我敢說,一旦步入像日本那樣的「經濟成熟期」, 就會看到越來越多的「一輩子」作家。
而且,就算如此,也不意味著一心想賺錢的作家無意或不能成為大師: 過去的莎翁不提,村上春樹在成為暢銷的國際名作家,並擁有「日本 海明威」頭銜後,還是一再表示,他絕非一般的通俗小說家,一貫的 創作態度都是認真的。 我相信台灣不少,大陸上也不乏這樣的名家。
以偏蓋全,以一時論長久,以現象取代真相,正是這位漢學家自身的 最大盲點。 一般讀者可以隨隨便便的說三道四,作學問、搞研究的學者怎麼可以 如此孟浪呢? 這種態度可以取寵於媒體,卻很難能就如卡萊爾「英雄與英雄崇拜」 這樣的一家之言。
多年前,瑞典學者、也是決定「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瑞典文學院十八 院士之一的馬悅然,就因對當代中國文學認識有限(很可能已無遜我們 大部分的學者),多度一意推薦,想把這個獎頒給北島;後來幾次來台, 相信對「中國文學」,特別是「中國當代詩歌」這部分,知悉的要比顧彬 多,也不致說出類似輕率的話。
至於從中國作家不通或不精外語而來論斷一個或一國作家的高下,最多 只是自覺或不自覺的顯示自身(如精通多種語言的顧彬)「優越意識」的 沙文心態。 過去,我認為可笑,此刻,卻不免認為愚昧了:無論懂不懂外語,誰能 說「德國現代文學之父」海涅,只因終生堅持創作本國文學,而不是 一代大師?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在全球趨勢化的今天,更算不上多重要的議題。
當代中國作家和整個文壇、生活環境確是有很多、很大的問題;顧彬的 幾點批判,除了剛才我所指出的一些,身為愛詩人,我最在乎的還是 這兩句: 「中國沒有當代詩歌」、「所謂的當代詩歌,僅是外國文學的一部分」、
若說偏重外語、無視中國以外的漢語作家是愚昧,說這兩句話的人, 簡直是狂妄了!
當然,顧彬一定有他的見解。 我不知他是怎麼想的,我只能自問:
若由一個時代有無大師,是否產生過經得起時空沖刷的作品來判斷-- 現當代的中國似乎沒有大師,是沒有幾部稱得上經典的詩作。 若要比爛鬥嘴,我自可以反詰:你們又有幾個大師?又有幾部經典詩集? 卡夫卡為何也默默而死?還不是五十步笑百步。
但何必呢! 所有藝術的價值都在於達到的高點;大師更是如此,他留給我們而歷史 接受的,永遠是他最好的,而非次要作品。 面對藝術,每一分每一步都很重要,就這一點而言,五十步是會被 百步笑的。
而「所謂的當代詩歌,僅是外國文學的一部分,」雖有部分事實,若由 詩的「本質」來看,顧彬顯然不可能了解台灣詩人瘂弦所謂的「一日 詩人,一世詩人」這句充滿深情、而且更貼近真理女神的名言。
換言之,顧彬可以看不起中國當代詩人,無論如何,都不該說出「中國 沒有當代詩歌」這種被自滿矇蔽而狂妄無知的話。
想想那些愛詩、吟詩、在月光下歡喜寫詩的年輕靈魂吧! 想想無數世紀以來、地球上每個有人的角落,那些安靜或狂熱創作的 影子吧! 想想自己童年讀過、生澀青少年時寫過、睡前母親在床邊唸過的••• 那種感覺、那種心情、那種美好、乃至像一粒種子抽長成芽的神奇 過程•••
一個大師也許就這麼的誕生、啟蒙了;數百萬計的靈魂啊,卻各自得到 珍貴、溫馨、無法取代、不能複製的人生拼圖••• 詩歌、文學、藝術的價值,不就在這裡嗎: 永遠的喜悅、並讓人生發出更美的光!
一定要出名、一定要寫出讓人眼紅的曠世傑作才是作家、才是作品嗎?
--那是尼采,失去詩心後,他瘋了。 --那是莊子,因為滿溢的喜樂,他化身成萬物,達到了天人合一的 境地。 --那是顧彬,批評別人永遠比自己創作要容易。 --那是我,一個已孤獨寫到今天的愛詩人。
一個人,不該認為只有為了創造巨著的寫作才是寫作,才是作家。 一個學者,更不該狹義的,為詩歌、為文學、為一切創造性的作品, 下缺乏人性的定義! 希特勒的時代已逝,希特勒的作風和想法都被歷史證明是可怕的。 用六十年時間創作「浮士德」,深深了解人生的歌德,一生言行才是 更值得重視、學習的對象!
過去,我常和朋友說:「只要你寫,你就是詩人」、「一如人人有佛心, 人人都是詩人」。 近些年,我更深深了悟到,只要存著那份詩心,舉手抬足都是詩! 就算你一輩子都沒握過筆、透過按鍵寫出一行詩,你也是詩人!是 活脫脫的生活詩人!甚至比鑽入文字迷宮的「文字詩人」,更接近詩的 核心!
走筆至此,我已不想多說什麼了。 對顧彬的盲點,我深表同情。 對顧彬的真誠批判,我同樣感動。 對大陸翻譯家、劇作家葉廷芳所言:「一個嚴謹的民族、嚴肅的作家、 嚴謹的學者,面對一個陷入浮躁的民族、浮躁的作家群」,並發出 「四九後,中國缺少創作上想像、內再和外在環境上的自由;在二十 世紀的下半葉,中國有出過一個思想家、大作家嗎?」這樣沉重的感嘆、 呼聲,值得我們深切反省。
但對葉說,「一個民族沒有自己的思想是最可悲的,這證明你這民族在 世界上沒有說話權。」 我想補充的是,「羅馬不是一日形成的」,思想更不是一蹴可及的, 日本要經過「明治維新」加上兩顆原子彈、德國要經過兩次世界大戰, 各自才有了今天--
所謂「民族說話權」,在已然「地球村」化的二十一世紀,根本不是
我關心的是:寫詩、創作的我們,也是每日和百億眾生一樣活在 同一顆太陽下的我們,能從歷史學到什麼呢?
簡單的說:我們究竟為何寫作呢?
2007/3/28寄自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