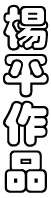
|
說「性靈」
1. 從小就對「性靈」一詞困惑而嚮往。 在這之前,我已知道,並透過一黑溜的長髮,喜歡了我所認為的「靈性」女孩──沒有長髮,一個人,特別是少女,最多可形容為「清純」,是難得稱得上氣質或「靈性」的。 《紅樓夢》(八十一回)便有寫:「我看他相貌也還體面,靈性也還去得,為什麼不念書?」指的便是這等意思。 這些天真的想法,幾乎左右了我全部的青春期。而我的青春期又特別長,直到進入新世紀,都年入中古了,才不得不黯然同意:「時代不一樣了,」 當然,不一樣的是時代、是少女、是社會環境對美的定義與追求,不是我對「靈性」的長髮女子的偏愛,有何改變。 啊哈。
2. 「靈性」固然是小說裡常見的字眼,相較下,「性靈」更是,從文學到美學到哲學到宗教,有時還包括心理學等等,範圍就更廣泛了。 我個人感興趣的則是文學(特別是詩詞)上的運用與見解。 如韓愈(768-824)〈芍藥歌〉:「嬌癡婢子無靈性,競挽春衫來比並。」便可見這等嬌娃雖有天然風韻,卻少了些流轉之間的別樣深度,自是可憾。
南朝文評家劉勰(約465-約532)在其钜作《文心雕龍》〈原道〉篇中說:「人之所以是『有心之器』,而不同於自然界的『無識之物』,即在於人是『性靈所鍾』」。 北朝顏之推(531-591)在其傳世的《顏氏家訓》裡說「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亦是此意。
其稍後的文評家鍾嶸(約480—552)在另一經典《詩品》中強調詩歌「吟詠情性」的特點,表示詩人之真美在於「即目」、「所見」,如阮籍詩可以「陶性靈,發幽思」,和後來「性靈說」的主張十分接近,所以袁枚(1716-1797)說:「抄到鍾嶸《詩品》日,該他知道性靈時。」(《仿元遺山論詩》) 若再往上推,唐詩人李商隱(813-約858)也曾說:「人稟五行之秀,備七情之動,必有詠歎,以通性靈。」(《獻相國京兆公啟》) 南宋時,楊萬裡(1127-1206)因反對「江西詩派」的模擬剽襲、與為文愛掉書袋的習氣,主張「風趣專寫性靈」,如這首〈曉出淨慈寺送林子方〉:
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 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
當然,各個時代的「性靈說」,自有其時代因素,像明代前後七子(1480-1520,1520-1570)等受嚴羽(南宋詩論家,生卒年不詳)「法盛唐」的觀點影響,極力推崇重視盛唐詩歌,宣導「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主義,反使當時詩文大都陷入模擬蹈襲的死胡同。
等到反叛大王李贄(1527-1602)提出「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的《童心說》:「詩非他,人之性靈之所寄也。」(李贄《雅娛閣集序》)。也因而影響了後來的晚明文學革新,「公安派」領袖袁宏道(1568-1610)便喊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袁宏道《序小修詩》)」此等詩歌理論:「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繼之的袁枚(1716-1797)可謂集大成:「“真”、“趣”、“淡”是“真性靈”的體現。」並更進一步的,由「才」、「性」角度發展出「性靈說」:「詩宜樸不宜巧,然必須大巧之樸;詩宜澹不宜濃,然必須濃後之澹,然人工未極,則天籟亦無因而至。」(《隨園詩話》)。 其「人工未極,則天籟亦無因而至。」一語,我們的「詩聖」杜甫可算是最佳範例。 而「漁洋山人」王士禛(1634-1711)通過嚴羽「透徹之悟」的理論,創立「神韻說」。「格調」說由沈德潛(1673-1769)提出,「肌理」說乃翁方綱(1733-1818)建立,加上袁枚「性靈說」,四家各有偏愛,也在有清一代各領風騷。
3. 嚴羽的《滄浪詩話》大體以禪論詩,其中〈詩辯〉裡有一段這麼精采的名言: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境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隨著時空流轉,邁入現今,「性靈」可又有生出什麼新意?或在古體之外,要怎生書寫「性靈詩」呢?
嚴滄浪《詩話》謂:「盛唐諸人,唯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余謂:北宋以前之詞,亦復如是。然滄浪所謂興趣,阮亭所謂神韻,猶不過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為探其本也。」
以今日觀之,「性靈」自「性靈」,「興趣」自「興趣」,「神韻」自「神韻」,「境界」自「境界」,各有各的面目、性情、風格、與夫深度,這點可由不同標籤的門派均出過大詩人為證。
也許這正是若干古典流香的奧妙所在,無論時代怎麼變化,學者怎麼扯,只要人心人性不變,人類還是地球而非外太空來的外星訪客,對「性靈」的看法都不至有多大差異。 像我過去寫的這首十四行詩〈在靜謐中聆聽夜的聲音〉:
今宵又是雨後的春夜 庭前花木鬱鬱染濕了窗痕 偶然映出一抹淡綠月影 原是宇宙心中的的一點孤寂
獨立于世人遺忘的都會一角 在靜謐中聆聽夜的聲音 淡香的茉莉悄悄傳述著紅塵的哀愁 極度蒼涼下的一抹溫柔啊 彷彿在深情的耳語 : 讓過去的過去 消散的消散 不必為昨日哭泣 也不必在意窗外的路燈是否為我點亮•••
隨手摘下一片樹葉 拋向記憶的邊緣 遠處 彷彿有人在彈琴
我便自覺很「靈性」,有趣味,有意境,有神韻,也多少表現出當代氣質的「性靈詩」。 若覺得此詩有點高蹈而嚴羽太過文謅謅,不妨看看李商隱的五絕〈登樂游原〉:
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或袁枚描寫隨園的〈雜興詩〉:「造屋不嫌小,開池不嫌多;屋小不遮山,池多不妨荷。游魚長一尺,白日跳清波;知我愛荷花,未敢張網羅。」 這些詩都很樸實,雖不華美,抒發的正是「性靈」。還有貼在隨園大門口的這副對聯:
放鶴去尋山鳥客 任人來看四時花。
換言之,一個人只要能靜心玩味,親近風雅,自然可以感受到何謂「性靈」?與夫人生蘊藏的、每每若隱若現的、可以感受、卻難以言喻的美妙與意境。 「性靈詩」當也是這麼一揮,便流出來了。
2015.6.12寄自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