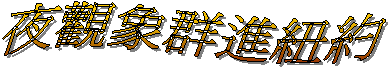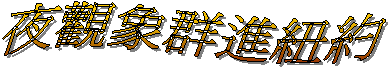從皇后區通向曼哈頓的中城隧道關了,還有通往麥迪遜廣場的幾條路也封了。女兒放下電話說。
恐怖分子來了?我臉一變色說。
不!象來了。
哈哈!真是大陣仗的。
你去看不?今晚
11 時45 分12
時,牠們從中城隧道走出來,大象遊街呢!
不!三更半夜的,又是零下五度。
這馬戲團年年來紐約演上那麼一個月的。這大象遊街的新聞,往往在第二天的報紙上才看得到。現在是那一帶的社區內部消息,通知社區的人在晚上十時半到酒吧集合,邊喝酒邊等大象。朋友剛才通知我,我們廿多年才得一次這樣的消息呢。
這一個名叫Ringling
Bros. and Barnum & Bailey的馬戲團,據説成立於1793年4月3日,第一次表演地點:Philadelphia(費城)。每年三月份來紐約,來紐約後火車把牠們卸在Queens(皇后區)。牠們只得步行,從Queens
Midtown Tunnel入口,走隧道中的北道(長6414英尺),走完這平日車水馬龍似的熙熙攘攘的隧道
--到曼哈頓的Midtown
Tunnel 出口處走進Tunnel
Exit street--向右轉進入34 street--向左轉走進入7Avenue--再向右轉走到7Avenue的33street終點就在33street上的巨型建築物Madison
Square Garden。據説這麥迪遜廣場地下室就是牠們的賓館。
每年牠大駕光臨的消息,總是保密的。儘管那樣仍有人得知天機,冒著嚴寒候駕的。牠們是紐約的貴賓,其演出場場爆滿。我也看過牠們的表演,真是精彩絕倫的。可象成群結隊地在曼哈頓的大街上行走,這倒新奇,真未見過。一下睡意全無,趕緊說:現在11時半啦,還來得及麼?
飛車!
一眨眼,車已開到威尼斯堡橋。撲入眼簾的是璀璨的萬家燈火勾勒出的曼哈頓那壯麗多姿的輪廓,五光十色的燈火映照那波光粼粼的河面。這一切,瀰漫著神話般的夢幻。
難以想像這原始森林的動物怎樣進入這鋼筋水泥的森林!
現實生活中的科幻小説題材。女兒一語,增添了這神話的色彩。
不一會,車停在曼哈頓的
Midtown tunnel出口處的Tunnel Exit street上,那兒,早有警員在擺著警戒用的柵欄。已有不少看客了。一個個棉的、皮的大衣,雪靴、圍巾、棉帽,把自己裹得嚴嚴實實的,頂著凜冽的北風在那兒築起了人牆。大多是白人青壯年。其中,年齡反差最大的是:我這一個黃種的古稀動物和一個約八歲大的白種的初生之犢。
女兒外出張望,叫我在車裡候著。等到差不多到淩晨一時了,還不見大象的影子。我在想,大象這樣笨重的,肯定走得一搖三擺的,遲來不足爲奇。後來才知道,原來在封路之前,那大象必經之路出了車禍。撒得滿地玻璃,警方正在清除到沒一粒玻璃碎片才敢讓大象行走。
我坐在車上百無聊賴的,免不了又胡思亂想:萬一那象發起性來,一腳踏在車頂上或者把車捲上天,然後狠狠一扔
這時,我想起我看過的一本書,裏面寫一個真實的故事:在印尼一條小巷裡一位老婦被迎面而來的大象嚇得當場暈倒。那像沒有踩她,反而蹲下來看了好一會,然後伸出鼻子把她捲著,放在象背上。走到人多的地方,把她放了下來。
我想在車內那象不識我這盧山真面目,我站出來,牠也許會知道我也是一個老婦,不會把我怎麼樣的。
媽呀,外面很冷!
我把我的思想情況向女兒坦白了。
哈哈,是大笨象笨還是你笨!
不一會,那堵人牆動了。那些看客像被人用手提著脖子的鴨,那人牆的弧線登時向上升了好幾度。
象來了!看著這樣的架步,我在自言自語。趕緊往中城隧道口望去。只見那兒有兩道會移動的白光。
虎來了?狼來了?虎狼的眼會發光,那大象的眼不會發光的呀!想到這,嚇得拉著女兒轉身就跑。女兒反而把我拉住了說:象來了,那是警車開路!我再不敢向女兒坦白些什麼,我怕她又說我笨。
是警車?但爲什麼悄然無聲的,沒了往日那種未見車來先聞其聲的威風。我嘮叨著。
它再發出警笛大喊大叫,那象群不亂了套。那時大象就是本拉登了。女兒說。
警車後有輛拖車,是平時用來對付路邊那些違規的或壞了的汽車的,可能現在是用來對付那些走到一半就不肯走的象吧。但我想,真是那樣的話,這拖車也對付不了的。
拖車後一頭特巨型的慓悍的大象,凜凜然走來。牠背上坐著一個人(在整個象隊中只有這一個人坐在象背上)。只有牠披上一大塊棗紅色的用發光的珠子來鑲邊的披肩,上面有幾個英文字:I
LOVE NIU YORK!(LOVE用心形來代替),其它的象,一絲不掛。
瞧牠那派頭,顯然是象隊的首領了。在牠後面,走著五頭大象一頭小象。每頭大象的頭都用發著亮光的鑲著珠子的布帶裝飾著,這帶子把一塊牌子固定在象的額上,上面寫:The
Greatest Show on Earth(世界上最大的絕妙的節目)。象群是相互挨著行走的。牠們像是各自獨立又相互關照地走著。其中,有兩頭大象的走相很特別。一頭象的鼻子捲著另一頭象的尾巴走。讓你想到一對夫妻、一對情侶在牽手。而那頭小象就緊挨著這兩頭與眾不同的象的旁邊走。那情景,就像一個孩子依偎他的雙親。我想這大概是象的一個小家庭。隨即,我又納悶了:如果真是那樣那兩頭大象爲什麼只顧得自己的恩愛而冷落了下一代呢?如果不是小家庭那小象爲什麼對牠倆如此依戀呢?我想問,問誰呀?
我以為這麼多的象經過,不地震嘛,起碼也會有沉重的咚咚聲,誰知象蹄聲猶如馬蹄聲。這些象真乖,怕擾紐約人的清夢呢。
牠們一點也不左顧右盼,一個勁兒地急匆匆地趕路,那小小的眼睛也不眨一眨;那長長的鼻子也不卷一卷;那大大的耳朵也不搧一搧。總之給人的印象是:專心致志地走。其莊重的神態不亞於古時的讀書人赴殿試;現在的求職者去Interview。
我想,牠的耳洞不會被那塊像大葵扇似的東西蓋住,什麼也聽不見吧,不然,爲什麼牠們對圍觀的人的呼叫毫無反應。聽,人們在呼喊:多可憐!這天寒地凍的,走那麼遠的路!牠們一臉的悲傷呢。爲什麼不用車子把牠們送往旅館?
我正在給牠們點數,我像一個小學生那樣的念數速度從一開始順著念,點到第七時,象群全在眼前通過了。
怎麼走得那樣快!我在驚叫著。回頭望去,只見像有一座灰黑色的小山坡在曼哈頓的大街上向前移動。
我望著離去的象群惋惜著:怎麼僅有七頭?
忽然,一陣很有節奏的得得聲是那樣的清脆悅耳。像是這寂靜的大都市的夜空敲起了鼓點。我趕緊轉過臉來看,原來在象群之後又有兩輛警車,警車之後
有好幾十匹馬和驢,牠們的身上都裹著毯子。看著牠們的毯子,我就為剛才離去的除象首外的那六頭象赤裸裸地走著而鳴不平。
奇!沒人騎著和趕著牠們,可牠們成四路縱隊前進;怪!打橫看去,基本上成一字形。
咦,比奧林匹克的入場式還要整齊!我在驚叫著。
不可能,沒人指揮、沒人驅趕,沒任何聲音暗示,為什麼會走得這樣整齊的?我想問,又問誰呢?
跟著動物進城的還有人,他們在馬、驢隊伍的兩旁用手拉著一條繩,小跑著前進。這繩子可能是起著馬圈柵欄的作用,讓馬、驢不要越過這條繩而走到人行道上。在這零下五度的環境下這些人僅穿薄薄的衣衫,而臉卻是紅撲撲的。有人還在揩汗呢。
馬、驢隊伍之後什麼也沒有了。怪!紐約人的遊行隊伍之後往往有垃圾車跟著的。而牠們走過的街道卻是那樣的乾淨,難怪沒有垃圾車跟著。嘻嘻,牠們比人還聽話!
容不得我在思忖什麼,那雙腳也不由我指揮擅自跟著剛進城的動物大軍跑去。
在場的看客早已一窩蜂地往動物大軍可能通過的街道提前跑去攔截。我忘了自己的年齡,比女兒跑得還快。望著那像一座小山似的象群和像塊鋼板似的馬、驢群,在曼哈頓的鬧區匆匆向前移動著。忽然,那相互挨著走的象群成一路縱隊地前進,馬路上像有一條巨大的鋼柱在移動。沒有人指揮,牠們就這樣擅自改編隊形。我還以爲孫大聖用牠的猴毛化成這些動物大軍在捉弄我們。我真不知道自己是否在夢游中。
我邊跑邊笑:天上的衛星可否攝了?這世界大都市的鬧區,這密集的摩天大廈周圍,這多彩的霓虹燈下,一隊尚解人意的象在有組織有秩序地行軍;一群不解象意的人,在無組織無秩序地狂奔。誰正誰奇?哈哈!我分不清啦。
媽,別跑,我開車搶在牠們的前面再讓你看個夠。
趕得上麼?牠們走得快到出乎意料的。
我就不信四個車輪快不過大象那四條腿。
車時而順開時而倒開,幸而晚間車少,此處的警察今夜關注的重點是人以外的動物。任她使盡渾身解數,待車趕到7大道的33街轉彎角,我趕快跳出車外看時,迎接我的是那大象的一個個又圓又大的屁股在晃著,像鞍山鋼廠工人舉著的大鐵鍋;還有那一條條細長的尾巴在搖著,像卡內基音樂廳指揮家揮著的指揮棒。
爲什麼會跑得這樣快的!我想問,又問誰啊?
我戀戀不捨地望著那灰黑色的山向前移動,直到它在麥迪遜廣場的大型建築物前消失,我在寒風中呆呆地佇立,不忍離去,夢耶?非夢耶?一時變得糊塗了。
這時一陣口號聲把我喊醒。原來上百人站在大象下榻處的麥迪遜廣場的大型建築物前,高舉示威的牌子。上寫著Stop
Animal Cruelty(不准虐待動物)!我馬上把它記在紙上。我此舉大概引起人們注意。一位白人女子遞一張印得很漂亮的傳單給我,上面印著一只象腿被鐵鏈鎖著。下面這樣寫:THE
SLAVE TRADE IS ALIVE AND KICKING(奴隸交易仍然存在和活躍)!
回到家已是凌晨二時,怎麼也睡不著。想著那被馴服得如此聽話的大象,心裏一陣興奮,但隨之眼前又晃出那傳單印著的象腳上的鐵鏈,我煩躁了,我沒了是非標準!
寫於2006年3月20日象群進紐約後的第二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