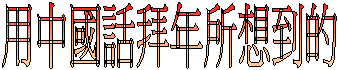
打電話拜年是紐約華人主要的拜年方式。在眾多親友中,最令我心靈震撼的是給兩位兄弟拜年。在檀香山的哥哥,是我們家族乃至全體華人的驕傲,因他在1982年榮獲美國科學二等獎。這位享有盛名的物理學家,有一句令我聽起來鼻子發酸的話:“我每年只講一次中國話,那就是在你給我拜年的時候。”
紐約和檀香山時差有五個鐘頭,我整天心神不定地盤算該什麼時候打電話才合適。平時我哪敢打,聽說他天天由飛機送到山頂去上班。
“鈴!”我懷著激動的心情等待著鈴聲之後哥哥那親切的聲音,誰知卻是我那位日裔的嫂子接電話。她講了一段英語之後用中國話說了一句:“恭喜發財!”
放下電話我黯然自語:“今年哥哥連講一次中國話的機會都泡湯了!”
幾小時後,家裡的電話鈴聲響起來,我拿著電話筒高興得差不多跳起來:“哥,你剛才去哪?啊,去打乒乓球,對,那是我們的國球。”
“你說你的十首詩入選在《全球華文詩詞藝術博覽全書》,這書什麼時候有賣?我要買。你懂中國文學,要多寫,特別在美國。我們國家的文學很豐富的,但我這裡找一本中文書也難。哪像你們紐約有中文電台、報紙、書店的。”
“哥,你還記得中國字?”
“記得一些,我查字典慢慢看。看起來很親切,像回到家那樣。我給你寫信,那些方塊字就這樣湧出來了。那畢竟是祖宗的東西,自家的東西,忘不了的。”
放下電話,我想起和哥哥那樣也是小小年紀就出國的弟弟,23年前我和他在紐約相逢時他只會叫一聲“姐”。此後十多年,姐弟交談全靠我弟媳翻譯。後來,其工作對象越來越多華人,老外找他翻譯,急得他連夜找我想辦法。這時我想起曼哈頓一些西人商店門口貼的告示:“我們會講中國話。”這樣才有不少不懂英語的華人光顧。但我弟所在的機構是法院,法院傳你去時,你不懂英語也得去的。不像你逛街時知道店裡有會漢語的,你才進去。這就難倒了不懂英語的華人和不懂漢語的老外。看著我弟那副華裔面孔,懂不懂漢語的都找他。
我搜刮枯腸,想不出一個應急之計。後來見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英漢、漢英詞典,便送他一本,叫他按漢語拼音學講普通話。我還把CCTV4《快樂中國—學漢語》專欄節目錄給他。他晚上對著字典讀;對著華語電視劇邊看邊學講話。
去年,在宴會上我和他同席。他居然整個晚上用普通話和我交談。
“姐,我第一次聽人家說‘老婆’,不知道他說什麼,回家問阿玲(其妻),什麼叫做老婆,阿玲說老婆就是她。”頓時,人們笑得有牙沒眼的。他還一個勁地問:“叫老婆?不是叫愛人的麼?”
“叫老婆不文雅,叫愛人不準確。以前我們叫學生作文,題目是《我的媽媽》。有學生這樣寫:媽媽----我爸爸的愛人。有老師這樣批:‘不一定!’”我話音剛落,有人噴飯了。
這樣的弟弟我非要利用拜年的機會考他不可。他果真講了許多吉祥的話語,講起普通話來沒那樣中腔西調的,而且還能組成一些句子。
每提及兄弟的語言困境,我就想那幾個在美國出生的孫兒女,非要他們懂得中國話不可。昨天到兒子家吃年飯,一進門孫女就說:“Happy
Chinese new year.”
“不說中國話我就不派‘利市’。”
不一會,我耳邊響著清脆的童音,標準國語:“恭喜發財!”
大孫女告訴我,她考紐約重點中學時的那篇作文取材於長城。後來老師要她拿著照片到各班去介紹長城。正當她興緻勃勃地說這一切時,她家裡電視吸引著我:“中國對外國學生進行中文的‘托福’考試”,接著,那美國中文電視台又賣廣告,紐約有名的顧維斯律師,這位上了年紀的老外身穿唐裝,頭戴瓜皮帽,在打躬作揖,用那讓人費很大勁才聽得懂的中國話說:“恭喜發財!”
我孫女在問:“他那個‘恭喜發財’怎麼不像我們的‘恭喜發財’?”
“你們是華人,更要學好中國話。”
2007.2.23(丁亥初六)寄自紐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