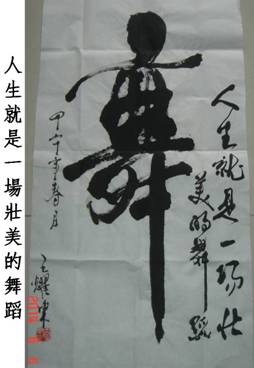|
|
|
嶄新的路 是勇敢者踏出來的 ——《王耀東詩文選》訪談錄
綠色中國網總編 顯 勇
讀《王耀東詩文選》使我進一步想到美國《新大陸》詩刊在2001年發表的詩評家劉耀中的一篇關於“美國詩人羅拔.弗羅斯特”中的一段話,他說:“在中國詩壇上,我特別關注王耀東的新鄉土詩,他探求了一條詩神之路,他的詩已經不是習慣意義上的鄉土詩,如變形、隱喻、象徵、幻化、畸聯等,是詩歌觀念和審美超向的根本變化,這種精神變化和弗羅斯特是相通的。”這一段話實際是指出了大陸鄉土詩人王耀東和美國19世紀桂冠詩人產生了歷史性的對接。大家都知道,詩人與作品歷來是見仁見智,各有所好,那麼大陸上王耀東的詩怎麼就和美國詩人扯到了一起呢?終於找到了一個機會,在發行《王耀東詩文集》的時刻,讓我見到了這位詩人,並同這位鄉土詩大家進行了訪談。
果然,文如其人,同王耀東的這次交談,如讀他的詩,他人樸素而且使人愉快,簡練而且深情。
我問他:“你喜歡美國的鄉土詩人弗羅斯特嗎?”
答:任何詩人都有過自己在歲月中的掙扎,美國這位詩人,經歷也很艱難,但他很刻苦。少年時期,在農場勞動過,還當過織布工人,很能吃苦耐勞,他寫詩是受母親的影響,雖然他寫詩,但沒有寫出名堂,快四十歲了,去了英國,接觸了英國“喬治安派詩人”,從此一舉成名。我是在八十代,在一本外國詩集上,讀過他的詩。我贊成他對詩的觀點:即“文學是淨化生活的,它能去掉社會上的一些雜質。”是的,我們的靈魂依附於這個世界,詩人在不同的區域塑造了各自的靈魂,我們還要把她歸還給這個世界,這些就是詩人的歸宿。
問:弗氏有一首著名的詩篇叫:沒有走過的路,詩中說,人生有兩條路,一條是尋常人走的路,一條是無人走過的路。你走過的是哪一條重要的路呢?
答:弗羅斯特一生喜歡探索,重視自己的感覺,他死後,從他家裡發現了一千多封沒有發出去的信,從中可以看到他的思維活動,那就是傾訴自己,這種對詩的探求與傾訴他不想讓人知道,實際是述說了詩人艱難探求的悲傷史,重視靈魂深處的這種開掘,就是一種不同的詩人之路,敢於向靈魂深層傾訴,找到自己的制高點,是不容易的事。我開始寫詩注重事件的描寫,往往不注重開掘心靈的細節,結果把那些土的掉渣的又值得捕捉的細節忽略了,後來明白了,我們忽略的往往也是最值得詩人去挖掘的。例如鄉間那些不起眼的事,在農人看起來都是極平常的事,然而你換一個詩的角度,用詩的眼光去觀察,就感到新奇了。在80年代我寫過一首“他要挺起的”詩,寫的是一位農人進自己新蓋的房門時,不經意的彎了一下腰,這個“彎腰”和“一個挺起”是一種歷史的巨大變化,想“挺起的”是一種自信,結果被貧窮壓彎了,是很難再挺起來的。此詩引起了當時詩壇的廣泛關注,出現了不少評論。咱們有一句話,叫老樹開新花,是極平常的事,也是習見習聞的事,如果用詩去挖掘它的新花,就有了新趣、新奇。寫鄉土沒有“土”怎麼行呢?有土才能生新芽。我從小就是趴在地上,吃土抓土,是身上沾滿了泥巴長大的,我那時一聞到土就覺得很香,在幹活時鞋中都塞滿了土,汗珠和土攪在一起,沒有覺得鞋裡臭啊!這些看起來非常樸實的甚至還有點愚昧的、苦澀的、醜陋的細節,往往是發現神奇故事的精神支點,所謂鄉土性最重要的是要從農人的傷痕中發現心靈的蘇醒。我從小就跟著父母下地幹活,十四歲就學習用木輪車推煤、挑水,在河灘挖沙種瓜,這些受苦受累的活兒,現在看也是一筆重要的財富,沒有遭難的感知,也寫不出有自己鄉土感悟的詩。
問:你的述說,讓我很感動,你這一生也非常不平凡,能執著追求自己的鄉土詩,不像有些寫鄉土詩者,就刮一陣風。
答:我讀弗羅斯特的詩,思想上經常產生共鳴,就是那種真實感。鄉土最重要的在於樸中有真,弗氏喜歡大自然,認為世界上只有經過原生的自然的洗禮,才純樸、真誠,所以他特別喜歡大自然的空氣,喜歡大自然的流水,其實這是他靈魂深處的奧妙。這也是他與同時代詩人的不同性。也是他成功之處,他是用鄉村的哲學,農夫的眼光看待一切,於是他的詩就是他自己的世界。也就有了他的個性和特色。
問:這一點你倆有共同之點,我喜歡你寫的“最初的歌”、“拔節之韻”、“揚麥場上”、和那些寫母親的詩,讀起來就覺得是自己身邊的事,動情處還讓人流出淚來。
答:我有我的立足點,就是一個農民兒子對自我的審視,用一個農民的眼光來審視自己,故土上的人、事、及風俗人情,其實就是詩的“能”,一種詩的磁場,這些東西都潛藏著詩的無盡的創造力,對於它神奇的發現,就是鄉土自身的一種醒悟與感覺。中國歷史上有成就的詩人告訴我們,神幻源於一種真實,這個真實卻是原始的,它比人的情感更深沉、更難言、更便於流傳,這就是藝術的胚胎,就是藝術的磁場,在我們的生活中散發著無窮無盡的能量。抓住了它,就抓住了詩人創造個性與特色的核心。
問:人人都有自己的夢,我發現你的夢一直放在鄉土上,七十多歲了還沒有離開,這是為什麼?
答:人的夢都在頭頂上放著,就是說放在至高無上的地方,不管別人怎麼放,有的人甚至是放在城市的高處望鄉土,我與他們不同,我把夢始終放在了自己腳下的這片熱土上,這裡有根有花有果,一代代長著麥穗的金黃,這裡有一代代不會衰竭的夢幻,凝聚著鄉土的靈魂,一代代發出神聖的呼喚。
問:時代變了,商業的慾望影響了人們對貧困鄉村的看法,做為一個詩人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答:問得好。這也是現代詩的一種苦惱,所謂現代,從根本上說,就是日益發展的高新科技和日益膨脹的貪慾粘在了一起,一切都表現在利慾上,市場利慾的驅動,把純淨的詩篇排擠到了最邊緣的位置。寫鄉土唱鄉土越來越變得不值錢,生存都困難了,這是一個無法改變的現實,其實這種東西本身就不是一種商品價值,從本質上講,文學的使命不是輕了而是重了,我們的詩我們的文學,要告訴人類的是:污染是對大自然的破壞,鄉土地上處處拆遷,是對原生態的破壞,這樣就賜予了詩與文學更深刻更偉大的使命,那就是呼喚鄉土的陽光、食物和水,呼喚人的良知與美、善,來保護我們的地球和人類,詩如鄉土地上的布谷鳥、淨化劑。時代在發展,詩表現手法不能退化,也要不斷的更新自己,自覺跟世界先進文化對接。要與時俱進,用詩與文學的形式來表現、述說。一部《紅樓夢》,它是世代能傳承的財富,唐詩宋詞,有的甚至僅僅是幾句話,卻能讓一個民族驀然蘇醒,就是這些不易說清的詩與文學,述說著鄉土詩的靈魂情結與走向。並能產生不可低估的巨大作用。
問:還有一個問題,我注意到,大家對你的鄉土詩,前邊加了一個新字,是新鄉土詩!鄉土詩和新鄉土詩有什麼區別呢?
答:這個問題很重要,一是說寫新鄉土詩,它的具有新的時代性,更重要的是在於創新,鄉土詩實際是古代的田園詩的別稱,鄉土、田園應該說內涵是一致的。新鄉土是不僅僅是一個叫法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鄉土詩要有它新的詩意的深層結構,現在的田園已不再是陶淵明時的桃源狀態,而是具有荒原化的現象,從農人心理結構上講,現在鄉下人有一種失落感,傳統化的心態遭到叛逆,對鄉村的前景出現了斷裂意識,鄉下人到了城裡會不自覺的產生自我失調感,具有個性化的鄉村從心靈上趨向了弱勢化,另一種是詩的表現手法由於受西方文化的滲透,有一種雜交現象,多元文化的結合對鄉土詩的發展也有很大的啟示性。讀現在的鄉土詩和五十年代寫的那些鄉土詩覺得大不一樣,鄉土這個老字眼兒是在新條件下新異的陌生詞。所以說,寫新鄉土詩一定要寫出俗中的不俗,不凡中的不凡,不神奇中的神奇。思那已去者,盼那將至者,抓住新發現,發現新珍寶。
問:你既然談到了時代的異化對新鄉土詩的影響,那麼做為一個鄉土詩人如何面對這個現實,走出自己的道路呢?
答:世界著名詩人帕斯說過:“現實是遙遠的,它是一個需要經過艱苦努力才能抵達的東西。”帕斯這話說的是什麼意思呢?他說的現實是指詩意的現實,並非是日常生活中的現實,如何用詩去揭示鄉土這個現實,是詩人必須著力追求的東西,如何表達了這種現實?這就是詩人面對的一種挑戰,寫鄉土並非不現實,寫鄉土並非已遙遠,時代精神對鄉土的投射是詩人義不容辭的責任,今天面對鄉土如何與現實去對接,詩人的意象之源又在哪裡?,所使用的心象、心緒、魔幻,都應該是鄉土中的珍寶,是詩的神秘世界。時間是貧窮的,在詩確立詩的本質時,首先要確立它新的時間,這就是現實,詩看起來不是真實的,而本質卻是最真實的,鄉土詩要寫好她的現實性,說到家是如何對自身的一種重新確立,是一項堅實的又是神聖的活動,不應該局限於像與不像之間,而應該是人類靈魂的一面鏡子,我們都有一顆腦袋一顆心,都有兩只手、兩只腳,誰能離開腳下這片土地呢?只要我們認準了淨化的目標,左右開弓,雙向進取,凡是阻擋我們前進道路的石塊、坎坷,一定要排除、越過、要勇敢的衝過去,帶著你的原生態和鄉土給你的氣息,敞開自己的心靈,這樣就決定了你的情調與特徵,這就是詩人高揚的態度與使命,我相信,只要鍾情於此,獻身於此,一條嶄新的路會踏出來的。
2004年6月1——4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