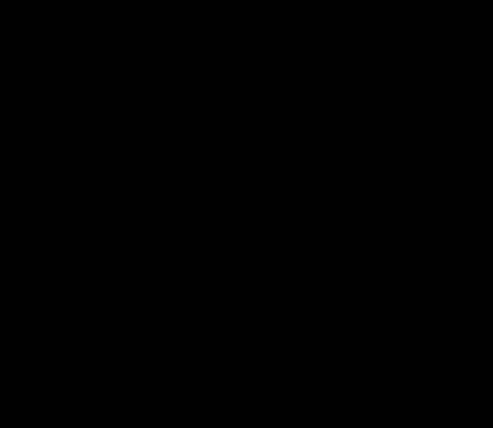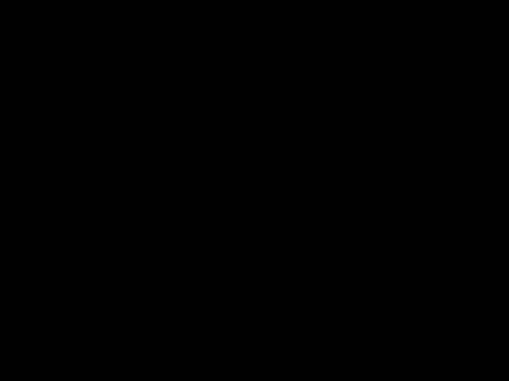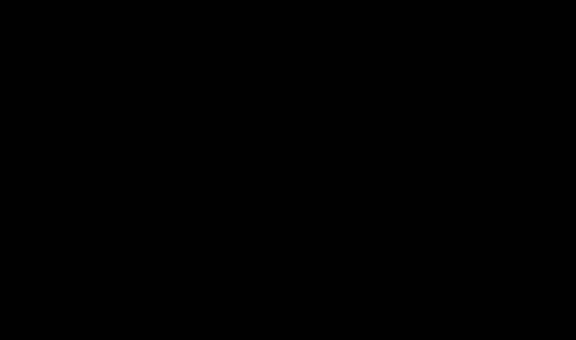名
家
評
介
何 與 懷 評 介
比現代更現代,比寫實更寫實
✦
試談非馬詩歌藝術追求與思想內涵
非常有幸,由於參加一些國際文學會議,很多年前就結識了非馬先生這位享譽世界華語文壇的“業餘”詩人。私底下,我們不時電郵往來,通常是他傳來詩作讓我欣賞,我則傳去文章向他請教。記得相處最密集的是2008年三月那次。他與夫人應邀一起到悉尼訪問,立時掀起一陣旋風。應文友們要求,我在《澳華新文苑》刊發了一期“非馬專輯”,並與澳洲酒井園詩社以及“彩虹鸚”網站一起舉辦了幾場座談會、聚餐會,以歡迎他們的光臨。其情其景正如悉尼詩詞協會會長喬尚明以金·劉著〈月夜泛舟〉、清·姚鼐〈金陵曉發〉、宋·王沂孫〈高揚台▬和周草窗寄越中諸友韻〉,以及唐·高適〈別董大〉各詩集句所描畫:
浮世渾如出岫雲,風煙漠漠棹還聞。
如今處處生芳草,天下無人不識君。
多年結交證實,這位“天下無人不識”稱為“非馬”的詩人,的確,此馬非凡馬。這是一匹長途奔馳而壯心不已的駿馬。早在1978年,他在〈馬年〉一詩曾經這樣寫道:
任塵沙滾滾
強勁的
馬蹄
永遠邁在
前頭
一個馬年
總要扎扎實實
踹它
三百六十五個
篤篤
這是自信,也是自許,更是自勵。風入四蹄輕,現在又過了幾十年,來自太平洋彼岸的篤篤馬蹄聲,總是不絕於耳,總是在我們心房迴響。
一
反逆思考:非馬詩作的重要特色
最初看到“非馬”的名字——好像是三十多年前了,總之是認識非馬本人之前許多年,首先進入我腦海裡的自然是“白馬非馬”這個典故,是戰國末年名辯學派的著名邏輯學家和哲學家公孫龍和他的著名哲學論文〈白馬論〉。我自然想到“白馬非馬”那個眾多哲學家特別是先秦哲學家探討和爭論不休的問題。
繼而我又知道非馬這位詩人是一位高尖端核工博士。他在臺北工專畢業後,於1961年赴美國留學,先後獲得馬開大學機械碩士與威斯康辛大學核能工程博士學位,畢業後在美國能源部屬下的阿岡國家研究所從事能源研究工作多年。
因此,我一直最感興趣的是:曾經嚴謹而又長期科學工程訓練的這位詩人與眾不同之處何在?
的確,正如許多論者所言,對於許多詩人與詩論家來說是尖銳對立的詩與科學,在非馬那裡卻得到了和諧與統一;文字簡潔,旋律短促,是非馬詩句的特徵,十足表現科學家的乾淨俐落,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他以對科學無窮的探求的姿態寫詩。他的詩既發揚優秀的中華文化傳統又結合現代文學的先進的表現手法和批判精神,用凝煉濃縮的語言營造驚奇的意象,表達具有多重內涵和象徵的內容;他不但對社會人生熱切關懷而且以冷靜的哲理思考見長;而且兩者相得益彰;人們特別用一個常常形容科學家思考方式的詞來評論他的一些詩作:“反逆思考”。
試看非馬寫於1976年的〈共傘〉這首詩一個片斷:
共用一把傘
才發覺彼此的差距
但這樣我俯身吻妳
因妳努力踮起腳尖
而倍感欣喜
短短五行,三十四個字,卻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塑造了一個饒有趣味而耐人尋味的意境。這種藝術魅力除了取材立意外應歸功於“先抑後揚”的突轉結構法。戀人無意中發現“差距”,有些掃興;但當讀者正要順此思路往下走時,突然出了戲劇性的變化。由於“差距”,一人低頭俯就,另一人踮腳趨迎,愛情經過“差距”的驗煉而愈顯純真,自然使人得到一種特殊的審美愉悅而“倍感欣喜”。這就是非馬的“反逆思考”,先將讀者的思路引向與主旨相反的方向,然後突然扭轉到詩人力圖表達的正確的方向上來,因而獲取新奇獨特、深刻有力的效果。
這種手段在〈鳥籠〉一詩中用得最為精彩:
打開
鳥籠的
門
讓鳥飛
走
把自由
還給
鳥
籠
誰讀了此詩都會極其驚奇和感嘆。採用籠中鳥以喻失去自由是一個相當古老而平常的意象,但在非馬看來,把鳥籠打開,讓鳥飛走,這不僅是把自由還給鳥,更是把自由還給鳥籠。詩人怎麼想到強調後者,而且這麼強烈?!這真是畫龍點睛的驚人的神來之筆!這樣寓意不凡的“反逆思考”,真讓人叫絕。
這就開拓了審美與思考的另一空間。這是一種雙向的冷靜的審視。在一般人的眼裡,“鳥籠”是自由的、主動的、掌握別人命運的。但現在非馬告訴我們,這種想法是淺薄的。事物是相輔相成、相互鏈接又互相制約的動態系統,而不是絕對單一固定、不與他者發生任何關係的存在物。鳥被關在鳥籠,鳥固然失去了自由,鳥籠也失去了自在的自由,不自由是雙方的。許多論者都指出,以此哲理來審視人生現象,便會因詩人新奇的想像的觸發而引起多重的聯想。可以把“鳥籠”和“鳥”的形象看作哲學上的代號,象徵兩個互為依存互為對立的事物,並盡可以見仁見智,將它們解讀為諸如靈與肉、理智與感情、個體與群體、自由與奴役、社會與個人、人的社會——歷史性與人的自足的本性、人類社會與自然宇宙……等等相反相成的概念。的確,順著這個思路,人們其實可以恍然大悟:當社會中的某一層次、某一部門、某一領域的人自覺或非自覺地擔負起監視、限制、管教另一層次、另一領域內的人時,實際上他們也走上了自身的異化,他們同時也失去了本身應得的自由。特別是,在政治領域,非常清楚,禁錮的施加者在鉗制他人的過程中,其實自己也往往陷入無形的囚籠;唯有鬆解禁錮,還他人自由,禁錮者也才能走出自囚的牢籠。沒有自由便沒有和諧——這是起碼的真理。
非馬詩歌意象簡練,卻又內涵深廣豐富,決定了人們對其詮釋和演繹的多元化,〈鳥籠〉一詩是一個最好的標本。這首傑作寫於1973年三月十七日,在臺灣《笠》詩刊第55期(同年六月十五日出版)發表後,在臺灣引起轟動,後來還入選臺灣東吳大學中文系編注的《國文選》。此詩一直是海內外論者品評非馬作品的一個重點,被看成是“反逆思考”或“多向思考”的經典性作品。
許多年之後,非馬又寫了兩首相關的詩。前者是寫於1989年四月廿七日的〈再看鳥籠〉,同年七月一日發表於《自立晚報》副刊。他這樣再看鳥籠:
打開
鳥籠的
門
讓鳥飛
走
把自由
還給
天
空
另一首是〈鳥•鳥籠•天空〉,寫於1995年二月二日(同年十月發表於《新大陸》詩刊第卅期;十月廿一日發表於中央副刊)。詩這樣寫道:
打開鳥籠的
門
讓鳥自由飛
出
又飛
入
鳥籠
從此成了
天
空
關於〈鳥•鳥籠•天空〉,非馬告訴我,這首詩是為一位在美國南部一個小鎮上經營雜貨店的詩友寫的。他為日夜被困在店裡而煩躁痛苦不堪,我勸他調整心態,打開心門,把它當成觀察社會人生的小窗口,同時偷空寫寫東西。後來他大概還是受不了,乾脆把店賣掉搬離小鎮,到休士頓去過寓公生活。在〈再看鳥籠〉附記中,詩人讓人很出乎意外地寫道:多年前曾寫過一首題為〈鳥籠〉的詩。當時頗覺新穎。今天看起來,仍不免有它的局限。因為把鳥關進鳥籠,涉及的絕不僅僅是鳥與鳥籠本身而已。非馬何以將業已還給了鳥籠的自由收回,改而還給天空?正如居住舊金山的美國華裔詩人劉荒田認為,非馬是把鳥籠放到廣大的背景——天空去了,天空的自由,是靠鳥的自在飛翔來體現的。因此,鳥籠剝奪了鳥的自由,歸根到底是剝奪了天空的自由。
非馬原名馬為義,取筆名“非馬”,開玩笑是說自己是人不是馬,也免不了讓人聯想到“白馬非馬”這一個典故,但最主要的是含有跟他詩觀相關的更深層的意義。他希望“在詩裡表現那種看起來明明是馬,卻是非馬的東西。一種反慣性的思維,一種不流俗的新詩意與新境界的追求與拓展”。他對自己詩寫的追求就是:“比現代更現代,比寫實更寫實”。
所謂“比現代更現代”,我覺得主要是他營造意象的手法非常現代,非常新穎獨特。人們發現,非馬詩中的意象大都單一,純淨,他絕不作繁冗的堆疊,他執意讓意象壓縮,跳接,讓意象產生非確定性與多層意義,使他的詩歌獲得外部形貌簡約而內部意蘊豐富的詩美。順便說,正因如此,他的詩譯成外文時,可以和中文原詩一樣完美,既沒有雜質糅入,也不會讓原味消失。還有,他有意識地反逆人們平常的觀物習慣思維習慣,這是他求新的獨特方式。他要從平凡的事物中找出不平凡,從而製造驚奇。創新雖為藝術的普遍法則,但通向“新”的道路卻因人而異,從這裡往往顯示出作者的獨特風貌,其高低雅俗,深刻或平庸,一比便了然於心。劉荒田說,他在解讀上述這三首詩時,不禁想起了禪的三個境界,即見山是山見水是水、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的確,就這三首詩來看,通過詩人營造的意象,詩的意境,詩的境界,層層遞進,每層都有獨特的風光,實在是迭生驚奇,令人把玩不止。許多人都說了,非馬的詩歌作品都充滿著強烈的生命感及雋永的哲思,簡潔純樸的形式,負載著多重涵意及可能性,常予人以意料不到的衝擊。
二
民族悲劇深深滲透的詩心
非馬的價值,在藝術手法技巧之上的,是其“比寫實更寫實”所表達的深刻的思想性。就讓我們從他寫於1981年的〈羅湖車站〉(返鄉組曲之八)說起。當年,他經過中國廣東省深圳和香港邊界的羅湖車站,寫下這首兼具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的詩篇:
我知道
那不是我的母親
我的母親
她老人家在澄海城
十個鐘頭前我同她含淚道別
但這手挽包袱的老太太
像極了我的母親
我知道
那不是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
他老人家在臺北市
這兩天我要去探望他
但這拄著拐杖的老先生
像極了我的父親
他們在月台上相遇
彼此看了一眼
果然並不相識
離別了三十多年
我的母親手挽包袱
在月台上遇到
拄著拐杖的我的父親
彼此看了一眼
可憐竟相見不相識
非馬1936年生於臺灣臺中市,不久隨家人返回祖籍廣東潮陽,1948年再到臺灣,1961年到美國,迄今一直住在芝加哥。而他的雙親,至寫此詩時已經離散卅多年、一個住在臺灣臺北市區、一個住在廣東澄海縣城。顯然,他的家庭,又是時代悲劇民族悲劇的一個縮影——正如〈羅湖車站〉所揭示的深層含義。
非馬在羅湖車站看見一位老先生和一位老太太,像極了他的母親父親。這也許不過是他潛意識的幻覺。因為他多麼希望他們是他的父親母親,多麼希望他們能在同一個月台上相遇。但是,他立刻想到,他父母親即使真的相遇,彼此也只會視同陌路,失之交臂。全詩語言通俗淺顯,但意境卻非常深沉凝重;白描淡寫的詩藝相當傳統;亦幻亦真甚至荒誕的意象卻很現代。雖是寫一家平民百姓卅多年的離愁別恨,但是,誰又能認為詩人僅僅是表現自我一家的命運呢?詩人此時此刻所感受到的希望和失望、無奈和悲哀,顯然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而是代表了由於國家分裂而骨肉長期離散的千萬個家庭。這一幕以邊界的羅湖車站大舞台演出的悲劇,飽含著詩人真摯深沉的人道主義精神。
〈羅湖車站〉是廿世紀八十年代後期臺灣文壇興起的“探親文學”熱的先聲之作,堪稱為“探親文學”的序詩。而在寫作〈羅湖車站〉之前,於1977年,也就是非馬在剛剛跨過四十個如夢春秋之後,詩人更寫出曾被許多浪跡天涯的華夏遊子奉為抒吐鄉愁的經典之作的<醉漢>:
把短短的直巷
走成一條
曲折
迴蕩的
萬里愁腸
左一腳
十年
右一腳
十年
母親啊
我正努力
向您
走
來
此詩把醉態十足的寫實與鄉愁無限的寫意巧妙地結合起來。左一腳十年,右一腳十年,這個借酒澆愁的遊子,離家門近時卻寸步難進。“短短”的巷子,竟然有“萬里”愁腸的心酸。“巷子”與“愁腸”的比照,把走近門口將要與親人相見的一段歷程強化了。詩末尾的一字一句,更暗示了步履的艱難,以及路程的遙遠和時間的流逝。這種近鄉情怯的醉態,極為令人黯然神傷。
非馬特能致力於刻求表象以外的意境。因此,一條巷子竟是萬里愁腸,一腳竟然十年,這是超現實的非寫實,但又比寫實還寫實。人們不禁對這首詩作多重意義的理解。所謂“醉漢”,可以是真正醉酒後酒入愁腸而懷鄉,也可以是表現因思鄉情切以致迷離恍惚,如醉如痴;其醉態可以是實寫走近家門的一種心情的比喻,也可以是表現醉漢般恍惚迷離的幻覺。許多人更是把〈醉漢〉看成一首尋根詩,詩中的“母親”象徵詩人魂一夕而九逝的祖國。這樣,“醉漢”還不僅僅是一般的流落異鄉的遊子,這還只不過是事物的表象,而這表象的內涵是——抒發和反思民族分裂的鄉愁。人們閱讀此詩時,會情不自禁地聯想起當時已經冰封了幾十年的臺灣海峽。這“左一腳/十年/右一腳/十年”的漫長艱難的步伐,正是動蕩年代的象徵性意象,蘊含著咫尺天涯的悲劇意識。而“我正努力向您走來”,是對母親的傾訴,也是對祖國的傾訴,傾訴抑制悲情扣開鄉關的努力,傾訴擺脫內心困境和外界現實阻擾的曲折的努力,傾訴時代的悲劇,人生的悲劇……
非馬一次回答提問的時候,說出一段意味深沉的話(〈答問〉,劉強著《非馬詩創造》,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年五月):
寫詩是為了尋根,生活的根,感情的根,家庭和民族的根,宇宙的根,生命的根。寫成〈醉漢〉後,彷彿有一條粗壯卻溫柔的根,遠遠地向我伸了過來。握著它,我舒暢地哭了。
〈醉漢〉這首僅僅只有四十個字的小詩,正是詩人灑下的一枕懷鄉夢國的清淚,這首經典式作品的每一個字,都具有金石般的分量。甚至可以說,它的意境和象徵,堪比一部史詩,一部長篇巨著。它把具體的現實性與嚴酷的歷史感深刻地統一起來,那種酸甜苦辣的心頭滋味,那種迴腸蕩氣,直達心靈,震撼心靈。
非馬寫作〈羅湖車站〉時,羅湖車站幾乎是中國大陸與外部世界、特別是與西方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接觸的僅有的交匯點,而事實上那時海峽兩岸的親人還得不到從這裡進出的“來去自由”。至於寫〈醉漢〉時,中國大陸“四人幫”剛剛倒台,開放改革的國策更是連影都沒有。今天,三四十年過去,中國大陸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可憐竟相見不相識”的現象可能沒有了——該相見的大都早就相見了,或者來不及相見早就去世了。但是,中華民族的悲劇遠未結束。“把短短的直巷/走成一條/曲折/迴蕩的/萬里愁腸”這種悲劇還在繼續。大陸背景的澳華作家楊恆均曾在北京當時的《天益網》上發表了一篇他於2007年十二月廿九日在臺灣臺中市親身實地考察後寫就的隨筆,標題是〈臺灣海峽為什麼越來越寬?〉這篇引起網民熱烈討論的文章對臺海兩岸至今還是——從深層意識來說或者更是——極其隔膜的嚴重狀況感慨萬千。因此,即使今天,相信每一位吟哦非馬〈醉漢〉和〈羅湖車站〉等詩作的人,還會禁不住低迴反思,感嘆不已。
三
民族苦難的根源何在?非馬的探問
黃河與中華民族緊密相聯繫。這條古老的大河承載著華夏歷史,也見證著中國人的苦難,甚至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的血淚和苦難匯聚的河。我注意到,非馬作了兩首〈黃河〉。
前一首溯“源”,作於1983年四月五日,最早於當年七月廿二日發表在臺北的《聯合副刊》:
溯
挾泥沙而來的
滾滾濁流
你會找到
地理書上說
青海巴顏喀喇山
但根據歷史書上
血跡斑斑的記載
這千年難得一清的河
其實源自
億萬個
苦難泛濫
人類深沉的
眼穴
此詩兩節,第一節運用極為寫實的手法描繪了黃河挾泥沙滾滾而來的氣魄,但在第二節詩結尾處卻用超現實的幻覺手法,把黃河的源頭寫成億萬個人類苦難泛濫的眼穴。地理書上的“源”和歷史書上的“源”,兩相比較,得出詩人的獨特發現——發現被俗常目光埋葬了的詩意。這樣,如論者指出,就跳出了“實象”的河,不落於一般寫黃河的舊窠臼,甚至包括習慣的“母親”意象,而進入了“靈”的層次:人類苦難歷史之“河”,出“虛”,肉眼不可見。原來,“苦難”之“源”,如“眼穴”意象所喻示,是“人為”的,是歷史上各種腐朽罪惡的專制制度造成的。
後一首析“流”,反而是先作的,1975年一月十二日寫成,最早發表在《笠》詩刊第七十期:
把
一個苦難
兩個苦難
百十個苦難
億萬個苦難
一古腦兒傾入
這古老的河
讓它渾濁
讓它泛濫
讓它在午夜與黎明間
遼闊的枕面版圖上
改道又改道
改道又改道
詩人不直接寫從黃河中看到了苦難,而是“把”苦難“傾入”,突出了苦難的積壓,突出表明了這條河自古以來就是一條承受苦難的河。“苦難”的量化實際上是對中國人數的量化。從“一個苦難”到“億萬個苦難”逐漸遞增,表現了從個人到民族,從時代到歷史苦難的普遍和久遠。“苦難”的反復重疊幾乎就像一座在成長的大山壓過來,最後發展成一個種族的記憶,讓全世界的華人都會聯想起母親河的災難,災難的場面與情緒:戰爭烽火、黃水患難、流離失所、無窮哀怨……等等。
第二節則突出剖析“苦難”之“流”。這裡用了三次“讓”這個詞,就像上節“把”苦難“傾入”一樣獲得同樣的效果。詩末“改道又改道/改道又改道”的意象迭加最為使人震撼。這不僅僅在於抒發情感,而是要喚起讀者強烈關注問題的嚴重性。自以為是的人類把追求表面的發展看為第一要務,一直在糟蹋黃河一直在糟蹋自己的居住環境。這個迭加的意象,緊扣歷史和現實。對“苦難”實行“改道”的苦難,只是使“苦難”一再加碼,而“改道”卻不改其“轍”,只是重複歷史的回頭路。真是令人深思!
兩首〈黃河〉,是大氣深沉內涵豐富的詩章,具有雄性的美學特徵,具有厚重的時代感和歷史感。非馬在1982年還寫了一首題為〈龍〉的詩,外表看來和〈黃河〉很不同,但我發現其思想內涵是共通的:
沒有人見過
真的龍顏
即使
恕卿無罪
抬起頭來
但在高聳的屋脊
人們塑造龍的形象
繪聲繪影
連幾根鬍鬚
都不放過
非馬這首〈龍〉,是一首小詩,僅有十行共四十九個漢字,但它顯示了非馬詩作強烈的社會性,而且別具一格,甚具深意。如論者所言,詩一開頭,詩人便以突兀峭拔的否定語式將龍這一千古神物推上了曝光台,這種開門見山式的表達,如一把利劍,一下子戳穿了東方文化尤其是華夏文化的神秘面孔。的確,只活在古老的傳說之中的“龍”,有誰見過它的真容呢?即使是“恕卿無罪”的所謂真龍天子,也只是古代和現代的迷信而已。然而,構成強烈的反諷的是,人們卻偏偏四處塑造龍的“光輝”而且具有威嚇性的形象,連“幾根鬍鬚都不放過”,就像世人創造“神”然後對其頂禮膜拜,中國人也創造“龍”以作為頂禮膜拜的神物。這不就是意識形態上的異化嗎?今天“龍”已成為中華民族的尊貴的圖騰。雖然“龍”在中華民族的傳統心理積澱中具有多重象徵意義,但誰能否認,“龍”最重要是象徵權力、專制、絕對命令——龍是天上的權威,自命的真理,高高在上。如果說古老的華夏歷史最初有一個自由的狼羊對立而又共處的時代,那麼,後來就進人了龍愚弄、統治、奴役羊的大一統時代。非馬這首詩,如一聲洪亮的警鐘,將人們從以“龍”為內核的那種負面傳統文化所衍生的虛妄與自傲中震醒過來,讓人彷彿覺得上下五千年的歷史都在震顫。詩人在這裡賦予詩的意象以民主與科學的哲理思考的內涵,對迷信和愚昧予以鞭撻,毫無疑問具有值得稱讚的時代精神和當代意義。
一般共識是,權力異化是當今中國社會最大的毒瘤,而且其毒素已經滲透到整個社會肌體的基層細胞和神經末梢了。像“權力私有化”、“權力商品化”、“權力特殊化”、“權力家長化”,這些並不是單個出現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促進、相互影響。以國家機器作後盾的權力異化和泛濫,後果令人震悚。貧富懸殊,貪污腐敗,言論鉗制,定於一尊,成了今天中國令人觸目驚心的社會現象,使整個社會呈現畸形發展。因此,有人提出,要根治腐敗,就必須認真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公共權力的異化,尤其是要解決“一把手”的權力異化。當然,這首先就要像非馬在〈龍〉一詩中所要警示的——要克服“龍”崇拜這種思想領域的異化。
許多人也許不知道,近年來,非馬雖然年事漸高,但仍然思維清晰,心明眼亮,對世事洞察秋毫,保持高度的批判力。2016年底,我在電郵中對他說,這一年對美國人來說可能是最不尋常的一年,明年大家會有些東西看了。這一年又是中國文革五十週年。我傳給他我主編的文集《文革五十年祭》。我為此書寫了一個“代序”,長達三萬字。非馬說這是他讀過的最長的序了,作為讀後感,他附上他最近寫過的有關毛澤東的幾首短詩,謙虛地說,“比較起來顯得蒼白無力”,“博您一笑,或一哭”。我說,短有短的好,你精煉的短詩,一針見血,讀後難忘。這首題為題為“獨家風景”:
把所有的
陵墓古跡文物文化
道德信仰人倫人性
統統搗毀之後
他終於心安
體更安
大喇喇躺在天安門廣場上
獨佔風光
這首題為“毛澤東紀念堂”:
寄存了所有的身外物
以及喧嘩
便紛紛攀附
長龍的尾巴
等著瞻仰
死神的真面目
我不得不佩服
化裝的巧妙
在每張漠漠的臉上
竟看不出
絲毫的驚訝
(或會心的微笑)
對著大門口
冷冷站立的
一對牌示
“請勿吐痰”
這首題為“微雨中登天安門”:
從這樣的高度看下去
原來你們是如此的渺小
螻蟻都不如
要不是天空陰沉著臉
還有那些便衣警衛耽耽虎視
說不定我也會高舉雙臂
豪情萬丈地大聲宣布
今天
我——
站起來了
一首詩歌的價值最終是要從它達到的精神高度和豐富的內涵來體現,否則,語言再新技巧再高也沒有力量。非馬不僅繼承中國知識分子的以民族憂患意識為核心的愛國主義精神,也繼承西方文化中的批判精神傳統。他以思想家的睿智和詩人的敏銳橫空出世,在思維方式和審美取向方面可謂獨領風騷,其思想價值藝術價值肯定不是時間可以抹去的。
四
弘揚普世價值 承傳終極關懷
行文至此,意猶未盡,我覺得我還可以再說說。
1978年,非馬從美返臺,在一次談及“理想中的好詩”時,明確指出:“對人類有廣泛的同情心和愛心,是我理想中好詩的首要條件……對一首詩我們首先要問,它的歷史地位如何?它替人類文化傳統增添了什麼?其次,它想表達的是健康積極的感情呢?還是個人情緒的宣洩?對象是大多數人呢?還是少數的幾個‘貴族’?”(莫渝,〈詩人非馬訪問記〉,《臺灣日報》副刊,1978年九月一日;《笠》詩刊第89期,1979年二月十五日)
作為一個人道主義詩人,非馬通過自己的作品建立了一個值得稱頌的藝術世界,這是一個富於正義、充滿人性的世界。
讓我們讀讀他寫“給瀕死的索馬利亞小孩”的〈生與死之歌〉:
在斷氣之前
他只希望
能最後一次
吹脹
垂在他母親胸前
那兩個乾癟的
氣球
讓它們飛上
五彩繽紛的天空
慶祝他的生日
慶祝他的死日
這首寫於1992年八月十五日、同年首先發表在香港《明報月刊》十月號和臺北十月廿七日《人間副刊》的詩,是一篇催人淚下的作品。我們經常在電視上看到,饑荒中的非洲兒童,那種眼大無神,形銷骨立的畫面,使人觸目驚心,不忍卒睹。非馬的這首詩,正是以這些活生生的現實為主題。這個索馬利小孩臨死前,渴望母親的乳房能脹滿奶水,甚至飽滿得像要騰空高飛的氣球。把乳房比作氣球,真是奇思妙語,卻符合小孩天真的幻想,表現了他對果腹,對生存的強烈渴望。詩最後用“生日”和“死日”對襯,從而把悲劇氣氛推向高潮,成為撼動讀者情感的巨大的衝擊波。詩人寫出一個天真卻是瀕死的小生命,那麼渴望美好卻又那麼幼小、孱弱,那麼短暫的生命,充分顯示了對在死亡線上掙扎的非洲兒童的深切同情,深刻地實踐了自己對詩歌的“社會性”的承諾。
由於地理條件的惡劣,再加上人為的因素,特別是統治者貪婪腐敗又治國無能的因素,非洲一些國家的人民長期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戰亂頻仍,饑饉連年,哀鴻遍野,滿目瘡痍。人們說,非洲是“被上帝遺忘”的地方,那麼,像是美國,這個“上帝給以青睞”的地方,就沒有悲傷嗎?居住在這個國家的非馬,以他的詩歌明確告訴我們,悲劇到處都會發生。
這是他寫於1985年的〈越戰紀念碑〉:
一截大理石牆
二十六個字母
便把這麼多年青的名字
嵌入歷史
萬人塚中
一個踽踽獨行的老嫗
終於找到了
她的愛子
此刻她正緊閉雙眼
用顫悠悠的手指
沿著他冰冷的額頭
找那致命的傷口
這是一個具體的場景:一位老婦在碑石上尋覓無可尋覓的愛子,她把冰冷的大理石幻覺成愛子的“冰冷的額頭”,而且硬不死心地要找出“那致命的傷口”。這種哀傷臻於極頂時的痴心妄想雖然無言可是卻發散出強大的控訴力量!正如論者說,這首詩所突現的心態情感極富現代人的時代特徵,又由這時代特徵而在歷史進行中獲得了時空縱深感,具有穿越時空的魅力。這首具有“現代感”與“歷史感”雙重性質的詩章,統領大時代的風雨硝煙,統領人類歷史發展的縮影,統領無數親情的悲歌。
如果說,非馬對母國文化的無限依戀凝成他創作心理上的民族情結,那麼這種對全人類的關切熱愛意識便是他的“人類情結”。他的詩中,常常出現意蘊的層層遞散與深化,由一己、一家而推及全民族以至全人類,這不但是民族情結的漾散、擴張,而且是它的昇華與入化。
對於人類,為禍之烈,莫過於戰爭了。詩人對於人間這個散佈仇恨、自相殘殺的魔鬼深惡痛絕。〈越戰紀念碑〉是對於“人類文明一種自身反省”的卓越貢獻。它給人以強烈的震撼,讓人們充分認識到戰爭的殘酷。它像警鐘一樣將告誡懸掛在人類的頭頂之上:遠離戰爭,不要以任何藉口去觸摸戰爭。
關於那場戰爭的起因,紀念碑這樣告訴後人:“中國已經成為共產主義國家,不能再讓越南成為共產主義國家。”可是,後來,又發生了另一場越南戰爭,卻在早先的“同志加兄弟”——中國和越南這兩個共產主義國家之間發生。歷史的詭譎,真需要人們反復思考。
然而,縱然經歷過這麼多的悲劇,世人未必都清醒。
非馬以〈電視〉熒光幕隱喻人類奇詭並可悲可嘆的記憶──即使對最受咀咒的戰爭:
一個手指頭
輕輕便能關掉的
世界
卻關不掉
逐漸暗淡的熒光幕上
一粒仇恨的火種
驟然引發
熊熊的戰火
燃過中東
燃過越南
燃過每一張
焦灼的臉
熒光幕上一粒小小的熒光,會逐漸展現世界,而一粒“仇恨”的火種,也會“驟然引發熊熊的戰火”。戰火會燃至世界任何一個地域,這些會不斷地改變,但只有一種是不受膚色、種族、國籍的限制而改變的,那就是“每一張”受難的焦灼的臉。這是“關不掉”的真相。但是有些人就是想關掉,像關掉電視機一樣,動用一個手指頭,輕輕便把“世界”關掉。事實就這麼殘酷。人類就這麼愚蠢。〈電視〉這首詩的諷喻,表達了詩人對人類社會的關切和批判。
中華民族五千年的傳統文化倡導“終極關懷”。終極關懷是對人存在的根本關懷,同時也體現了對人的現實關懷。它與自由、民主、博愛、科學等當今普世價值是相通的,都是超越一切民族、語言、膚色的差異,超越一切宗教、信仰、思想、文化和社會體制的差異,超越一切時代和地區的差異。我們從非馬的詩章中,也分明看到中華文化的終極關懷的承傳與當今普世價值的弘揚。
(本文各章節曾於2008年三月各自單獨在《澳華新文苑》發表,現稿修改於2018年九月十一日,“九一一”,一個當今世界不能忘卻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