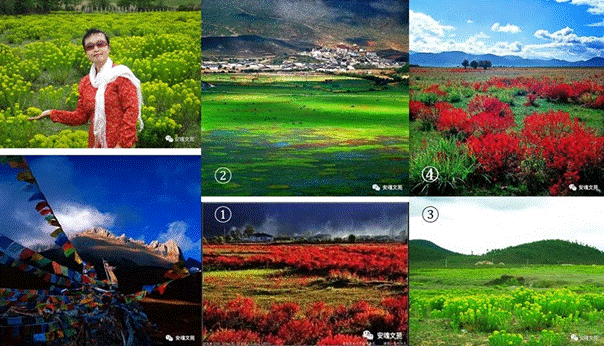


香格里拉
✦
狼毒花
不到香格里拉,還真不知道世上的花兒,竟有這種另類的命名:凶險,卻誘惑。①
朦朧四圍,是晨霧中尚未醒來的雪山。腳底曠野,是前世沉默至今的海底。小車打著哈欠,駛入早晨的靜謐。②
忽然,一大片翠綠頂著鵝黃,猶如沉悶中撲面而來的朗朗笑聲,撞直了車內所有人的坐相——③
那似花非花的尤物,在小中甸通往洋塘曲的路上,一蓬蓬,手挽著手,聚在山腳高聲合唱。好大的陣勢!彷彿青春無所忌憚的狂歡;喧鬧中,又透著些許生死由命的……安詳?
(香格里拉八月的狼毒花)④
時逢春夏之交,遠山還蓋著積雪,人在夜裡也要蓋著棉被。寒冷凄清中,飛來隆重的一筆——似乎只要有一塊朝陽的平地,就會有一大片野性張揚的狼毒花海,慷慨地為季節鋪墊暖意。
已經落草於五千多米的高海拔,高高在上的她又亮出更野的名字作鎧甲,是在拒絕某種親近嗎?
藏族導遊不時告誡大家:不要折斷花兒,小心有毒,連犛牛都不敢吃的!
看不出,這纖柔的小生靈還挺有個性!據說在這乾旱高寒的地方,她的生命力之所以勝出其他草本植物,全憑有著強大吸水功能的長長根系。想像她細細的根鬚,竭盡全力在板硬的砂石地下艱難伸展,才把那矮矮的小身子挺立在地上。⑤
千萬年了,她自說自話地熱烈著,自足自洽地孤獨著。在這遠離人群甚不宜居之處,她擎舉起弱小者倔強的意志,笑傲天涯。
無論陽光下,還是風雨中,都有萬千風情,足夠她搖曳,純真又妖嬈。她為長年枯寂的高原,捧出多彩的韻律……
說起她的履歷,簡短,卻不簡單。⑥
每年到了五月,她就把燦黃的笑臉,少女懷春般漸次鋪展到春天的深處。而到了盛夏七八月,花事將另起一章:她先從脖頸,慢慢紅遍臉龐,紅得晶瑩又恣肆。夕陽下,紅瑪瑙隨風掀動燃燒的海浪,吸引來無數遊人。熟透了的情色,從不屑於隱瞞——
她來到世上,彷彿就是為了證明:怎樣才能活得率性、激昂。雖然命運如同季風一樣倉促,但她懂得:傾情出演自己,然後謝幕,是另一種自愛和堅強。
就這樣,她用匆匆兩季,簡單三色——從綠到黃,從黃到紅,體溫一次比一次高,詩意一次比一次濃。精練、又響亮地過完了人類幾輩子也難得的絢麗與豪爽。
捧著比別處更藍的天,比別的花兒更高的燒,比世間女人更大的心——小女子從一落生,就選擇了今世的特立獨行。⑦
她首先對自己痛下狠手——當別的花兒尚在名字裡,努力清秀或端莊,努力良家婦女時,她卻不惜自我毀容。為拒絕成為獵物或食品,她一開始,就在芳名裡廢了媚功——她才不屑於功夫在詩外呢。不屑於小姐、小資、小家碧玉。她果斷地廢了自己成為被把玩的寵物、被潛規則的可能……⑦
直至,廢了芳名——她成為披著狼皮的羊。
現如今,在狼都成了圖騰,赤裸裸,不稀罕、也不需要穿羊皮的時候;在羊都懂得穿上時裝去公關的時候,她的叛逆,是不是有點冒傻氣?
沒成想,她大不吝地穿上惡名,卻無意中“惡”成了風景,成為旅行社的“招牌菜”
;為貧困的西部,成就了旅遊業的GDP。⑨
然而更多的時候,世事艱難。
我忽然有了另一種猜想:也許為對付辣手摧花,免遭荼毒,她才讓自己先服了毒。以帶毒之身闖蕩江湖,也許就能刀槍不入?在滿世界的叢林法則面前,這不過是弱小者小小的人生策略吧?⑩
說到帶毒的同族姐妹,她應該和罌粟花有一比。可比起妖媚得有些邪性、勾引人類下地獄的罌粟,她無疑更坦蕩、更簡潔、更率真,更像是陽光下的純情少女……
面對這個爭名奪利,卻又名不符實的虛偽世界,她要把不屑,進行到底!要讓聲名之累,早早自盡於——她的自信!
她因而更加天高地闊,無牽無掛了。無論何時,她的站立都成為一種昭示:再惡劣的環境也壓不住生命的飛揚。無論何地與她相遇,旅人疲憊的目光頓時鏗鏘;高原粗礪的風
,也委婉了腰身……⑪
今夜,我一遍遍翻看著與她的合影。捧著相冊,像捧著一個棘手的誘惑……我想像著自己如若是個男人,對她是否又愛又怕,又怕又愛?⑫
我進而猜想著:在人慾橫流、越發輕薄的世風下,她把自己包裹在如此酷厲的名字裡
,除了以示決絕,是不是還想著,與這個毒奶粉、毒白酒、毒豬肉、毒膠囊、毒心腸的人間PK一下——以毒攻毒,負負得正?
哦,我也許不太明白花兒的心思和理想……
我最終需要明白的是:如何才能活得熱烈昂揚,又滿不在乎;敢於浪擲虛名,更敢於命名於另冊——像這高處自在且自持的花兒一樣?⑬
(香格里拉小中甸六月的狼毒花)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