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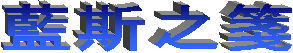
|
風笛不該寂寞,我不該不回來,約會幾時? 斯箋不是箋,箋人不是我,你也不是接箋的人 我是趕馬回來那漢子,等你,明晚的月光 異日吾若再翩臨,當搖當歸酒一瓶吾等共醉之
1973.07.04 今天借給你一本散文集《也斯:灰鴿早晨的話》,這是一本讀起來文調清淡而過後感覺沉重的書;也是一本現代人心情與意識觸覺的書,不容錯過。 再也想不出有甚麼可說了──在這戰爭的年代。 你以為我們「風笛」需要一箇有藝術修養的人嗎?我想再把「風笛」的方向拓展,集文學與藝術於一爐,當然還有舞蹈、音樂、繪畫、設計、翻譯等等。你認識那些有天才的人嗎?中國人為甚麼不喜歡團結起所有的力量與智慧?我們這一代為甚麼不把很好的心靈交出來?中國的搖滾樂幾時才敲打敲打? 要說的話還是很多很多,但我們要說出甚麼呢?我們這一代的心靈要如何去組合呢?
1973.07.15 今晚的月光該好圓好圓的,誰去踏月呢? 《風笛詩展之三》的稿心水星期六才拿來,所以編好後趕不及約定時間拿給你,也以為你今天要來的。好想著笛人們,也有太多話要說的,但提起筆,腦袋悶塞得利害,情思斷成了連串不嚮的風鈴,真的不嚮呵!敲打小樓的鞋音也不嚮了,杳杳。 首先歡迎冬夢成為笛人之十三。十三號碼不是中國的忌諱,而我們很中國。 我們也歡迎異軍喜獲小乖,為風笛之新一代也。 風笛應不應該擴大?還是任之我們這一代最好的心靈各獨黯然耕耘?當然我們應該有系統的計劃,如同是為現代文學藝術而搖旗的,那麼我們的組合就不會雜亂,大家有一個確定的認同,而且怎樣尋求其中的和諧及共鳴,才是我們要走的路。例如舞蹈,這當然是一種動作的視覺的表現。音樂則是在聽覺和心靈相互牽動的線譜。而繪畫的觸覺是要如何在國畫和西洋畫之間尋求一種契合的呈現。這些都是和文學有一個共通點,在時間與空間的現代意識謀取更寬頻的表現;我之所以欲連結其他人才各異藝術類型揮灑的靈覺中能夠得到更實質的互動的收益,我們所需要的就是在過程中思考將現代性所欲表達的境界呈剖出來。這是我一個構思,我知道,實行起來是非常艱難的。 所以我又想起我們最好的心靈在哪裡?
1973.08.18 本就想不寫斯箋之,但想念得緊哪!──迷湯。 相信吾的一篇小說出籠當不會給你意外,就想聽你一張金口,給吾一帖良藥,究竟吾之小說有無得救?若金口不開我非罵不可也,最少一句他媽的是免不掉的! 話說冬夢小子莫非管管起來了?希望下回能還我河山,再描上兩道清眉。話說冬夢小子竟自己起來,那就不同,至少是我認識和喜歡的,而且一日比一日的美麗。 好像言不達意的,若明晚(拜日)不雨不約會女生,請登南樓,吾已約好心水齊來。 風笛之四之五如之何?異軍之稿如何之?
1973.08.31 昨晚真過癮而又不夠過癮,畢竟夜太短,話太長,畢竟昨夜來吃盅中國茶的不是你,而是那片雨後的月光,李白在三峽的那邊。 風笛之六請搜集李刀飛在南方未發表的稿專成一輯,以懷念他不幸遭遇之情;思之憂然,憂然思之。 你借與我十五冊書,要死嘍,變作書呆子也不定。近日我構思一篇小說,要如何與詩、散文、劇、電影等化合,我稱之謂實驗小說,但懶得動筆,或許我在藝術文學各方面的修養還吸收不夠,這是我之悲哀也。另外《風笛散文專號》的你、異軍、黎啟鏗為甚麼還不出招?心水之招已等得不耐煩。
1973.11.09 信已悉,讀完,卻不見你飛揚的字跡,彷彿,你是月光下的騎士,不見雲煙、不見形象;彷彿一幽靈,來自夢中。 很美的笛十郎,很美的月光手札,很美的笛聲,相思不相思思相不思相又怎樣?總想起笛人們,並且歡迎笛十五郎(劉開賢)。 軍色匆匆,不詩不散文已久,意念裡,總有一份戚然。 附上一信,請代為覆,係為一陌生女子來信,名字凌煙,在成功日報似乎不時看到,你可留意?希望你與伊能長期通訊,若可能,笛十六妹留席以待亦行,我將來有機會才去信給伊也。 草蓆為桌,草此書信,草念你、心水、秋夢、李刀飛,以及其他笛人們;若有機會,吾等當再相聚。
1974.05.02 (捎給荷野乍臉的,不是月光手札。) 想給你寫信很久了,但我不想在行軍的野地上寫上我懷念的情感,而且想說的話也很多,但現在提筆,竟無言也。 問其他笛人們的好。 風笛寂不寂寞我不知道,但我實在寂寞,所以拼上命也只這麼兩首短而且不怎樣過癮的詩。莫怪。散文很想寫,而且很想寫很長很長的散文,時間不黑市,地點也不浪他媽的漫,心情更不能安靜下來。你說:莫怪。幾時再見笛人們之臉? 希望風笛能更風騷起來,希望除詩與散文外,其他專輯如評論、小說也能搞上,難處也很多,是不? 應該要再踢出李刀飛的水星之貌的評介出來。應該仙人掌平心而辛厲的評文來。應該心水的小說新風格滾出來。 風笛不應該寂寞。我不應該不回來。約會幾時? (藍斯。沒有信封的,我寫的也不是信。你讀的只是一片流雲。)
1974.05.16 遠方已朝面走來。你我莫非已在五月以及笛人們。就趕寫一頁散文酬應風笛專頁的風采。誰又在其中醉了。誰又過癮。最好仙人掌能客觀的長批短評起來。想起屈原。笛人又在何處問笛?我想又缺我笛音矣。我曾提及最近很想寫一頁長長的散文及一箇小說,卻因環境的動盪和心情如亂絮般而作罷。時代之。我又何必強說愁。何必年青。何必風騷。真的菊花茶幾時啤酒幾時笛人嬉春幾時該你該李刀飛該藍兮該劉開賢該誰幾時。問冬夢異地的好。問古弦上任的好。他媽的。做爸爸有乳而無乳水的滋味你嚐過未?再幾時。仙人掌幾時再聽到他小子一口漂亮的國語。若有信可投向孤家。藍斯。五月十六日六十三年的民國。藍斯。 附上的散文麻煩誰再重抄乙次,軍營重地原稿紙洛陽。藍斯。
1974.11.20 君自雲中來或並不,想我忘了;但有一些屬於敲打風笛的日子,非我所能忘的。遠在百幾里外,風更風雨更雨的營裡,怎樣也詩不出和散文不出的沾上一種置之死地的懶散。我穿上一件青衣,青衣穿上一件中國的靈魂,這是我還能詩還能散文的一種感覺,一種在深淵裏復活的感覺。 風笛好像在一些訊息中沉默了,誰都不相信風笛會成為一支枯寂而不能闇嚮的枝梗,我相信我們的笛手並非無能編奏屬民族性的樂曲,並非在等待,也並非在尋求按地置身的生活,而是在發現。是的,我們不甘於隨流,更不甘於嘩眾,「風風處,是該有笛。」這句話是藍兮說的。 風笛的《評論專號》居然發不出,(雖然仙人掌已答應趕寫一篇批評散文的作品)在評論方面我們太弱了,我想應該用另一種方法來「逼」出風笛的手們揮出一些聲音,就是我們把《評論專號》改為「筆談會」性質,出一個題目,讓大家像中學生寫作文那樣寫出數百或數千的字來,然後編集出輯。這意見陳燿祖以前曾提及過,我不過舊調重彈而已。你認為怎麼樣?你說你說。 還有我曾提及的《個人作品特輯》,是希望在風笛中選出一些有彈性而又能有新風格,並且以最近的作品為代表,可以以詩或散文或其他的類別為總輯;當然,他們的作品要很豐富的 (並非量而在質)。 青衣以來,我一直不箋了,更不箋長。斯箋不是箋,箋人不是我,你也不是接箋之人。搖窗一片,雲自雲外落,落下竟是一個你的名字輕輕,輕輕竟似不覺的雨;雨在誰的髮上?雨在誰的相思裏? 問好笛人們,都問好。
1974.11.25 我不是箋。我不是箋人。誰是?而──我更非帖。但你來是不來還是白不來?南樓好寂寞。最好趕及早早的月光。吾們再去風流再去卜運再笛郎數個。真的。我是趕馬回來那漢子,等你,明晚的月光。十一月廿五晚月光的藍斯。
1974.11.26 今夜心水將赴南樓。汝若來請急約三五笛人們共聚暢談之。並取李刀飛的《雲說給雲聽的》散文上期給吾瞧瞧可好?
1974.12.31 今夜若非春夜。請來南樓。南樓更非除夕。來是不來由你。
1975.01.04 別來無恙之。吾又匆匆過客,乍臉之姿幾時再?今夜窗下捎星也許不是我,莫非是藍斯?風笛何以無采色,連情詩專輯也無。幾時笛人才吹笛起來。 異日吾若再翩臨,當搖當歸酒一瓶吾等共醉之。
藍斯之箋 1975.1.21 成功日報《風笛書簡乙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