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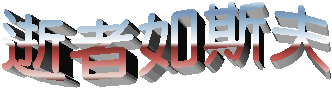
恭記我的老師卜寧(無名氏)先生
西元二千零二年十月十一日凌晨,一個意志力比鋼鐵還堅強,個性比頑石還頑固的文學名作家無名氏,在昏迷在醫院中十一天,終於被死神戰敗了。據送醫的房東宋先生說:「卜先生送醫院時還很清楚,他吐了滿身的血,幫助他換衣服時,他還一直說:「不好意思!你給弄髒了!」
送入急診室,他的右手在空中亂畫,已講不出話來,房東堂兄宋上校立即隨手掏出一隻筆給他,旁邊的護士小姐扯下一張空白病歷卡,卜老師握著筆寫下:「不要死!」,旁邊站著的宋先生立即大聲安慰他:「不會死!不會的! 您安心休養幾天就好了!」但是等到插上管子後,人就呈昏迷狀態,氣息微弱,面色臘黃,據醫生初步診斷:「嚴重失血,大小便亦失禁,肝脾腫脹硬化,內臟器官已經完全喪失功能了。」床前已掛上了病危牌子,送進加護病房。
十月五日,迴光反照,看到來人,微笑點頭。一位護士小姐看他一個人孤伶伶地躺在床上和死神掙扎、孤獨無助,要求來探視的輔仁大學的陸神父,幫忙替他做天主教洗禮,希望天主接受他,不要讓他死後靈魂無所依。
筆者從澳洲飛返台北,到醫院的太平間辦理出院手續,工作人員打開棺木;看到他睡在那兒,雙目緊閉,雖然已經過逝世了二十一天,皮膚一如活著時有彈性,只是有些冰涼。他熟睡了,我用手指輕觸他寬闊額頭,心想著這裏面隱藏著多少的文學的瑰寶和知識的寶藏啊!又用手指輕輕滑到了他的雙唇,耳畔響起那些風趣的聲音、機智幽默的話語、誠懇的訓誡,及開懷時張大了口,呵呵笑聲不斷。此時,愛說話的嘴巴早已合成一條細線,緊緊密閉,似與聲音斷絕了關係,我俯耳傾聽,多麼希望能再聽到他的一字或半語。也許他的口中仍然含著一句未及時吐出的話語!
記得他不論睡覺或休息,都是保持半警覺狀態,這是他半生飽受戰亂憂患,習慣於將精神繃緊在緊張狀態中。有時造訪老師時,他在二樓臥室假寐,耳朵重聽,就是敲破了鐵門,他也聽不到。好在他的床靠近窗戶,於是拜託他略微開一個手掌寬的窗縫,這樣子可以繞到通往三樓的樓梯,經過他的窗戶,一邊拍窗框、一邊喊:「老師起來了!」他「噢!」的一聲爬起來。此後他一直記得將窗戶留個縫。就在他十月二日吐血昏迷送醫那天,房東見他仍開著窗戶,問他晚上天涼了,怎麼不關上窗戶﹖
就連最後這幾年和小師母分居的日子中,早過八十歲的老人應該可以輕鬆頤養天年,和老友聚聚。但是他卻踏上了「老年歌德」的不歸路,把靈魂抵押給了梅菲斯特,為了還情債,頻頻出國演講、書法展覽和新書發表,連在電話中都形容自己忙亂得“像打仗”。
2001年夏天由宋北超世叔陪同訪羅馬、巴黎,參觀久已嚮往的羅馬文明和神話古蹟。老師在但丁雕像前嚎啕大哭,驚嚇了同行旅客,他們那裡能夠理解,他11歲時北伐吹起了號角,歷經抗戰、國共戰亂,事隔了一甲子,才挨到瞻仰著作但丁神曲的本人雕像,神曲中「最高的玫瑰」也就是表達追求“最高人性的真善美境界”,也是您心中膜拜的理想境界。不如說:「您們兩位是超越了時空的知音。」
您的頭髮潮濕而油膩,化妝師替你擦上了髮油以維持型態,這一頭濃密而烏黑的頭髮,一向是您所傲人的:「我從來不染髮、頭髮又濃又密!」,是的!您還欠我一把可以增添頭髮的神秘梳子,因為您除了注意自己的形象,同時也非常照顧四周的朋友,每次從大陸演講回來,必定帶許多土產、茶葉、泥娃娃等等稀奇珍寶送給友人,那種神奇的梳子早給一幫老友分光了,大概他們也想不到這個和您們相差三十歲的學生比他們更缺乏煩惱絲。
坐在殯葬車上,我雙手撫著棺蓋,遵照習俗;每過一橋必大聲呼喊:「老師過橋了!」或者:「卜爸過橋了!」,不知道您愛聽那一句,我都是兩種互相重複著。「天曉得!這是一個怎樣的懲罰﹖」就在您六月昏倒前幾天,還曾寫信回憶:「自己八十多歲的晚年尚能享受親子家庭的歡樂」,去爬皇帝山(殿),被我和印傭兩人架著登山,一路上不停地喊饒命:「我請你們吃石碇土雞和紅燒豆腐,好不好!」,結果只到皇帝殿階前,就打退堂鼓了,你明知道我惡作劇,故意考驗「那位視五仟仞華山為履平地的“印蒂” 是吧!」
好脾氣的您像溺愛孩子的父親由著我們捉弄而莫可奈何。動物園裏讓您返老還童;一定要看大猩猩、獅子、老虎,還說是好幾十年未進過動物園了。中午我們坐在涼亭內各據一方吃午餐,我買了涼麵,您怕肚子不好,不敢吃,只吃自己帶的葡萄乾土司。我津津有味地吃完一盒又一盒,一面咂咂嘴:「哇!又麻、又辣、又香、又涼,真好吃!」,您靜靜看著、欣賞著,然後說:「這個涼麵一定是你上中學時的最愛!」
憑著我高中生物的優異成績,一路上賣弄著:「什麼樹,什麼花」的名字,故意考問您,您不知道是裝傻還是真的不知道,只是搖頭。我樂得哈哈大笑「原來卜爸都是紙上談兵!」,
「什麼﹖」您耳背,往往每一句話都必須大聲重複兩句。
「我說,您在小說中大談天文、歷史、地理、生物、化學、藝術等的科學知識,原來都是從書中背來的!」
卜爸自幼天資聰慧異常,一目十行、過目不忘,博聞強記,17歲時放棄了高中畢業考,離家出走到北京自修大學課程,兩年內優異成績畢業俄語訓練班(免費),又閱讀了上千本文學書籍,並以同等學力考上北大英文系証明自己的能力,抗戰期間當記者就直接撰寫英文稿給報社,也曾翻譯一些精緻散文和詩投稿,在大陸期間寫信要求香港的二哥卜少夫先生寄歐美文學原文書籍。常鼓勵我學好英文,才能欣賞英美文學的精髓。
在茶餘飯後聊家常,讓我熟悉了您家中許多大小故事,及晚近結交的黃昏五友。雖然我想結識他們,卜爸卻認為時機未到。小心謹慎地保護著我,常說:「有些名作家“乾女兒” 滿街走,我是不隨便收的!」 有時拿著我的照片,點頭說:「真像!真像!」,又問我要年輕時照片,看他一副迷惘的神情,我答應回去找給他。等到後來收拾房間,才看到劉菁阿姨了,也就是離婚的第一位師母。人老了總是迷糊地回想往事,有時候又說:「以前我那個二轉子(俄國混血)女朋友都很聽我的話,不亂跑的!」其實每次返台都有一大堆的事要處理,但是老人家如果打電話找不到我,立即發脾氣:「你怎麼每天都亂跑!不在家﹖」同學和朋友都知道我忙,少打電話,只有他老先生比較空,老查我的行蹤,老媽代接過幾次電話,就問:「無名氏是誰﹖」
卜爸年輕時是愛看文藝片的,但是一個人就沒興致逛電影院了。我建議到華納威利戲院看「莎士比亞情史」,他一聽說是最崇拜的“莎士比亞”立刻答應前去,等到進了電影院才知道是限制級的,我只好向他說“抱歉自己的疏忽” ,他笑著說:「和馬福美結婚時朋友邀請他們去吃飯,飯後的餘興就是看“小片子”,哈哈哈!真的呀!我們寫作的人是百無禁忌!只要不要像有的作家為了寫作,真的下海做什麼特種職業就不值得了。」如此,我就放心了。
結果這部電影裏的莎士比亞像個嬉皮,一點也沒有想像中的風度翩翩的文學大師,也可以說電影拍得很生活化。男女主角演床戲時,當女主角脫掉上衣,他竟然大聲說:「唉喲!她還是處女呢!」一會兒男女肉搏激烈時,他竟然忘我地哇哇叫:「哎喲喲!哎喲喲! 這麼快! 比我的呼吸還快!」
「噓!...噓!」四周有人在抗議了。我不得不警告:「老師啊!你再哇哇叫,我不看了!等一會出場時亮燈,人家都要看我們什麼活寶了!」他才像小孩子一般乖乖不哼聲了。
有一天吃過午飯,老師突然想下午去植物園散步,在路上即提醒:「要從那個方向,那座大門進去!」我心想,植物園那麼大,有東、南、西、北四個門;從那邊進,進那個門,有什麼關係﹖不過,既然他老人家堅持,於是我們叫計程車司機開到西、南邊側門。下了車,只見他在大門口團團轉,口中唸唸有詞:「不對!不對!不是這個門!錯了!錯了!」,這時候車子已經開走了,他站在馬路上,伸手招另外的計程車。
我奇怪了,明明進去都是植物園,管他那個門呢﹖他著急了:「我要計程車繞繞看,才知道那個門才對!你怎麼說就是這個門!...你看看!這那裡是﹖」我忽然想起,卜爸想舊夢重溫,「當初他來台灣時,和小師母馬福美常常在園內散步,談情說愛。」他想重返園中拾回往事。我之特別提起這件事,是看到報導小師娘恨老師特別著書罵他;其實老師還很感念她,曾經在婚前義務替他抄寫稿子,並且還誇她聰明,琴藝好又唸了許多文學、哲學書籍。只可惜兩人年齡相差四十歲,老師又忙於寫作,無法常常陪她出遊,所以生活步調不一致,磨擦就多了,分手也是不得已,覺得很遺憾。畢竟紅袖添香、才子佳人的姻緣是可遇不可求的。
所以每當老師回憶起來,一生中真正給他甜美的婚姻生活,只有前妻劉菁。那位曾經被太師母收養的養女,他看著她長大,她對他愛慕景仰,兩人日久生情,太師母安排他們結成連理,甜蜜的十八年愛情生活。但是文化大革命時兩人被迫離婚。以後老師雖然到了台灣卻一直惦記著她,並且於九八年返鄉時,帶了禮物向她致謝,以前結婚時容忍他不工作,由她一人賺錢養家,孝順婆母,任勞任怨,讓他順利完成「無名書」後四卷等作品,這輩子對她的感激無以為報。
有人要奇怪為什麼1999年我會回台灣,而一住是三個月,原因是我患了腎結石,又常常腰痛,在紐西蘭醫藥雖然發達,但是住院排病床不易。另外就是我住的小城醫生少。卜爸是位敏感而神經質的人,加上他以前女友趙無華患過腎衰竭,於是立即叫我回台灣治療,他要替我安排一切住院及治療,因為沒有健保,都是私費,所以只要有空床位立即可住院,但是當時沒有空床位,叫我在家等電話,等了一天,我就煩悶極了,溜上街逛書店、看同學去了。
這期間,老師帶我去旁聽聯合文學發表會,爬皇帝殿山、看電影、上館子、淡水濱海餐廳看日落,植物園石橋上觀沉魚落花、動物園看獅子、指南宮西亭賞夕陽、政大西餐廳吃牛排,等等郊遊往事,至今仍歷歷在目。誠如他老人家在2002年四月十九日寫的:「回憶1999年的春天,你回來的那段日子..,真是恍如隔世」。 因為他以為這種溫馨的日子再也不會有了。
當遺體被送入火葬場時,撿骨師叫我們大聲叫喊死者的名字,這樣靈魂才會脫離肉身,免受烈火的焚燒。我大聲哭喊著:「火來了! 老師快跑!火來了! 老師快跑!」,我們活人聲嘶力竭地哭喊著,焚屍爐內烈火熊熊,轉瞬間肉身化為白骨灰燼。六張犁的火葬場在山谷下,焚化爐外搭建遮陽鐵棚,旁邊有紅瓦磚牆地藏王廟之間是一線狹窄天空,剛才的小雨已歇了,午後陽光斜斜射入,掃除了棚內的陰暗,不知道是否老天爺也在憐憫 - 一位當代文學巨擘臨走時卻如此悽涼、冷清。
過了一個小時,一切肉身化為灰燼,撿骨師叫我和卜凡及卜師叔幼子各撿一骨放入罈中。我表示想取一塊做紀念,他說:「如果屍骨不全靈魂是不能昇天堂的。」果真如此,我希望攜片白骨回家去,讓他老人家的靈魂,常住我家供養呢! 一個表面越是堅強的人,他的內心越是寂寞。
您說?永生在那裡?在天堂嗎? 一定要天人永隔才感受到生命的可貴,才能珍惜生命,珍惜仍停留在世間生存者的存在?
我不會和那位偉大的、高高在上的X帝之流做交易的。信祂得永生,人類渺小而短暫;我也不會愚蠢到和它相抗,卻只想好好珍惜自己所擁有的,雖然我曾經很荒謬地、殘酷地冷凍了一個可以珍惜,卻任其流逝的生命。
我跪在靈柩前,如錐心泣血,卻再也喚不回一位關愛我如生身之父的恩師。
如果真有上帝,讓它懲罰我吧! 我寧可待在地獄底下,衷心的懺悔還心安些!
後記: 先師遺像已置供桌左角,中間是菩薩,
右邊是外子祖先牌位,每月初一、十五點香祭拜。
俗子 於清明節前的哀思Mar.22,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