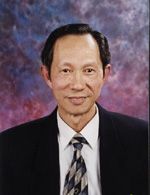|
|
語言天賦
墨爾本華埠當年的珍寶酒樓與京寶海鮮酒樓集團,是由印支背景幾位僑領合股經營。詹實先生是其中一位股東並任經理;每次去飲茶或宴會時,遇到詹老時必定尊稱詹叔、彼此傾談都用潮語。 未久、由蔡達明先生創辦“澳洲墨爾本潮州會館”,籌備創會前忽接詹叔來電話,邀請我出任“澳洲墨爾本潮州會館”的中文秘書?我在錯愕的剎那間自然反應回答:「詹叔、潮州會館成立是好事,但好像和我沒關係啊?」 老人家聽後生氣說:「你怎能這樣講?你是潮州才子、著名作家,敦聘你當潮州會秘書是最恰當的喲!」 「詹叔您誤會了,我不是潮州人啊!」 「你說什麼?不要數典忘祖啊⋯⋯」說完掛了電話。後來、我親自到珍寶酒樓、帶去一冊拙書、翻出書扉頁作者簡介展示,證明了我的祖籍是福建省廈門同安人士。詹老才消氣,驚訝的問我、為何潮語說得那麼地道? 我和兩位弟弟均在越南南方魚米之鄉蓄臻省(Soc Trang)誕生,當地的幾萬華裔,幾乎有九成半以上是潮籍人士,市面買賣的正宗越南小販也都學會潮語。先父經營的咖啡店鋪、聘請的會計、售貨員、廚子與佣人全是潮州人,先父母都以潮語交談。 因此當我牙牙學語時、潮州話就是我的母語了。世上那會有人講不好母語呢?如我冒認是潮州人,絕對不會有破綻。 先母患上思鄉病,帶著才兩歲的二弟和四歲的我回到閩南家鄉同安大路村;與童伴們玩耍,我成了他們口中的番仔,滿口令他們聽不懂的「番話」? 只會潮語的我自然也無法聽明鄉音了?小朋友學習能力強,幾個月後我已經能用閩南鄉音與童伴們溝通啦。 那一年鄉居歲月、大部份記憶都已隨流水,可卻讓我掌握了廈門鄉音,恢復回如假包換的閩南人士。當然、深印腦內的潮州話是揮之不去的語種。幸而這兩類語言、除了發音外、詞句應用區別不會太大,也就沒有衝突。 從閩南再回到南越、舉家遷移到華埠堤岸市(現改名胡志明市)、家住第五郡與第十一郡交界處的楊公澄街,面對的是法國殖民者的軍營。經常有法軍將罐頭等乾糧扔出營外、給我們這些好奇的小朋友們。 七歲上學、就讀一公里外的中正小學,開課時我變成了同學口中的「鄉下佬」?老師與同學們的講話、我竟完全聽不懂?幸而遇到潮籍同學張順祥,這位同學後來成了莫逆至交。惜天不假年、於我舉家逃難到達墨爾本後翌年,接到他長兄代覆的回函,告知噩耗。說被機車撞倒殞命,只享陽壽三十六歲,留下未到週齡的遺孤、這位在他週歲前見過一面的世侄,如今也已是三十餘歲的人,可惜茫茫人海無覓處。每一念及、不免惆悵無奈。 言歸正題、在中正小學讀了三年,附近新建樓高四層設備完善的花縣學校開始招生;我兄弟倆便轉校到新學校,一直就讀到小學畢業。在兩家學校完成小學課程,也完全學會了粵語,講起廣東話,新交的朋友絕不會知道我是閩南人。 當然、也因能說流利粵語,最終才順利追求到祖籍廣東南海的淑女婉冰為妻。 花縣學校沒有中學課程,要升初中時、先父指定我去福建中學報名;原因是福建人當然要在閩邦人士興建的學校讀書。面試的是蘇新標老師(歷任福中訓導主任、經已辭世),可憐我這個連半句國語(普通話)也不會的小學畢業生(中正與花縣學校全用粵語教學。)對著面試老師啞口無言? 萬幸的是因為入學申表格籍貫處、填上了“福建同安縣”,由於我是福建人,是“福中”招收新生規定屬於必收的對象,因此才能順利成為福中的學生。 這所南越當時知名的邦立名校,高峰期全校學生有九千餘人,僅略少於廣東人興辦的穗城學校(後改名越秀中學)。 機緣注定讓我就讀福中,不但在那三年初中歲月裏學會了字正腔圓的國語,(福中辦學先賢們高見,從小學至初中課程全部用國語教學。)也因教國文的馮小亭老師是一位紅樓夢迷,他對這部名著中大量詩詞背得滾瓜爛熟,投入時在課堂上便忘我的朗誦,我被馮老師朗誦詩詞時神采感動;開始買些文學著作課餘捧讀。 因為初始不懂國語的自卑,努力專心向學,期考都名列前茅,成為同學口中的書呆子。也因為文學的豐富內涵,不但用我的情詩打動了芳鄰淑女並娶得美人歸;後來且完成了當初志願、最終成為作家。 初中畢業後、本想前往臺灣升學,當時越戰正熾,為擴充兵源,華裔青年不准出國,留待從軍。我因不願充當美軍炮灰、遠走他鄉去到中區大叻山城農村、從義市郊外的新村執教,由張忠智神父創辦的聖文山小學開學時,陪著張神父到村內走訪村民,我為神父當翻譯、請求村民送子女到學校讀書。 本以為廣東話難不倒我?雖知當地村民講的是廣東與北越邊境少數民族的話,他們叫做「講蟻」?不是講螞蟻話,而是類似客家話的語種,後來聽學生們講,最終也學會了,才知道是欽廉話。欽廉才子眾多,如葉華英先賢、南越知名作家村夫與大僑領梁善吉(已辭世)、墨爾本僑領葉膺焜、洛杉磯樸魯詞長、沈昱明大國手、沈季夫、詩人黎啟鏗、英國夜心文友、多倫多夕夜、舊金山潮聲文友等不勝枚舉。 點算下我經已掌握了五種中國語言,那是潮州、福建、廣東、國語與欽廉話。 又輾轉去了中區芽莊市,在美軍物資中心沈昱明主任辦公廳當文書;幾十位職員泰半是越南軍隊中的將領及校級軍官的夫人們,幾乎都用越語交談。糟糕之至,我懂的那五類中國話竟全派不上用場,唯一能溝通的只是上司沈昱明。 那段文職工作中,又令我有機會學會了越南語,而且是北方腔調極其典雅的口音。後來回到華埠繼承父業,那些越南人經營的咖啡館輕易成了我的顧客,他們都以為我是北越移居的「同鄉」呢? 中年攜妻子和五名兒女奔向怒海,移居新鄉,到達墨爾本移民暫居中心,被送去學習六週的基本英語後,就到汽車工廠當車工了。每天放工後在廠門口買一份英文前鋒報,看新聞圖片,大標題逐字查字典;等晚上六時電視新聞報導時,再學習那些生字的發音。每天與工友們在休息時間或車間胡謅、學些破碎英語會話。 沒有上正式英語學堂,這些年與洋友人交往,普通會話都能應付,日常生活包括去見專科醫生等,也可傾談自如。全得益於強迫自己聆聽新聞報導,久而久之,算是略懂英語了。 朋友說我有語言天賦?非也非也,那是機緣巧合及人生遭遇有關,才不是真的有「語言天賦」呢!至今家族中,同輩與後輩尚沒有超越我而能講七種語言者。墨大畢業的長孫女會講國、粵、英、日等語言。在美國史丹福讀醫科的外孫李強能說英語、普通話、粵語與西班牙話四種。居德國的大侄明正、住瑞士的二侄明順與侄女如意、在廈門的小侄兒明志都會講英文、德語、普通話、粵語、閩南話等五種,算是很不錯啦。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八日於墨爾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