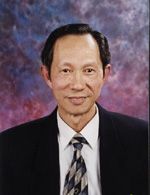|
|
小孩子通常都很怕理髮,也許從小帶來的陰影,使我對剪頭髮心生恐懼;每次非要等到髮長過耳,實在到了礙眼有損形象時,才踟躕再三的把頭顱交給那位希臘師傅耍弄,那二十分時鐘裏真有渡秒如日之感。 當理髮師手持利刀在我臉皮隨意輕移,我的神經不聽控制的緊張起來,肌肉僵硬,腦內飛駐著的都是刀片割切後血如泉湧的恐怖畫面,恨不得快快逃離現場。因此、刮鬍子、修臉皮等涉及用利刃的工夫,我幾乎能免則免,理髮師與我相熟後,他也樂得省事,反正工錢照收。 這陣子應酬少了,也沒注意髮長髮短,倒是老妻對我參差不齊的亂髮不以為然,讓她嘮叨多次後,才勉強去商場內重新裝修過的美容院。 在小鎮定居了二十多年,左鄰右里的街坊也早已認識,見面打個招呼是常有的事,但同時在理髮廊內踫面,卻還是第一次。 大衛五十開外的人,身材適中,略為發福,挺個微凸的啤酒肚,眼睛湛藍有光,一口英語還有濃濃的意大利鄉音。人頗熱情,喜歡澳洲足球,球季時不論在何處遇到,必被他拉著手口沬橫飛的大談各隊球技;沒完沒了的三五分鐘後,往往還好心的給我貼示,要我下注,除了感謝他的好意,我還真怕和他遇上呢。 但在什麼地方踫上這位住近我家橫街中段的大衛,我都不覺意外,可是竟然是在髮廊內,郤讓我覺得不可思議。我們居然同時坐在鄰椅,他的理髮師是位女士,我因為是希臘師傅的熟客,所以都由他一手來把弄修理我的頭頂。 有好幾次、明知失禮我也真忍不住爭取輕輕移動頭臉,偷偷望向大衛,只見他安靜的合起眼,任由小姐為他修剪,那位女師傅真能耐,一絲不苟的又是電剪又是剪刀,我的好奇心是犯上了,變得彷彿窺人隱私一般。 由於我的不合作,經常要給希臘師傅調整我的頭顱;以至同時理髮,鄰座的已完成了。往日只花大約二十分鐘,這次卻多了幾分鐘之久,但因為我是老主顧,希臘師傅也隨和極了,一點也沒有表現不耐。 大衛自然比我先離開,笑嘻嘻的對我說再見,從鏡面反映中我回應了一句: 「 Bye Bye !」 見到他的頭和理髮前根本沒絲毫分別,同樣的油亮光滑,實在百思難解?大衛整個禿光了的頭顱,寸毛不生的頭頂為何還要費時再花十六元來「理髮」? 在結帳時,我問希臘師傅這個難明的問題,他故作神秘傾身輕聲的說: 「禿光了的頭、毛髮再難生長,金錢買不回失去的頭髮,所以他常來此享受理髮的滋味啊!」 年過半百,一向視理髮為受罪的我,在希臘師傅微笑的話中,總算明白,原來理髮也是難得的一種享受。 走在回程的路上,想著大衛在「理髮」過程滿足的神情,我才知道自己身在福中竟不知是福,我還保有三千烏絲,多捧啊、、、、、、 (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於無相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