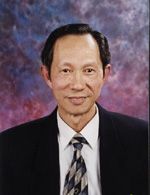|
|
春香湖的漣漪
週未午夜忽傳驚夢鈴聲,衝出睡房抓起話筒,心中嘀咕著不知何方冒失鬼擾我清夢?竟是長途電話,對方問明我就是他要傾談的對象,語聲興奮;滔滔不絕講了不少陳年舊事,在半醒迷糊中仍然無法令我憶起他是誰? 濃濃睡蟲在腦內咬著、催促我快快返回眠床,幾乎當我放下電話的剎那,萬里外傳入耳膜最後一句話是:「你難道也忘了珍姐嗎?」使我宛如沉睡不醒的植物人,驟然受雷轟震撼而悠然轉醒。 語音寂滅、線竟中斷了,他究竟是何方故知呢?不報姓名又如何能讓我僅憑聲音猜出是誰?但珍姐當然不會忘掉,躺回席夢思溫暖的被窩裏,再難入眠;前塵往事如影畫在腦內顯現翻騰,將三十餘年前的歲月帶回眼簾…… 越戰時為了逃避充當美軍的炮灰,我改名換姓,辭別了新婚未久的妻子,隻身前往距離西貢城三百公里外的山城大叻市( Da Lat )。這個海拔二千多公尺的南越桃花源觀光勝地,四季如秋;市內到處是歐洲風格的建築物,是當年法殖民地高官們留下物業。狹窄石路兩旁都栽滿了櫻花樹,每年初春時分滿城花海,粉紅色的花瓣將浪漫洒遍遊子身心。站於櫻花樹下嗅著幽幽醉人花香,宛似我也幻化成朵朵花蕊。 過往行人莫不臉露笑顏,無人擔心山城外燃燒正熾的戰火;雖然在寒冷深夜往往會被美軍B52轟炸機地氈式投彈時的巨響震蕩著神經,人們竟當它是催眠曲。平日往還絕口不提,好像只要講起,戰爭就會突然焚燒蔓延過來。 我寄居在城中心的潘廷逢大道中段、那座獨一無二的法式豪華別墅內;別墅後方是座小教堂,由臺灣來的張忠智神父住持。這位飽學的張神父除了拉丁文、英語和國語外,卻不懂廣東話和越南話。而當地的華裔教友們大多只會廣東話,我因此成了張神父的臨時翻譯員。經常隨他到處探訪散居山城郊區的勞苦大眾。 神父的吉普車前左方插上一面羅馬教廷的旗幟,右旁掛著越南共和國小國旗;所到各地機關、守衛軍警均立正敬禮。小地方的安寧人員每每見到我陪著神父,竟都誤會我是修士。路上檢查壯丁,也從不問我證件。知道了自已可免卻被抓去當軍的危險,膽子也就大壯,沒有神父相陪也敢獨自出門逛街了。 偶而也幫掌廚的阿婆去雜貨店購買些沙糖、醬油、雞蛋、鴨蛋之類的用品;雜貨店只有兩母女在經營,起初交易後、微笑頷首說聲謝謝。漸漸熟絡了老闆娘後,便愛多聊幾句,也是她告知那位羞答答的女兒芳名是雪珍。 雪珍很少開口,烏亮的眼珠子像透視鏡能望進人的心底,瞅你一眼便令你顫抖難安;二十來歲的青春燃燒著烘烘的熱火,披肩長髮烏亮、肌膚雪白、臉頰飄紅,沒塗脂粉的素色,清美純潔。有些像教堂右側垂首低眉的聖母瑪利亞,那份氣質自然高貴,沒半絲妖野,也不是冷艷令人動念的那種姿容。 我們淡淡的交換幾句社交話,倒是掌櫃的近乎熱心的招待我,把我看成是她女兒的朋友般。這也難怪、戰爭每天吞噬了無數年青的生命。女大當嫁、可適齡的少女往往難覓異性對象,我竟完全不知因我的出現,而讓她母女心湖攘起圈圈漣漪。 雪珍一家是從北越海防市、南撤逃亡的難民;其父死於法越戰亂,兩位弟弟如今也被配到前線作戰,生死未卜?母親希望女兒能早日找到歸宿,最好是入贅佳婿,這種人選可不容易遇上呢! 那天、雪珍在找回碎錢時、抬頭瞄我的眼眸,彷彿有千言萬語要傾訴?盈盈眼波流轉,接過錢也同時將紙條納入我手掌。懷著忐忑之心出到店外,就急不及待的展閱。她從來矜持害羞,才讓我大為好奇。紙條上沒有上下款,秀麗字體端端正正,極似她平常目不邪視的樣子:「明午二時春香湖畔、出租踏水車處見。」 相識近半載,我因新婚不久便被迫離家,住於教堂內生活有如出家人般,心無二念。和雪珍泛泛之交,漸漸成為朋友,但總是在她店裏、立於櫃檯前閒聊幾句,絕沒半分妄想倚念。故從來不約會她,她的主動令我整晚輾轉難眠,也猜不透究竟所為何事?去與不去的在腦內掙扎著。 好奇心的誘惑,讓我忍不住的按時到達名聞遐邇的春香湖。大叻勝景著名的有水廉洞、鵝芽大瀑布、皇陵、嘆息湖等,但均比不上位於市郊靜臥於群峰繚繞中的這面青翠捺人的春香湖。 繞湖五公里、在處處垂柳飄拂中築有漫步小徑,斜坡釉綠細草如絨,穿著越南傳統長衫旗袍的女大學生們,或坐或半臥於草坡上閱讀書報。白雲輕移,山風掠拂,湖面漣漪旅舞圈圈,零星散開的七彩腳踏車劃破水鏡,置身湖上,彷彿已走入畫圖中,人與畫早已融為一體。 雪珍穿著碎花紫紅長袖上衣,深藍色牛仔褲配著運動鞋;展顏微笑,甜蜜芬芳;淺淺酒窩在白淨臉上欲隱欲現的掛著,她猶如是一杯清醇的陳年茅台酒,令我未飲已醺醺欲醉。 「坐水車或散步?」雪珍的聲音像夢囈,宛若不對著任何人而發,許是害羞或者天生腆顏內向,亦可能是少女矜持作祟,連望我的勇氣也沒有。 「我從來沒試過在湖上踏車,就試水車好嗎?」我有點失態的凝望她說。 她微微頷首,我就前去辦租車手續,因不是假期也非旅遊季節,水車排擠在湖畔任挑,我選了一部較新的,便扶著雪珍踏足仍在搖晃著的車內。 水車漫漫駛至湖心,我幾乎忘了身旁還有位寡言的佳人同遊。獨自陶醉在湖光山色的詩畫裏。當被迎面的另輪水車濺上水珠時,才猛然驚覺的想起雪珍,不禁問她:「你找我出來、有什麼事嗎?」 她朝我望著,什麼也不說,眼淚卻如岸上落櫻紛紛飄下,沿頰流瀉。使我頓時手足無措,將毛巾遞去,沒勇氣為她拭擦,怕唐突輕薄,小心的問:「珍姐,我能為妳做什麼嗎?」 「媽迫我嫁,可那個男人竟大我二十歲。」 輪到我沉默了,不知該如何接口?她的淚珠暫斷,繼續啟口說:「我想問問你,我該怎麼辦?」雪珍說完側身,噙著淚注視我,猶如我是一塊被她發現的古玉般,要全心全意專心的凝視。 「不歡喜就反抗啊,都什麼時代了?我幫妳說去,伯母並非是蠻不講理的人啊!」望向她楚楚動人的姿影,不禁激起了憐香惜玉之心,未及深思脫口而出。好像我就是她的護花使者似的。 沒想到我的話宛若是顆定心丹,她倏然轉悲為喜,破啼嬌羞的一陣忘情,粉頰無端飛紅。涼風颯颯送至,傳來她少女特有的氣息、芬芳撲鼻,使我如飲玉液瓊漿、酡酡然飄浮於湖上。 雪珍驟然抓著我雙手,熱切在說:「有你相幫那就太好啦!媽看來不會再迫我了。」她往昔的矜持竟因我先前那句話、而使我們間的界線忽然隱遁無蹤。我剎那中竟幻化成她的救星,或者已變成了她內心夢境繪描的“白馬王子”,這些心態我是無從知曉和追查了。 遠山近水、映照午後暖洋洋的秋陽,碧翠湖面,我們的倒影依偎。在迷茫的情懷裡彷彿如夢中。而雪珍已化為妻子,溫熱從丹田頓湧上升,不自覺的嘴唇滾熱難禁,正想移近那兩片充滿誘惑靈秀濕潤如魚唇的小口,雪珍出奇不意抓起我的右手,一臉寒冰凝注我,冷冷地開口:「你原來已經……」 我茫然的被這意外舉動震嚇著,縮回手,妻子的容顏倏然穿越時空、顯現自那枚白金結婚戒指上,我慚愧而失落的重重點首。她忽然的將身體往左移開,竟像我已變成一條會吞噬人的毒蛇?先前融洽溫馨已因她觸及我指上的金戒指而消逝。我再非她一廂情願的救星,自也不是她心中的王子,她的淚珠無聲的滑瀉著,山城善變的氣候也翻臉了,雨絲如鵝毛般滿天滿湖的飄落。 「為何你不早告訴我?為什麼啊?」她瞪著湖心怒吼,猶似要向春香湖討回失落的自尊。我腦內空白一片、無措而惶恐的加速腳力把水車駕回湖畔;心中湧起一份無奈和遺憾。從沒存心去騙她,更不會在對嬌妻濃濃的相思中、分心向另位女孩獻殷勤,何況事先也無法猜度雪珍相約的目的。 自那次遊湖分手後一段時間,我再去購物,以為雪珍不會再像從前般搭理我?意外的是她竟若無事般,悄悄對我說:「原諒我那天的失態,我已經認命了。 」 我有如被她狠狠錘擊著心胸般、聽著她不帶感情的聲音。她像春香湖上繽紛的彩虹偶又貼到的眼瞳,在我還來不及細細觀賞,那抹美麗的形象便已隱沒天際,我有份失落的傷感,急急逃遁。 知道她出嫁的消息還是張神父對我提起,那時我已到山城外三十五公里的從義市新村聖文山小學教書,神父任校長,也把遠在西貢的太太接來同甘共苦。 戰亂連綿、河山變色,投奔汪洋,悠悠歲月馳騁如野馬;和雪珍一別,匆匆已三十餘載,縱然擦身而過也無從相認啦! 午夜一個萬里外的電話,記憶不起的聲音,卻勾出了春香湖畔那個美麗午後,可人的珍姐及山城的櫻花依然鮮艷如昔的在我腦內映現,還有仙境似的春香湖,都在我夢裏悠悠轉醒了……。
二零一二年元月十八日首發於墨爾本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