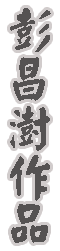|
|
|||
|
歸鄉偶記
在我的記憶裡,故鄉的春天已經成了久遠的一種回味,這種回味裡帶著些青草的馨香,油菜花流淌的金黃,池塘裡蛙聲的延綿,幾只穿過庭院的白色蝴蝶,田埂邊幾朵淡紫色的不知名的小花的點綴,還有母親在田邊向午季的收成殷切地眺望。
我在上海至南京的火車上這樣暢想時,故鄉就已經像一幅水彩畫一樣鋪現於眼前了,故鄉在這個春天裡有些沉默但又心意飄搖。我是於清明節回家的,清明時節已經有了些春暮的味道了,有些凋謝與花落知多少的憐惜。當我與大小姐踏進我家院子時,院子當中的那株桃樹已經有卸妝的模樣,枝上還有些零星桃花的殘存,而靠近院門的那株桃樹似乎有些遲疑是否已經過了春天的時令,這樣的遲疑讓她的枝頭還有大朵桃花的不忍飄零,盡管這已經有了盛極而衰的隱喻。
父親打著手電筒把我與大小姐迎進院子,我們家附近的人家幾乎都搬到公路邊去居住了,只留下殘垣斷壁,還有些孤零的房子在星夜的顯出黑黝黝的鬼魅的色調,四處都是雜樹斑駁的影子以及藤蔓的到處爬行,偶爾會有一只夜行的貓發出警惕的叫聲,風從遠處的山崗上吹過來,帶著油菜花的睡眼惺忪混沌的香味。我家後門透出的一絲燈光在夜裡散發出溫暖的指引,指引夜歸人,我便與大小姐在這樣的指示下到達曾經熟悉的家。
母親已經在家裡等待已久,聽聞我們雜沓的腳步由遠及近,已經在大門口引頸張望,聽到父親的咳嗽聲,忙不迭地去開門,父親的咳嗽聲簡直就有了「漁歌互答」的調子了。
問候了母親一聲,寒暄完,母親便有些笑盈盈地半是打量半是欣喜地與大小姐聊起了路上舟車勞苦之類的話題。筵席漸次擺上,只待漂泊的心稍稍安定。我端起了酒杯,目光逡巡而後又游離至庭院中去,喝下一口燒酒後,忽然想起「一舉累十觴,十觴也不醉」,那是杜甫在友人家的感懷傷時之作,我與大小姐省親也不至於要省得如此累落寡懷吧,夜風吹過庭院裡的竹子,竹子發出了沙沙輕暢的聲音,驚起幾只入眠的小鳥起身繞樹輕鳴。
母親使出了渾身解數,拿手的菜悉數托出。一道菜是蒸鯽魚,我想那是不能叫清蒸的,因為魚身上覆蓋了一層薄薄的醬,那是母親自己做的醬,要是祖母還健在的話,祖母應當是做醬的行家裡手了吧,記得小時候,記得在盛夏的烈日下,祖母總是在不停地翻動那些蒸熟了用來做醬的小麥,祖母在夏天總是習慣於穿著她那由家織布做成的藍色的褂子,褂子的紐扣是由布條繞成一個布團而成,這樣的布團紐扣與現代的服裝工藝沒有什麼技術上的傳承與緣源,這是屬於我祖母有關於過去年代的記憶與把那樣的記憶帶到現在的無奈與略微的心酸。祖母的墳塋就在東山坡上,明天我就要去探望,墳塋前的那棵苦楝不知是否有粗壯幾許。蒸鯽魚上甚至還覆蓋了一層豬油,這是母親關於菜肴烹飪技藝的一種理解,凡是油多的,尤其豬油汪汪在目的,母親便認為是可口而且營養上乘的,這也是母親對過去困苦生活理解的一種遺存。在所有的菜肴中,魚可能是我最為鍾愛的一種,而且鯽魚又是最喜,因為有關於鯽魚有太多的鄉土氣息與太多的故事可以浮想與回憶了。且不論鯽魚那流線型的體型、大大的眼睛讓人有歡喜之情;也不論鯽魚隨遇而安,可以生活在任何一個池塘,任何一片水窪,它簡直就是一個農村孩子暑假生活不可分離的一部分;還不論當母親從廚房端出一碗漂著蔥花與辣椒的鯽魚湯時,那種齒頰生香的感覺;單是我與哥哥拿著魚網在溝裡辛勤捕撈時對鯽魚在網底跳躍的渴望或是我與弟弟在河邊甩下魚釣祈盼留於夏風的情形就足以讓鯽魚成為我記憶的一部分且夜夜隨我夢回這一方水塘與河溝。
一盤泥鰍煮掛麵,泥鰍在麵條裡隱約輕快地游。泥鰍是這個時令的鮮物,它們從幼稚園開始就一直生活在池塘、河溝以及稻田裡,那裡是它們的家園。我家曾經在村子邊有一塊水田,有時種上一些蓮藕,再養上一些小魚,有時也會種上荸薺,荸薺收獲的季節一般是在深秋入秋的時候,放乾了水,然後用手扒開肥潤的淤泥,就會發現在淤泥中荸薺塊莖,而有時就會發現有一尾泥鰍就在淤泥之中穿行,這時的泥鰍已經驚恐萬狀了,只要把雙手掬成一捧,指間不留一絲縫隙,泥鰍在手中已是甕中之鱉插翅難逃了。除了在荸薺地裡捧泥鰍,我還見過其他捕泥鰍的方式,一種是在仲春時,在池塘裡撒下一排魚鉤,魚鉤用一根長線連著,然後到早晨時去一拉,就會發現不少魚鉤上有泥鰍在徒勞地掙扎,有些還是肥碩的大泥鰍,只是我並不知道魚鉤上用的是什麼誘餌;一種是在初夏時,池塘水漲時,就會向河溝裡泄水,這時在泄水的小缺口處放置一個長圓的籠子,籠子下面的入口處有一個倒嵌造型,而泥鰍極喜逆流戲水,而這種挑戰自我的性格也成就了泥鰍成為盤中餐的一種自我犧牲的精神;再有一種就是在油菜花盛開時,打著松子燈或是電筒,在水田或是小溝邊,用一根竹竿前端綁上一把牙刷、牙刷上嵌有許多縫衣服的針的裝置直接去刺靜靜伏在水底的泥鰍,這時被光亮照著的泥鰍往往一動不動,它們還不能理解黑夜時出現的光亮是怎麼回事,就已經被針刺中背脊,這是我最為神往的一種捕泥鰍的方式,在那樣的一個春風夜,耳邊聽著風吟與蟲鳴,聞著野花的香氣是多少令人心馳神往的事情啊,只是那裡父親極嚴厲,而且我和弟弟也經常把牙刷的針插得東倒西歪,以至於沒有親手用這種方式捕到一尾泥鰍。
父親的頭髮在燈光下愈加顯得斑駁而灰暗,白也白得不徹底,黑也黑得不純粹,在我的少時記憶時,只要有條件父親的頭髮總是梳理得一絲不苟,有條不紊地分別佔領額頭兩側,油光可鑒而又神靈活現,可是如今,當皺紋佔領額頭的全境及兩側時,父親對頭髮的打理已經顯得敷衍了草與心不在焉。父親與我一起喝酒時已經沒有橫掃一切的犀利眼神與揮斥方遒的慷慨之態了,取而代之的是裡面叮嚀時而細囑,真讓人喟嘆歲月雕琢人世間的恢弘之力。
母親端坐於我的對面,歲月在母親的臉上留下了深深淺淺的劃痕,母親眼睛依然溫和,只是不再明亮澄澈甚至有些含義不清起來,有時她會神色滯重地看著我,好像想了解我奔走於江湖的寂寥心事也表達對我的足夠擔憂。母親年青時可以喝些白酒,我偶爾會看到她的即興發揮,但高血壓等疾患纏身已讓她對白酒疲於應付而毫無歡娛之情了。我與母親碰杯時,她的手粗糙而黝黑,表面多有些龜裂的口子甚至還用膠布來封住這些貪婪的口子。她小小地呡了一口,並不急於表達這酒的灼烈與難以下咽。
父親母親和我與大小姐就在這樣的一個安靜的春夜喝酒吃飯,時間凝滯。星光透過薄薄的雲彩灑在院子當中,遠處有狗的吠叫聲隱約傳來,還有夜行人虛裝聲勢的咳嗽聲,夜蟲也開始了鳴唱。
朝陽映上窗戶時,我與大小姐還在殘夢中沉澱,父母早已經起床,他們總是有早起的理由,當早起的理由並不存在時,早起就成了習慣。母親做的蛋炒飯做得極好,蛋是家裡養的雞下的,這保證了蛋炒飯原生態品質,母親放些鹽油還有雞蛋,最後再放些蔥花,這也保證了蛋炒飯在形色上的生動與鮮亮。
吃完早飯,大小姐在家裡與母親說些家鄉桃李之類的話題,我與父親去掃墓。我扛著鐵鍬,父親提著鞭炮與紙錢。鐵鍬用來挖掘個泥土的帽子,安放在親人的墳頭,我一直不太明白這帽子的含義,想來可能是用來表達兩層意思,一是表明這不是荒墳野塚,二是明確這墳裡的人數,因為在我曾祖父與曾祖母的墳上父親總是鄭重其事地擺放上兩只新鮮的泥土帽子。
曾祖父與曾祖母我並不認識,父親也僅是在孩提時代親見過他們。尤為神奇的是,在多年前的一個中秋節,曾祖父告訴尚年幼的我的父親,說昨夜夢到一著白衣之人騎一白馬,說些生死由命之類的話,大概是大限將至料理後事吧,沒過幾日,曾祖父便逝去了。這些都是父親告訴我的,每當給曾祖父母祭拜時父親就會說起。父親有關於曾祖父的記憶還有一件事,就是某個風雨交加夜,父親要去找祖母,曾祖父只好背著父親躓跛於泥濘,後曾祖父跌倒傷及了腿,祖父知道後對父親的任性妄為舉動大加呵斥,云云。
祭掃完曾祖父母後,我與父親就去祭拜祖母。祖母離開已經近八年了,八年之間,每逢春節回家,都只見祖母靜靜地沉寂在照片中,而時間也停留在2002年的那個春節。照片中的祖母正襟端坐於大門前,大門上還張貼著我寫的春聯“夜月一簾幽夢,春風十里柔情”,我寫的春聯用遍了詩詞佳句,唯秦觀的這句記得很深。我放鞭炮,父親焚燒紙錢,祖母沒有讀過書,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娛樂喜好,唯好打紙牌,那是一種與麻將相似打法牌面上畫著些象形圖案的紙牌,曾經在與祖母年齡相彷彿的人群中風靡。父親焚著紙錢,我們依次給祖母叩了頭。父親忽然有些莫名地擔憂祖母那邊物價房價飛漲,祖母打牌用度窘迫等等,我也不知道這是父親借故詼諧還是真的心有憂戚。每次祭拜祖母時,我都不由得想起歸有光的『項脊軒志』裡的句子,「娘以指叩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這也許是當年高考前夕我在院中誦讀文章時,祖母就在旁側勞作,今日思之,恍若在昨,嗚呼,汝在九泉,冥遙不知其所,我在汝墳前祭奠前塵,春風颯颯過東山之陰,荒草蓬蒿漫過墳頭。
剩下的日子就在暖陽忽明忽暗間蜜蜂在花間與庭院穿梭中度過。當我與大小姐同故鄉作別的時候,母親還站在原處,她沒有向我揮手,我還沒有來得及向母親說聲珍重保重諸體的話時,我們就已經漸漸遠去,雲低低欲雨的時候我告別了故鄉。
2010.5.20寄自上海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