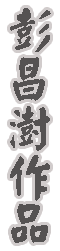|
|
|||
|
故 鄉 (一)
故鄉沒有三千里,家書也不到十五行。
故鄉隱隱約約地蟄伏在長江之北隅,不聞世事,靜默而隱忍,離名山尚遠,隔大川咫尺。故鄉在歷史的風雨中飄搖了幾千年,她已經習慣了春華秋實,農人的忙碌,遊子的回歸。故鄉安靜地躲在地圖的一角,當我的目光在地圖上逡巡時,她竟有些羞澀地一閃身。
大多情況下我回故鄉的時間是在冬日,而且多為近春節的模樣,於是冬日的故鄉便長久滯留在我的記憶深處。冬日的故鄉是蕭瑟的,百草凋零,萬木盡枯,只有偶爾某家院子裡探出身的竹子仍在言不由衷地抗拒季節的召喚,堅持著半角的蔥蘢。村子大部是荒廢了,鄰人們都遷往公路沿線,而荒廢的村子卻顯出了古樸與荒涼的味道,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喜鵲三兩只站在屋脊上或是跳躍於柿子樹枝頭,一派和氣景象,麻雀呼啦啦一群群落下,在地上尋覓秋天的殘剩谷物繼而討論起秋收冬藏的話題,然後便一轟而散。風,不緊不慢地吹著,時而銜枚疾走,時而慵懶無力,它來自哪裡,將去向何處?這都不打緊,它是否帶來嚴冬冰冷的口信或是帶來春天暖陽的問候,也不甚要緊。當出門的姑娘意識到頭巾被吹落時,風確實已是一個存在。
離春節愈近,整個村莊便陷入一種近乎虔誠的期待之中,張家兒子北京打工未歸,吳家女兒在上海嫁人不回。而面對這個春節,仍然是有一部分人是並不期待甚至是想刻意規避的,我便是其中的一個,當然我的孰視無睹的努力注定是徒勞的,因為我的故鄉會不經意間從我的夢中掠過,留下些倒影,但記憶卻隨著波紋一圈圈蕩開。
大年三十,我們這兒的習慣是要去看望地下的祖先,先人們一般會在今天收到其後人通過陰曹地府人民銀行彙出的人民幣或是美元,當然,彙款的方式是當面焚燒那些印刷粗糙的冥幣,後人們也並不知道陰間的人民幣與美元彙率如何計算,但他們並不理會這些,他們將冥幣付之一炬,然後向先人的墳頭叩頭,點上鞭炮,完成一次陰陽間的探視和對先人的緬懷之情,也不管在地下的先人對後人們這種熱切期待交流的心情是否理解,但這種理解與否對後人們完成祭拜的過程並不產生絲毫影響,因為他們完成所有的固定程序後便離開,甚至等不及另一個世界有什麼樣的反應。
我盤腿坐在床頭,年夜飯已經用罷,父親對我煢煢孑立形影相吊寡落而陰晦的情狀不飲也酣了,我也三杯兩盞地郁郁而下了。我換了個更舒適的姿勢,但此時姿勢已不重要,我甚至忘了季節。故國,故鄉,故人,雖近已遠,所有與我有關的人或是物不是故去便是塵封,只是我還存在,存在於欣欣向榮的春天前夜。夜冷,酒暖,風急。葉落,心傷殘。故園,隔了長江,船在浦口渡,緣何回不去?故人,有隔陰陽,有鬢髮染霜,可也不待我。故事,在春天玲瓏,在冬日謝幕。我悲愁啊悲愁,我枕著悲愁入眠,悲愁的秋波裡,我踏不上歲月的船。
故 鄉 (二)
2011年2月4日,星期五,正月初二,晴暖。
這是一個苦撐苦熬的春節,一個光棍漢,睡在斗室裡,四周寂然,唯渺遠處圩上的冬鵝的鳴叫聲時而傳來。狗吠倒是少了,顯得夜不夠岑寂,像圓月夜浮在半空中的雲彩一樣,薄而輕飄。
十一回家時,家裡尚有一狗一貓,而此時,它們皆被遺棄於寒冷而曠莽的角落,曾經的家它們是斷然不識的,我想即使它們識途,也是斷然不會回來的,因為它們也是有尊嚴的。它們之所以被棄,狗則活潑有餘,看家護院尚有餘力,常追逐孩童並作囓咬之狀,家人恐釀成禍端,棄也。貓剛喜睡於父親無比珍視的棉花之上且便溺無度,棄也。真不知道它們是否尚在人世間且這個春節延綿的鞭炮與煙花有無嚇著它們,巷子裡四處飄溢的香氣有無讓它們想起曾經的殘羹剩炙的甜美。總之,我是想祝福它們。
而此時,我卻成為一個得不到祝福且被生活所懲罰之人,我用一半的時間來思考過去,一半的時間來思考未來,而在一半與一半之間,我被時間所凝固,失去了知覺。
我睡在靠北的房間裡,夜裡,一些不可名狀的往事便像精靈一樣跳起來啃噬我的靈魂,讓我的靈魂如同Apple一樣殘缺不全,凡即此時我總是習慣寫著“向往事道別”,我也知道我只是向時光揮手,而不是往事,往事無論你如何轉身,也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我越寫越晦澀,越寫越陰冷,冷得這厚厚的棉被也難以阻擋往事冰冷的穿越。
我一人獨歸,一個根本就不應當存在的獨歸,一個失魂落魄光棍的歸故鄉,不是大風歌裡的劉邦,“威加海內兮歸故鄉”,也不是宋之問的“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我也早有預見,但還是一頭扎進鄙薄非難指責猜忌擔憂五味雜陳的泥沼之中,掙扎不得,形同窒息。
一只夜行的貓走過我的窗前,不遠處喻意不清的鞭炮響了起來。
2011.2.24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