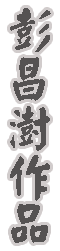|
|
|||
|
我的祖母
祖母去世已近十年了。十年以來,我鮮少會夢到她。只是在大學畢業的那年春天夢到她死去,我從悲痛哭泣中醒來,卻發現四川的春天有種迷朦的美,繼而我有些慶幸這只是一場夢,祖母還活著,還鮮亮著活在安徽的某地鄉下,還要侍奉炊煙,還要去河邊牧牛,還要關心莊稼的收成。
那時祖母已經是年逾八旬的老人了,步履有些蹣跚了,可她是一個自尊且相當固執的人,她也許花了相當長的時間來抵制從步態輕鬆到蹣跚這一過程,但她的固執沒有敵得過時間的堅持,她最後索性就放棄了,也順了時間的意。祖母的眼神也開始變得游離,她的眼神時而逡巡於蒼天與暮色之間,時而又將牆角絲瓜開出的淡黃小花和農村沒有未來的未來混為一談。
祖母的命應當是苦的。祖母本姓劉,因為家貧,被寄養在葉姓人家,故其大名是姓葉的。我並不知道祖母被寄養時的具體情形,但她與兩家的弟弟關係都還算融洽,當時也時常走動。祖母應當是十七八歲就嫁給了我祖父,而我祖父是個極嚴厲的人,妻兒一般只能是惟命是從吧。祖母沒有上過學,也不會講什麼故事,她與我講述的一般是一個情景,然後加上她的個人的情感或是評判,如某家夫妻打架,祖母敘述完便是評判,如女人不是,便評為“惡婦”之類,中間基本不作什麼停頓,也不會賣什麼關子或是故弄玄虛,好惡之色溢於言表。祖母在世時目睹三位親人的離世。一則是我叔叔,謂之殤。叔叔年幼時,趕上自然災害,家鄉餓死了不少人,雖不是餓殍千里,但營養不良常有人餓死確有其事,加上叔叔患上了什麼疾病,加上鄉下醫院對此也是束手無策,故只能放在家裡,讓幼小的生命來對抗死亡,結果沒有抗住,用一卷草席草草掩埋。那段日子我想祖母應當是悲戚的,是掙扎在淚水中的。二則是我大姑,大姑罹患食道癌,也是無可救藥的那種,那時我還年幼,並不善於察顏觀色,故沒有察覺祖母的悲憂。三則是我祖父,祖父也是癌症,記得祖父去世時,祖母放下帳縵,大放悲聲,並囑咐我去地裡叫父親,此情此景,記憶猶新。
祖母的命是苦的,我似乎並沒有給她帶來稍許的甜,也許是有的,但到底有沒有,祖母不曾說過,我也不知道。也許祖母認為苦是生活的本源,稍許的甜可能更怡人,但只能是稍許,多一絲毫就顯得過膩,失去了生活的本色,反而讓她惴惴不安如坐針氈。但還是遺憾,因為不知道祖母是否曾為我驕傲過,幸福過。 祖母是個善良的人。祖母在家境相當艱難之時,用家裡僅有的一點米為行路的陌生人做飯,當然過客吃完後並沒有拍屁股走人,而是解下包袱取出一升米,當時這應當是一大筆財富,因為父親每說到此,都神采奕奕倍受鼓舞的樣子。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這樣的故事父親講得多了,我們都相信這是真的了,而且似乎確實是真的。當時我確乎有些小聰明,曾反駁父親說,會不會是祖母覺得人家是有米之人,想殷勤做飯博些同情以達到不給米實在是過意不去而勉強為之呢,父親馬上面呈不悅之色,而且確實不悅了,只為這樣的懷疑已經偏離了他講故事的主旨,我只好閉嘴,任由這樣的故事在我家肆意流傳。
祖母樂於助人。祖母會一種類似占卜的巫術,經常會有人家請她去給一些受過驚嚇或是夢囈盜汗低燒的小孩做些問詢神靈之類的活動,我曾親眼見過,她手持一個小碗,碗中裝滿大米,用手巾扎緊,然後倒置,她提著在小孩的頭頂上頻頻轉圈,口中念念有詞,有時含口水,“噗”地噴出去,煞有介事,患者家屬肅然起敬,最後,祖母會明確給出結論,邪氣來自何方,患者家屬千恩萬謝。這樣的活動也許會消耗體力與精力吧,因為有時會聽祖母說累,時不時的嘆息一聲。患者家屬有時會送幾枚雞蛋過來感謝,祖母一般是會推辭的,當然一般是推辭不掉的,所以只得收下。
祖母去世前的那個春節,兄弟們只有我在家,她好像感覺自己大限將至,常會與我說起生與死,還有死後我是否會記得她這樣的話題,當時我有些不祥的預感,但看她還是比較健康的模樣,也就隱去了那一絲不祥。我和她說起我的戀愛,她似乎對這並不感興趣。她是對的,因為沒過兩年這場戀愛被證明是無果之花,她對沒有結果的東西向來是持懷疑態度的。某日傍晚,我去河邊散步,她從村口蹣跚而出,喚我回家吃飯,很急切的樣子,在暮色中有些凄涼,似乎有形將失去永不能再見的意味。她是對的,因為那是她給我最為深刻的最後一個瞬間。
祖母去世已近十年了。十年以來,我很少夢到她。不知是我的生命只給她預留了二十七年的空間,還是我思念至深。
2012.3.21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