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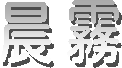
似乎是從遠古的黑夜洩出
那幽幽的笛聲啊
又似乎是從兩肩坐起
蓬鬆的髪髻遺留下昨夜的狼藉
當目光驟然駐錫
一株沿垣欲哭的忘憂草
我知道 我真的知道
要甦醒的終於甦醒了
那名字叫貓的
凝視
一件件未曾洗滌而又穿上的舊衣
坐在濕濡濡的青苔階上
睜目也見 閉目也見
少年時 是嘴嚼過的餅酪
年青時 是拭額成一掌的滄桑
他說: 才一九七二年冬末
才二十五歲零十天
甚麼葦蘆就纏著華髮
眉藏著蛇 蛇噬著心
然後穿霧而入
脫落是一些未在記憶的餘塵
當已証實;牆只不過是
躲避羞恥的屏障
早禱便扭曲如巫婦的咀咒
讓霧冉冉死去
讓陽光冉冉死去
讓無助的手
分白日成兩岸搖晃
一九七二年.冬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