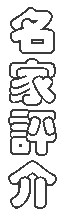|
|
李魁賢:論非馬的詩
|
||
|
非馬(1936-),本名馬為義,原籍廣東潮陽,在台中市出生、長大,念台北工專 機械科時開始以「馬石」(音「馬蛋」)為筆名寫詩,畢業後在屏東糖廠工作。 1961年秋赴美留學,先後得馬開大學機械工程碩士及威斯康辛大學核工博士。現任職美國阿岡國家研究所,從事核能發電研究工作。
非馬早期詩作發表於藍星、現代詩、現代文學等,赴美後,學有所成,重新執筆為詩,即以笠為中心發表作品,間或旁及幼獅文藝、創世紀、台灣文藝、聯合報、布谷鳥、台灣時報、自立晚報等,作品甚豐,出版有中英對照詩集《在風城》(1975年),《非馬詩選》(1983年),《白馬集》(1984年),《非馬集》(1984年),《非馬集》(1984年)和《篤篤有聲的馬蹄》(1986年)。他的翻譯更勤勉而豐富,除出版有英譯白萩詩集《香頌》(1972年)、《笠詩選》(1973年),和中譯《裴外的詩》(1978年)外,其翻譯世界各國詩作大部分發表在笠詩刊,據統計超過七百首,數量極為驚人,介紹遍及英、美、法、意、波蘭、俄、澳、猶太、希臘、拉丁美洲等國詩人作品,非馬做了這麼多文學交流工作實績,卻找不到出版機構替他出書,常令他感嘆萬分。
非馬作品曾被選入中華民國出版的《美麗島詩集》《中國新詩選》《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現代百家詩選》《中國當代新詩大展》《中國 現代文學年選• 詩 卷 》《80年代詩選》《聯副30年文學大系•詩卷》《1982年台灣詩選》《71年詩選》,日本出版的《華麗島詩集》《台灣現代詩集》,美國出版的《Yearbook of Modern Poetry》《Melody of the Muse》, 印度出版的Ocarina 版《世界詩選》 等。獲1981年吳濁流新詩獎,1982年笠詩社翻譯獎。
非馬寫詩的中心思想,可以說是植根於中國傳統儒家的「仁」為基本而出發的,他自述的「詩觀」說明很簡要清楚:
對人類有廣泛的同情心與愛心,是我理想中好詩的要件。同時,它不應該只 是寫給一兩個人看的應酬詩,那種詩寫得再工整,在我看來也只是一種文字遊戲與浪費。
詩人應該誠實地表達他內心所想的東西。一個人應該先學會做人,再來學做詩。從這個觀點看,我覺得一個人如果內心不美而寫出一些唯美的東西來裝飾,是一種可厭的作假。
對一首詩,我們首先要問,它的歷史地位如何?它替人類的文化傳統增添了什麼?其次,它想表達的是健康積極的感情呢?還是個人情緒的宣泄?對象是大多數人呢?還是少數的幾個「貴族」?最後我們才來檢討它是否誠實地表達了想表達的?有沒有更好的方式?更有效的語言?(注1)
足見非馬所著重的是秉持仁民愛物的「同情心與愛心」的根源與懷抱,來從事詩的創作。他強調「先學會做人,再來學做詩」,正是堅持詩人立場的最好注解。以人品的修養,才能建立詩品的層次,是他基本的觀點。因此,做為詩人,應負有文化傳承與教化社會的使命感,做為詩的作品,應具有適當準確的傳達性。而在此二項並進的作為上,先根植詩人厚實的立場,再講求詩藝的創作,正是非馬整個觀念論的基礎。
至於非馬的表現論,可以從他1977年在芝加哥中國文藝座談會上演講〈略談現代詩〉(注2),表現得最清楚,他認為一首成功的現代詩應具有四個特徵:
第一個特徵是「社會性」:非馬認為一個詩人「必須到太陽底下去同大家一起流血流汗,他必須成為社會有用的一員,然後才可能寫出有血有肉的作品,才有可能對所生活的社會及時代作忠實批判和記錄。」因此,詩人本身就必須是一個生產者,同樣是勞動人口。
第二個特徵是「新」:非馬排斥標奇立異,他所意指的「新」,是要從「平凡的日常事物裡找出不平凡的意義,從明明不可能的情況裡推出可能」,換句話說,是要喚起事物被蒙蔽的意義,令讀者發現其本質,而產生「驚訝」。
第三個特徵是「象徵性」:他說:「一首不含象徵或沒有意象的詩是很難存在的。一個帶有多重意義的意象不但可以擴展想象的領域,而且使一首詩成為一個有機的組織。」意象可以喚起讀者知覺上的經驗,達成必需的共感。而象徵是「意象」與「意義」間建立的關聯性,詩人如能善於經營意象,來產生象徵性效果,就會使詩成為飽和成熟的果實。
第四個特徵是「濃縮」:善用意象本來就是濃縮的手段,但非馬所要求濃縮的意義不但是要精簡字句和意象而已,甚至於也要求「避免用堆砌的形容詞及拖泥帶水的連接詞。過量地使用連接詞或形容詞,必然使一首詩變得鬆軟疲弱,毫無張力。」這裡實際上已牽涉到詩學上方法論的問題了。
我們考察非馬的全部作品,幾乎都是遵循著這四個特徵在努力,因此他的詩兼具了語言精煉、意義透明、象徵飽滿、張力強韌的諸項優點,具有非常典型性的意象主義詩的特色和魅力,和意象派六大信條中強調的:語言精確、創造新節奏、選擇新題材、塑造意象、明朗、凝煉,有相當符合。在我國詩壇上,非馬是正牌的意象主義者,旗幟非常鮮明,而且他的創作立場和態度也一直循此方向在發展,很少有曖昧或模棱兩可。
筆者曾在〈風城的巡禮〉(注3)一文中評非馬詩集《在風城》,並舉〈電視〉〈致索忍尼辛〉〈籠鳥〉〈鳥籠〉〈裸奔〉五首詩加以賞析。其實,非馬好詩很多,為免重複,今另舉《非馬詩選》以後的作品五首為例,以見其詩藝與風格之一斑。
<黑夜裡的勾當>
仰天長嘯 曠野裡的 一匹 狼
低頭時 嗅到了 籬笆裡 一枚 含毒的 肉餅
便夾起尾巴 變成 一條 狗
本詩前後以「狼」「狗」對比,來劃分出狀態的改變。狼和狗本來同屬食肉且哺乳動物,同列於犬科,實際上狗的祖先就是野狼,後來逐漸馴服,而狼則還保持相當強烈的野性。
在詩意上,狼象徵保持原有個性和獨立格調的存在,是極為明顯的。以「曠野」空曠無際罕有人跡的背境,來襯托「一匹狼」的惟我獨尊。而「仰天長嘯」之借用岳飛滿江紅詞,愈顯其壯志遼闊、豪情萬丈的氣慨。實際上,「狼」不是單純寫狼,其象徵的人物個性和態度已至為明顯。
從「仰天」到「低頭」,是純然的對比,並顯出突兀的改變。低頭時卻是嗅到籬笆裡的一枚肉餅,相對於前段產生譏刺性的境遇。由「仰天長嘯」時的精神昂揚,到「嗅到肉餅」的物質誘惑,從「曠野」的開放天地,到「離笆」的狹隘限制,顯示轉變的激烈。
然而,最令人觸目驚心的是「肉餅」竟是毒餌。這個「毒」可能是致死的美麗毒物,連壯懷激烈的人物也禁不住其誘惑。然而,更嚴重的卻是無形的毒劑,並不傷害其生命,卻是腐蝕其精神意志,摧毀其生命的本質。
於是,受到誘惑的狼,一下子就變成了「夾尾狗」,畏畏葸葸,真是喪家之犬了。由仰天長嘯的狼,到夾起尾巴的狗,其間變化有如天壤,而其變化之肇因,在於立場不夠堅定所導致。
題材新穎是這首詩的魅力,語言精煉是它的特點,而其象徵性所包含的普遍性意義,則對所象徵的某些社會現象產生尖銳而中肯的批判(回顧詩題〈黑夜裡的勾當〉,即思過半矣!)完全符合了非馬對好詩所立定的要求。
〈醉漢〉
把短短的巷子 走成一條 曲折 迴盪的 萬里愁腸
左一腳 十年 右一腳 十年 母親啊 我正努力 向您 走 來
這首詩曾獲得1978年吳濁流新詩獎佳作,非馬1936年在台中市出生後,同時隨全家遷返廣東潮陽原籍,1948年隨父來台,不久大陸變色,與留在故鄉的母親斷絕音訊。
這首詩雖然寫的是思親的愁緒。題目的〈醉漢〉本身便有多重的意義,可以表示真正醉酒後引起酒入愁腸化做相思情,也可以表示因思情以致如醉如痴的恍惚。
然而從詩裡所描述的,顯示一種近鄉情怯的醉態,是極為令人黯然神傷的情景。「巷子」與「愁腸」的對比,把走近門口將要與親人重見的一段歷程強化了。「短短」的巷子,竟然有「萬里」愁腸的心酸,除了真有舉步沉重,以致感到遙不可及外,另含有萬里尋親的真實意義在。巷子可能真的曲折,但是能夠克服一切困難,使親人重見,本身豈不是經過相當曲折的困境嗎?大概只有「迴腸蕩氣」才能形容那種兼揉酸甜苦辣的心頭滋味吧?
「左一腳/十年/右一腳/十年」,暗喻離別之久外,更是近門時那種寸步難進的寫照。對母親傾訴「我正努力向您走來」,這種努力也不只是抑制悲情要扣開鄉關的努力而已,真是不知要擺脫多少內心的交戰,外界現實的阻礙和困擾啊。
文字的簡單、旋律的短促雖是非馬的特徵,但在本詩到末尾的一字一句,更暗示了路途的遙遠吧。
幾乎每一個詩句都要負擔多重的意義和象徵,是非馬詩藝最講究之處,因此,看似短短的幾段詩,常是飽和的自足自立的存在,而象徵性的延伸,也是令人常有愈讀愈有新的體驗的發現,也感到讀詩的快慰和感動。
〈反候鳥〉
才稍稍括了一下西北風 敏感的候鳥們 便一個個攜兒抱女 拖箱曳櫃,口銜綠卡 飛向新大陸去了
拒絕作候鳥的可敬的朋友們啊 好好經營這現在完全屬於你們的家園 而當冬天真的來到,你們絕不會孤單 成群的反候鳥將自各種天候 各個方向飛來同你們相守
所謂「候鳥」是指每年順應氣候而遷徙的鳥類,主要當然為了生活,不得不避開惡劣的氣候,遷往容易覓食之地。例如氣候嚴寒時,向南方,等到氣候轉暖時再飛回,每年就重複如此循環的集體遷徙作業。相反的是「留鳥」,即無論氣候如何變化,只有在原地變化生活環境的海拔高度,而不向遠方移棲。
實際上,在鳥類學上並無「反候鳥」的動物,非馬創作此名詞,用來表示與候鳥相反的行徑,假設有一種鳥,不但不避開惡劣的環境,反而投往境遇不佳的場所,以求團結抵御困境的獻身,是一種迎向戰鬥的美德的象徵。
詩中所寫的候鳥,當然是明喻著對本身植根的土地失去信心,而逃往美國新大陸的人物。作者所寫「才稍稍括了一下西北風」,表示並非真正嚴寒季節來臨的徵兆,而候鳥的過敏,顯示過度反應的行徑。
當然,非馬對過敏的候鳥並未提出譴責,基於詩人悲憫的心懷和寬容吧。因為在下一段中,非馬立即對拒絕作候鳥的朋友們,表示敬意,那麼詩人對候鳥的態度,也就不言可喻了。
最後,非馬以自創的「反候鳥」,表示真正冬天到來時,將發揮與候鳥避難行為完全相反的赴難態度,回來共相廝守家園,是極為令人感到溫暖,並富有鼓舞士氣力量的宣告。
四季(2)
◇春 只有從冰雪裡來的生命 才能這麼不存戒心 把最鮮艷最脆弱的花蕊 五彩繽紛地 向這世界開放
◇夏 向焦渴的大地 奉獻我們的汗滴
滾圓晶瑩的露珠 源自生命的大海 帶著鹹味
◇秋 妻兒在你頭上 找到一根白髮時 的驚呼 竟帶有拾穗者 壓抑不住的 歡喜
◇冬 越冷的日子 希望的爐火越旺
我們心中 沒有能源危機這回事
對於意象主義者,追求以部分意象暗示全體的努力,似乎勢所必趨,因為透過這個層次,才能達成象徵的效果。非馬寫過不少以四季意象為主題的詩,季節的輪替,可以顯示自然景物的盛衰變化,從而看出生命的迭替。在《白馬集》裡,甚至寫出樹、鳥、狗等生物的四季形態,非馬刻意從意象中去探究生命的實質,是很明顯的。
就以此處所舉〈四季〉第二組詩為例,便一直圍繞著生命的勁力在表達。在春天,生命嶄露新姿,是大自然更新之始。非馬特別選定在雪後的場景,對於終年不見雪的台灣讀者,對雪也許只有遠隔的美感想象,缺乏親身的感受體驗,但以在入冬後即被雪封閉的芝加哥等北方之地生活的人們而言,冰天雪地真的有如夢魘。經過如此嚴重苦難後的生命,即使「最鮮嫩最脆弱的花蕊」,也敢(不存戒心)向世界開放,表示了生命從與自然的疏離,又進入與自然和諧的一個轉化過程。那麼,這個「世界」終究是一個自由的、自適自如的存在場所。
夏天正是酷暑的季節,大地的「焦渴」干旱,在大自然的調適上,也產生了疏離現象,然而詩人卻以生命的「汗滴」做為諧和的趨迎之道,同樣努力以轉化來提升精神的境界。由「汗滴」轉化為「露珠」,已成為「甘露」的象徵。而「鹹味」是鹽份的特質,生命的鹽份(本質)對焦渴的大地(存在)的基本關聯性,在此短短數行中表露無遺。
「秋」稍微帶有一些戲謔性,對於步入中年者初生華髮的心情,有反面思考性的表達。平心而論,人生歷練雖然學識經驗日豐,但生命卻日衰,尤以人到中年,感覺日漸強烈,因此,中年生白髮是相當「敏感」的話題,即使再如何坦然處之,仍不免有百感交集湧上心頭。非馬在詩中卻非常巧妙地把「白髮」與「拾穗」意象加以聯接,一方面在人生時序上,同樣有入秋,從夏季的絢爛回歸平淡的況味,另方面卻有進入收獲季的喜悅感,在精神上也是以「轉化」求得生命與自然的諧和歸趨。
在天寒地凍的北方冬季裡,如不升火取暖,人簡直無法抵禦自然氣候的肆虐,在北方可以沒有冷氣設備,卻不能沒有暖氣。然而,在發生能源危機的時候,因石油價格高漲,對北方冬天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威脅。非馬把現實的困境故意隱晦,卻以「希望的爐火」來代替,是從現實到精神層次的另一種轉化過程。由於此項轉化,在越困境中產生對未來越強烈的希望,所以「能源危機」的威脅自然不放在心頭。
芝加哥 ◆ 一個過路的詩人說﹕沒有比這城市更荒涼的了,連沙漠…
海市蜃樓中 突然冒起 一座四四方方 純西方的 塔
一個東方少年 僕僕來到它的跟前 還來不及抖去 滿身風塵 便急急登上 這人工的峰頂
但在見錢眼開的望遠鏡裡 他只看到 畢卡索的女人 在不廣的廣場上 鐵青著半邊臉 她的肋骨 在兩條街外 一座未灌水泥的樓基上 根根暴露
這鋼的現實 他悲哀地想 無論如何 塞不進 他小小的行囊
這首詩曾入選前衛版《1982年台灣詩選》。芝加哥是美國的工業城市,在詩中可以做為西方工業文明的象徵,美國詩人桑德堡也寫過芝加哥,就是其中一例。但非馬寫芝加哥,不單純在描寫芝加哥,而是企圖表達出來自東方文明國家的少年,來到西方工業城市的感受,實際上就是部分留學生的心路歷程的寫照。
所謂「海市蜃樓」是烏有的假想,初履斯地的東方少年,對於市內聳立的高樓巨塔,會產生難以想象的驚訝,因此,以為是海市蜃樓的幻境。可是盡管工業城市的建設令人驚嘆,那種「四四方方的」造型,對東方少年來說,已暗示著單調,而有文明技術與文明實質背離的觀感。
東方少年不可諱言是懷著理想來到西方城市,僕僕風塵來此登臨,本身行徑大概就有讀書人千里迢迢登臨泰山的朝拜心情,一種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壯志心懷,只是時空倒錯,自然與人工造境也就大異其趣。
第二段顯示非馬在廣大鏡頭內將意象加以壓縮和跳接到描寫技巧。凡觀光之地,大多有投幣式望遠鏡的設置,要投錢才能觀望,「見錢眼開」一則為寫實,二則諷刺物質社會唯利是圖的行為。所謂「畢加索的女人」指畢加索在芝加哥廣場的一座雕塑而言,而畢加索自從1907年繪出揭開立體主義序幕的「亞維儂的少女們」後,在他筆下,將形象加以肢解和重組,對於一般純潔、諧和的美,重做新的詮釋。這種立體主義以後的一些美學感念,正好與機械文明有些吻合之處,因此,非馬從實景聯想到畢加索的女人,也是自然而大膽的意象技巧。
女人「鐵青著半邊臉」,而肋骨暴露在兩條街外,這是很典型的畢加索立體主義時期的構圖,非馬的造型可以是景物的比喻,實際上也可以是實景的組合,簡單的說,從望遠鏡裡也可能真的看到一個女人鐵青著半邊臉,那是奇異化妝的側寫,而在兩條街外,另外有女人在樓基上作日光浴呢。但無論如何,女人肋骨與鋼筋的聯想,陰柔與陽剛的強烈對比,以及女人整體的美與鋼筋樓板犬牙交錯的醜相對照,都予非馬除了東方與西方的本質文化歧異外,又刻意加上的對立效果。
這樣的矛盾給予東方少年的衝擊,成為他無法包容或接納這種唯鋼鐵支持一切的工業城市風格。事實上,非馬寫出了東西文化接觸時的矛盾,而他的東方立場,使他肯定了表面上繁榮的西方城市實際上是荒涼的說法,因為只見技巧,而不見實質。
總之,非馬的詩正如他所要求的,具有著社會性、新奇性、象徵性、精確性的特質,他的努力已經把自己塑造成為相當典型的一位意象詩人。
附注:1。見《美麗島詩集》226頁,笠詩社,1979年6月。 2。《笠》80期,1977年8月。 3。《笠》70期,1975年12月。
原載:《文訊》,第三期,1983年9月10日; 《台灣詩人作品論》,李魁賢著,名流出版社,台北,1987年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