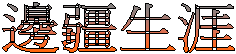
《征途摭拾》之八
越戰像潰爛的毒瘡,一天天的蔓延開去。為這毒瘡研討開方配藥的「巴黎診療所」,各醫師束手無策;觀點距離,各不相讓、各持己見的互相指責,消耗光陰和金錢,仍不能對症下藥。毒瘡由越南體內潰爛到柬埔寨,更發作到寮國去。
正在越軍進柬作業如火如荼的時候,在中區,又發動了寮南「藍山七一九」戰役。寮南的山頭血戰,胡志明走廊的搜索敵踪,險惡緊張,怵目驚心,我們到過柬境,領略到遠征異國的滋味,自然了解那種辛勞危難的情況。戰士啊!棄屍荒野,英勇犧牲,為誰征戰為誰亡?值得敬仰、追悼?還是值得可憐、可悲?唉!誰叫我們生長在戰亂時代?
實在,生長在越南的人民,負荷戰爭的包袱太吃力了,時間也太漫長了,像千斤墜重重的壓下去,幾乎沒有喘息的機會!試想:由十八歲至卅八歲,這段青春活躍的年代,都給軍役制度佔據了,軍役在戰爭狀態下,再無三年四年的期限,而是直至四十來臨,方可退休;如果到時升級至中士以上,那麼,乖乖地繼續服役多幾年,人老力衰,兒女成群,要你退伍的時候,却不願退伍了;退伍等於失業,社會謀生困難,怎樣維持家庭的溫飽?兒子小的必須教養,長大了,又要接棒踏上征途!
這樣情況,後方人才缺乏,影響生產;戰事破壞了市場,生意冷淡;軍事經費龐大,稅收時時增加;並隨時在特別場合,以金錢物質支援前線;人民的生活,焉能不困苦!?
在越南,為了應付北方的入侵,一切以軍事為主。由省長以至保長,一律由軍人擔任或輔佐,這是越南行政組織的堅強陣容!不惜犧牲,努力戰鬥;不僅限於國內,毗連的柬埔寨、寮國也一樣征戰!
然而,人是有感情的,妻子懷念丈夫,父母懷念兒子,幼童思戀父親,少女思戀情人,以及兄弟姊妹、親朋好友間的關切牽掛,家家不免,處處相同。哦!關懷戰地征人,後方百姓是多麼的煩憂啊!為了國家,不是死別,也要生離!
@ @
@
一九七一年三月初,我隨小團征柬歸來,在西寧省廿二號國路的邊防據點防衛,代替了休軍;歷經危險,仍保持無恙,能夠相聚一起的同袍,感慨特多。
有人埋怨巴黎和談為何毫無結果,「和談的地點設錯在花都,如果搬到前線來,在槍林彈雨下,包管他們立刻簽署停火!」
有人說越南成為兩大集團比賽武器的擂台,這是多麼不幸!更有人認為越南全靠戰爭的激動,加速了文明與進步!
有一晚,我不知收聽到甚麼電台的廣播,竟是范文同歡迎周恩來訪問實錄。
我明白了:越戰為什麼不和?印支為什麼亂糟糟?因為在不同主義的列強指使下,將永無寧日。我們居住其中,不知哪時才擺脫這種人為的災禍?
在邊防據點戍守,沒有大規模行軍,每天要嚴密戒備,保衛路段的安寧;這條路如果不暢通,由越南西寧省至高棉磅湛省的各個鄉村,人民的生活都成問題,大部份日常必需品,是靠西寧市接濟過去的。從西寧機場到善言基地的一段路程,最為恐怖,路中經常被對方埋藏地雷,無法防範周到,令人驚悸!晚上,在營地裡,間歇地遭受炮轟,真不堪其擾!
是三月底的一個深夜,我正在守衛,轟隆!驟然第一聲炮就落在更位左邊不遠的地方,可能是炮兵位置和美軍陣地,跟著炮彈像雨打般投下,大有震破耳膜之勢,令我驚悸不堪!轟隆!轟隆!前後都有炮彈聲浪,尤其在更位前面不遠處,連續的爆響著!我的媽呀!觀音娘娘呀!怎麼辦呢?我真耽心始終會擊中自己的位置,防禦工事即使能阻擋部份射力,也難保不會受傷的。
「哎唷!越共爬進來啦!」爆響聲中,驀地聽到李士崇的叫喊!他不斷將M七十九榴彈砲吊出去,阻止敵人的進入。我向外注視,漆黑一片,偶爾弄著了營外安裝的亮光彈,燃燒起來,也看不見敵踪;只有白天慣常見到的,東一橛西一橛的燒焦了的樹幹,我懷疑士崇眼花,始終沒有開火。
炮聲稍為稀疏,我立即跑回八十一厘炮位,負起我接聽傳訊的任務;這時,才知道越共的確已爬入了防線,敵方吊炮是掩護其敢死「特工」的破壞活動;他們從美軍那邊旮旯蠕進來,投擲炸藥,並霸佔一輛戰車,被美軍還擊;美軍實行毀車與敵同歸於盡,被燒焦的有五名特工,餘下幾名趕緊逃走,才爬過我們的防線來!事後查悉,死亡中有一位尉級組長。
平明,視察陣地,,就在我守衛的更位前,發現被投擲幾包炸藥──裹粽子似的炸藥!不知怎的不爆炸,有一名士兵被這些「裹粽」爆得腦漿四濺,好恐怖,好危險,我不禁暗暗吃驚,炸藥的不爆,該是我的僥倖!感謝神靈的庇佑!
不久,負責偵察任務的軍報中隊,在營外樹林邊搜索,活捉了一名特工,原來他們赤裸身體,只穿黑短褲,全身塗抹成黑炭頭,怪不得守更時無法看見。他們沒有荷槍,揹負一個布袋,盛裝著置人於死地的「裹粽」,他們叫做「啤打」(BETA)。
這傢伙是李士崇發現的,他口沬橫飛的述說:「我見到那一橛黑木頭,就認定是人了,他躲在樹頭樹枝堆裡,我立即大喝:『喂!不要詐死,舉手!』後面的人聽見,高叫:『崇!是敵人嗎?槍斃他吧!』違背規律,我堅決反對,留個活口,我對那傢伙說:『你看!我們越南共和國的軍人,仁慈寬恕對待你們,你們為什麼千方百計來殺害我們呢?』他說一切不知情,只奉命行事。我們就把他帶回來……」
唉!他們誓死戰鬥的作風,不知是值得可憐還是可敬?
經過這變故,邊疆的生活,真正驚惶恐怖而又煩悶枯燥。一部分軍人,忍受不住,趁回家渡假的機會,一去不復返了。我的小隊長獲調返師團學習韓拳太極道,我和他握手話別:「能夠離開這個地方,是你的福氣!老實說,我也想離去呢!」
我確實萌生退志。只是,與過去一般,每想到逃伍躲藏,偷偷摸摸,過著牢獄似的生活,諸多威脅,我總是猶豫不決。況且,不幸再被捕捉,送人軍牢嘗那鐵窗風味,及調派出軍隊幹「勞工逃兵」,一味捱苦差,失去了軍人起碼應享的權利,我知道自己無法承受得了。
我正難以抉擇時,小苗芽文友致函給我,他形容從報上登載柬戰情況:「真是令人觸目驚心,慘不忍睹。常常也默默替你禱告平安!」他希望我能夠回去,軍中生涯實在太危險了。啊!真摰的友情,使我萬分感激,永記於心。
那段日子,是士氣最低落的日子。整個指揮大隊甚至整個小團的軍人,都失去了往昔那一股活躍的氣氛!和美軍在一起,更感自慚自卑;越軍樣樣顯得貧困,糧食不充足;美軍則吃喝不盡,每期接濟十分豐富,剩餘下來,都倒出垃圾堆去,多麼可惜。有馬鈴薯、紅蘿蔔、蘋果、雪豬肉以及日常用品。我們不忍暴殄天物,在美軍燒毀之前檢拾回來。盡管小團長一再禁止,認為有失越軍體面,但那些「剩餘價值」頗高,確是增加豐富菜色,誘人垂涎;有時我們實際面臨豉油撈白飯的地步;因而還有人甘願冒受罰之苦,偷偷地去檢拾!
美軍的食品,全由軍部接濟。我們的餸菜,是發餉員每月發出一定的伙食費,由自己或一小隊,或選出代表,或火頭軍,或大隊的接濟員等,去市場購買。(平時紮營可能各大隊的組織不同,故有所分別;行軍期間,一定由接濟員負責。)物價日日高漲,鈔票有限,食品便稀少了。
在邊防據點,大約五七天間趁市一次,去西寧街市。為了安全,日近中天才起程,然後在西寧或返西貢逗留一宵,翌晨才採購食物,中午返回營地。很多次,我代表了八十一厘臼炮隊上市,有許多機會返回堤城;匆匆一夜,也很過癮,聊勝於在那寂寞危險的邊疆!每次回去,一些親友都再勸我「鳥倦飛而知還」,「在危險的戰地裡,一百次幸運,遇上一次不幸,那就完了!」
我仍舊未安排退路,照常返回營地。我把握這上市而回堤岸的機會,曾協助一位不同中團的朋友,離開邊疆返家團聚,因為他的一家大小掛念其安危而寢食不安。至於我自己,却不曾缺席過一天!
美軍方面,除了吃喝豐足外,還有一種娛樂組織,就是每月最後一個星期天,必邀請一團歌舞來表演,以慰勞士兵。表演藝員是美麗的越南少女,最主要的節目是脫衣舞,精彩、香艷、刺激!脫衣舞的名詞聽得多,估不到第一次開眼界欣賞,是在這簡陋的邊防據點;這是拜征柬之賜,也是叨美軍之光!欣賞脫衣舞表演,那美麗的胴體,確實吸引住整個人的心靈,拋掉了胸中所有的煩惱,正合粵諺所謂:「唔知老竇姓乜!」當然更不理會到這個戰事隨時會爆發,炮彈隨時會落下的營地!
脫衣舞表演,當時確曾使人渾忘一切,麻醉了痛苦的軍人,狂呼吼叫,嘻哈大笑!過後,我却感到無比的空虛,似乎欠缺了什麼!想通了,才了解內心所渴望的是自由與愛!行軍作戰,奢求自由,孑然一身,難覓至愛;我開始怨懟,這是從軍以來最鬱鬱不歡的日子。惜珍曾來信勸慰:「不要太為自己煩惱,人活在世上,有時也要相信命運!」我一向能夠正視人生的憂患,難道我的命運就是憂患無窮?
我的意志消沉,加上幾個談得來的華裔兄弟逃伍,尤以曾經和我一起調返軍眷營工作的周有金、吳建森也離去,一些越南軍友不時取笑我:「喂!三人樂隊逃剩你一個啦!幾時輪到你呀?」
「有什麼好撩撥的,遲早我會逃伍的。」
「哼!怕死鬼!」
「不知哪個怕死?戰場上的表現夠了,無須吹噓……」滿肚子牢騷,一連串搶白。
隔牆有耳,言傳快速,竟然傳到小團長的耳朵裡。
一晚,我經過小團長的行轅前,他把我喚住:「喂!怎樣?金和森逃伍後怎麼樣?」
我順著林庭福上尉所指的凳子坐下,然後答:「大尉,他倆逃伍後怎樣,我完全不知。上次遇見森的妻子說他會返小團的,誰料竟然逃伍了。」
「你說謊!」他顯然不信:「我聽說他們去『三號管治單位』報到,然後在家一個月,由某單位領回去,費用是五萬元!」稍歇,他又說:「他們太笨了,很可能人家調他們去東河!」
東河,在中區廣治省,是攻打寮南戰役的大本營。我却認為:「他們有可靠的後台呀!」
他大笑:「人家會尊重『三號管治單位』的報到份子嗎?祇有一個好方法,就是先在外面攪妥好的單位路數,再申請遷轉,那才是上策!」
「那麼,像我這樣申請遷轉非作戰單位容易麼?」我乘機詢問。
「很難說,有時靠彩數。」他又接回話題:「其實,這個時候逃伍最愚蠢,以後的生活更麻煩。」
「這也難怪,大尉不是不清楚,他們當了五年兵,一向隨小團轉戰各方,不可謂不肯捱苦;這回著實太危險了,害怕起來,只有逃伍,保存性命,其他的問題都不及思慮了。」
「如果害怕,不妨直接對我說。我就是可惜他們捱了這麼多年,最後蒙上個逃伍罪名。我們小團在西貢有軍眷營,還有後方據點,以前在嘉黎社的,最近都隨中團搬遷到隆慶了;我有不少方法可以幫助,為什麼要逃伍那麼笨呢!」之後他問:「你害怕嗎?」
「當然害怕!」
「你也打算逃伍吧?」
我坦白回答:「我在外面覺得有一股被壓迫威脅的感受,才肯在軍隊裡捱下去。但我很矛盾,我由到這個小團開始,却又想逃伍了;這次那麼危險,更加想逃哩!」
「像這次戰役的危險,很久才遇上一回,要是時常這樣,我也要逃伍呢!」顯然的,這位仁慈的小團長,不希望我也逃去。他並囑咐我有機會時轉告建森和有金,若回心轉意,肯重新回來的話,他出面向中團取回逃伍報告表,再安置一個好位置給他們。可惜他們一直不肯回來,辜負了小團長的一片苦心。
萬中無一,也許他們不相信有這樣好的長官。實踐諾言,也許小團長覺得要表現自己並非虛偽。大約一周後的早晨,上尉對我說:「我讓你回西貢一個時期吧!不是在軍眷營工作,而是在招募組招兵。這樣,工餘閒暇,你還可以幫助家庭工作。」
我甚為高興,真是個好位置。起先我還耽心他與其他的軍官一般,表面是幫助,實際還附有「送禮」的條件。但這位「大尉福」(越南人習慣稱大尉,不是上尉;先稱銜頭後叫名字,不冠姓氏;像中國古時稱太子丹、太公望一樣),明確表示全無條件的,單單這點表現,更令我對他傾心敬仰!
@
@ @
林庭福上尉將調我回招募組的消息,迅速地傳遍整個小團。隊友們見我獲得小團長的恩寵,嘖嘖欣羨。我更因此心急如焚,大有即刻歸去不可之勢。
日子像蝸牛的爬行,太陽十分緩慢的東昇西落;回西貢的行期杳杳,音訊寂靜,我懷疑上尉改變了主意。
雨季又來臨了。這個低陷的邊疆據點,很難支撐暴雨的季節。美軍就在公路對面的曠野建造新營地;我們也要建築小團駐防所需部份。指揮大隊全部總動員,合力進行建設;單是小團長的堅固「行宮」,就夠忙碌辛苦了。用巨大的四方柱,用飛機場的那類鋼板為蓋,頂上鋪蓋是沙包,四周圍繞也是沙包,挖土、裝包、堆砌,消耗體能,非常吃力;因為是指揮部,必須建設得周密和堅固。做妥了長官的,又到守更的堡壘,最後才輪到兵士們自己的洞坑。我隸屬於臼炮中隊,還要負責安裝那八十一厘炮位和彈藥庫。
新的營地正在密鑼緊鼓的建設,一場無情的暴風雨,把原有的營地弄成處處水窪,那晚大家幾乎沒有安睡的地方。我的洞坑本來是不怕風雨的。地下高墊木板,即使水浸,也不會侵犯到我;入口處可有些微漏水,用雨褸一遮住就沒事了。偏巧建造新營地,洞坑後面彈藥庫上的鋼板都搬遷了,變成大開門戶,狂風暴雨直接吹打過來,吊床和被子全遭濺濕了,不能再安睡,迫使立即動手,將雨褸綁上遮擋,剛弄好時,整個身體已被雨水濺濕了。
轟隆轟隆,雷電交作頻繁;嘩啦嘩啦,雨點不停打下;我總算可以「安眠」。可憐有些隊友的洞坑破爛漏水,有些地低浸水,無法棲身;更慘是正在看更的兄弟,在狂風暴雨中,一面顫抖,一面防守,景況多麼的悽楚!
唉!《邊疆夜雨》(Chieu
Mua Bien Gioi)之歌幽怨迴腸,實際領略滋味,更可悲、更難抵受。
六月初,新的營地建築完成,正式全面搬遷,忙碌了好幾天。之後,又回復沉寂的日子。雖然悠閒,我們却好生耽心,「萬木無聲待雨來」!上級如果認為你們休憩足夠了,必定再次調去接棒行軍的。而此刻,柬戰比前更險惡,從報章的戰事消息報導,越軍在士倫戰役傷亡慘重,促使我們提高警惕!
我們對於越軍退出士倫鎮的新聞,甚為關注,它同是第三軍區的範圍,比寮南戰役對我們更具影響力。報導指出:那地方在柬境第七號公路,撤退路線是越境第十三號國路祿寧方向,士倫大約離棉木不遠。參戰的主力軍是第五師的一個戰團,據說是由於越軍指揮官和美軍顧問意見分歧造成的錯誤。單單是吉普車和大卡車丟棄約十輛,被迫毀壞放棄的一○五厘炮和一五五厘炮,共有十二挺之多,鐵甲車在撤出時丟掉在戰地的不少,傷亡士兵有二百之眾!估計共軍死亡有七百人!從這種公開的報導可以想像得出,這場激戰是何等令人驚心動魄的!
我們小團會不會立即調去行軍?十八師會不會增援第五師的實力?兵士們甚為關心,不斷的談論著;但軍事策劃是秘密的,沒有任何人知道明天是怎樣的。
依然如故,我們還是靜靜地戍防著。六月中旬,輪到我回家渡假四天。如果不計算我在新春偷偷溜回家過年,那麼,由上次任翁東的四天假期至今為止,已是半年時光了;半年才得四天假期,既難得,又寶貴!
短短的九十六小時假期,在堤城一幌而過。我又循規蹈矩的,返回原來的邊防據點。越柬邊疆,又
有我的足跡!
小團長榮昇少校了,精神奕奕,容光煥發;他心情愉快,見我在最沉悶的日子中,不但不缺席偷溜回家,甚而渡假亦依時回營;於是,他實踐許下的諾言,決定調派我回招募組工作。
啊!總算守得雲開見月明,能夠離開戰地,返回後方,多麼值得高興啊!收拾東西,告別小團長、大隊長、中隊長、小隊長以及要好的隊友,拿著事務令,踏上返西貢的路途!由寧靜寂寞的邊疆,回到熱鬧繁華的都市,我身上的每個細胞都輕鬆起來!
本文發表於香港徐速主編《當代文藝》第一○五期,一九七四年八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