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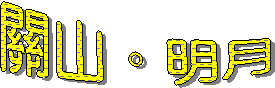
|
||
|
在翠林園的後端,是一片青蔥綠意的公園。 以前經常在黃昏時刻到那裡散步,讓自己溶融在大自然裡,忘掉世間的紛紛擾擾,任由思緒在無邊無際,天馬行空般的翱翔,恍若回到天地初開時,置身虛空。 虛空,才能找到自己的存在。 近年來忙於自己的工作,也極少再到這公園尋幽訪勝了。 那天正值無聊,就動起探訪之心。 不加考慮,換上輕便的衣裝,驅車而去。 到達了公園的入口處,一片濃濃的綠意,已撲鼻而來,加上適才下了場雨,林內的霧氣,於是飄然湧出。那一陣味道,除了是濃郁的樹木之外,更夾帶著泥土的氣息。當兩種味道混凝一起來襲時,所形成的名詞,就是“大自然”了。 公園內,是一片高聳參天的松樹,然後向空伸展,樹與樹之間的枝延,於是在空中互相推擠,只容陽光在葉子推摩的隙縫之間,直透而過,灑下一地碎芒,在草地上搖晃,亂舞。 那是一幅自然界中最美麗的抽象畫。 園內,地勢可是不平坦,於是這廣闊的綠意,就是依山起伏,松林蔥蘢的境色了。 所以走在林中的小道上,心情顯得愜意。 走到林的另一端,又有一個入口。 我想起不久之前,在這座公園附近,建了一座紀念碑和小型的紀念館,紀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殉難於‵死亡行軍′的澳籍軍人。 那是一九四五年初,北婆已淪陷在日本蝗軍的鐵蹄之下,那一些戰敗的英澳戰俘,從新加坡運來山打根,強迫做苦工,修築飛機場。同年五月,兩千餘人分批遣送到神山山麓的蘭腦(Ranau) 集中營囚禁。從山打根啟程,要步行一百五十哩的路程方能抵達,可是當中步行稍慢的,就被槍殺,有的在途中集體被屠殺,有的病死林中。據說到最後,就只剩下六人活著,然後逃到山洞中匿藏,直到聯軍抵達山打根後派團搜尋,這才逃出生天。 這死在路途中的兩千餘的英澳藉士兵,就是北婆最慘痛的「死亡行軍」事件了。 為了紀念這一些殉難的澳洲軍人,於是澳洲生存者發起了捐款,在山打根建立了一座紀念碑和一間小型的紀念館,紀念他們的貢獻和犧牲。 每一年,都有不少的澳洲人前來山打根,憑弔他們不幸死難的親人,獻上鮮花,靜默禱告,以慰在天之靈。 就像清明時節一樣,一年之中,也許就只有這麼幾天,才能到來這裡,哀禱他們的親人,當中,免不了傷感的場面。 這就是戰爭帶來的悲劇。 這一些軍人的孤魂,長年累月的在林中承受寂寞,然而,能夠安息在環境靜謐的松林中,作為他們生命的終點站,也算是有點安慰吧? 他們的犧牲,換來了和平,我想,盡了軍人應有的天職,也該感到驕傲吧?畢竟,他們的血並沒有白流。只是,這一些無名英雄,是否能耐得住思鄉的牽掛?而對頭的山坡上,也留下一些日軍的遺跡,是否他們也像“望鄉”的日妓一樣,恨怨戰爭,做了回不了家的孤魂。 萬里關山,他鄉的明月,是否會格外淒清? 自古以來,月亮,最能引發離鄉遊子的情懷。 關山疊疊,豈能擺渡彼岸? 悲慟,也許是他們唯一所能做的事。 在莽莽蒼林中,除了承受孤寂的煎熬之外,一縷孤魂,只能在深邃的林中,無奈的輕吐嘆聲,與蟬聲附和。 明月,依然在無垠的蒼穹裡懸掛,繼續她的嫵媚,可憐的卻是那一些孤魂,望月思鄉。 思鄉,在每一個月圓時分。 我站立在紀念碑前,默默的哀禱,希望他們魂魄安息。 戰爭,的確是一件慘痛的事,導致多少人被迫漂泊他鄉,家破人亡。吸取前車之鑒,我們應該珍惜太平盛世,共同努力創造國家繁榮。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