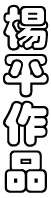
澳大利亞飛鴻 之三
|
墨 爾 本 印 象 1
●初遇俗子夫婦
跟著旅遊團坐12小時車,從雪梨到墨爾本,觀賞了這座城市的大街、地標、附近菲臘島上的企鵝、淘金鎮與十二門徒石,經過三天馬不停蹄的四處奔走,終於,透過在地詩友的幫助,我真高興,自己可以脫隊,以另一種方式去認識這座「文化之都」──說到這點,就不能不感謝幾位朋友。
一是雪梨華文作協的李明晏會長,和他在墨爾本最要好的朋友,汪雲飛先生(名字很像武俠小說中的男主角);只因我偶然出口的一句話,嘿,李會長這位熱心的東北人(哈爾濱)前後打了不下十來通電話,而汪先生亦很痛快的,把一間專門租給留學生的 房子,免費讓我住,使我全然無後顧之憂。 一是女作家俗子夫婦,和年輕詩人甘草。再加上遠在美國「風笛詩社」的版主惠倫兄主動而熱情的推薦,使我們有機會結緣一聚! 因為這幾位素未謀面的朋友處處幫助,不僅使我有機會進一步認識這座城市,也在未來四天,渡過非常愉快、充實的「墨爾本之行」,不能不在此由衷致謝! 看來,詩人雖然平素孤獨,若有需要,無論你是不是徐志摩,也可以像胡適那樣,「相交滿天下」的!
我和俗子夫婦初遇於墨大校園區的一家旅館。 據俗子姊說,她前幾天為我打聽住處時,也考慮到這一家,卻因要求是基督徒而作罷。看來,還是旅行社厲害,不知用什麼辦法打破宗教籓籬──在物質社會的大環境下,對這種無孔不入的商業行為,我能說什麼呢? 俗子夫婦倆個頭都不高,一早很冷,他們穿著外套,舉止言語都同樣的樸實自然;滿頭灰髮的吳先生一路多扮演沉默的護花使者;由一些動作細節可看出,做事專注可靠,相信平時也是這樣;而性格直爽樸實的俗子姊,加上對文學、美食(也因此享受到不少口福,包括此地的龍蝦大餐)的熱愛,相形下,就較活躍了。 他們由台灣來此已逾十年,其子作正也在此成長唸書,目前正在墨大攻讀博士;不論當初選擇墨爾本的原因為何,從她不時歡喜的指點介紹來看,已對此地產生了「第二故鄉」的感情──平時的生活簡單,已養成在這座花園城市漫步的習慣,享受蔚藍天空下,來自一座座綠色走廊的清涼、寧靜、和飄在空氣裡的芬多精;相信就是這等原故,那日儘管飄雨不斷,她還是興致勃勃的領著我去公園──包括日前去過的庫克船長舊居「菲茲洛花園」和「皇家植物園」(這才是全市最大的一座,是世界級的大公園,有湖有餐廳有黑天鵝有曲折小道,較雪梨的「皇家植物園」大,也比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園」100倍像森林);只要想到這一點:藍的蔚藍,綠的鮮綠,大塊的天空,到處林立古老的建築美、身上不時吹著南極送來的風,再伴以百多年來凝聚在大街小巷裡的人文氣質、能不使人精神?活出一份悠然安樂? 同樣在地球,只要讓自己腳下的步調慢一點,對周遭花木的感覺多一些,人生就會很飽滿,甚至不會感染「花粉熱」,俗子姊一家,就是最佳見證。
●●半山的藝術村之旅: 訪畫家傅紅&作家子軒
除了兩座美到不行的公園,那天俗子姊還帶我參觀了一處較特別的地方:一座開放的十九世紀監獄──「老墨爾本監獄」。 儘管氣氛森嚴,吊死過135名犯人,包括當時對富豪特權而言是「惡名昭彰」的耐得凱利(Ned Kelly),一個有如羅賓漢、廖添丁的人物。對大多數的年輕人而言,這可是充滿刺激的地方,雖怕人,也誘惑人;我個人不喜歡的兩個理由,可能是出於尊重生命,並不信任法律的公正性吧。 「這就是生命」,這句耐得凱利在臨刑前說的話,如今已成名言。相信法官、政客、財團、盜匪、藝術家、和為其寫傳記、拍電影、編流行歌曲的創作者與知識份子,都有不同解釋。正義,有時連一杯毒酒都換不來,更別說其它的了。
幸運的是,這已是去日的事;更幸運的是,俗子姊聽我喜歡藝術,特地透過當地一位著名女作家子軒,連絡上在此近乎半隱的一位畫家,傅紅──而他家就像管管、莊普那樣的住在山上,更棒的是,那裡的美與靈氣(我相信是靈氣),近百年來,不斷吸引著藝術工作者來此。幾十年前,也感動了一對法國藝術家夫妻,買下了六畝大的山林,開發成一座私人的「藝術村」,後來捐給國家,目前是由其子孫管理;因為一切都是心與自然的交流,更為此處增添了幾許如詩如畫的人文氣氛──說來,我只是無數驚豔聲中的一名幸運者。
那兒位於墨爾本郊區山上。 澳洲的山和大陸的江南差不多,不會很高,但都美的驚人,綠得飽滿,只要晴朗,直到落日消失前的寒氣都不重;我去過的藍山是一例,此處是另一例;一排排隨著山勢建築的房子,半隱半現的,和台北的天母高級住宅區有點相彷,卻是人與自然的美好而稀有的結合;不是後者的富人氣象所能比擬的。 從市中心開車駛進山來,你先看到一片墳墓,有些雜亂,但並不「豪華」或刺眼;一般而言,澳洲人很實在,不會炫耀什麼,對死亡的態度也不像中國人因積習而流於表面,講究排場。待方向盤一轉,很快的,當俗子姊說看到了,他們正在那等我們呢, 這座「藝術村」已伴著滿山青翠,啾啾鳥語,悠悠然呈現了。 我一顆期待的心,也在瞬間放鬆了──是的,僅僅這一瞥,我底心已溢滿了莫名喜悅! 首先是一幢造型不俗,兩層高的紅磚廳房(我不知是那一時代那一型的建築)聳立在近兩百坪大的泥土廣場前,一對男女含笑看著我們:穿著土黃運動衣,微微有點發福,仍很瀟灑、精神的,就是傅紅,而身旁著花裙,繫長辮的便是子軒──說來好笑的, 直到那時,我都不知自己會遇到何等人物?他們又是何等人物? 我不知道;但我從不擔心。 是的,我相信緣、相信人、相信美會吸引美、善會溶解醜、愛會擁抱所有渴望的眼睛,而大自然一如存在,就是神──我不是尼采那樣的哲學家,也非波特萊爾那樣的詩人,我一向的心思或者說信念,就這麼簡單,可說很莊子的。
我們的會面簡單如同多年老友般,沒有任何客套或隔閡感,只一路清談的隨著他倆從起伏有致、一幢幢大小不等的法式建築間走過去,夢幻般游過去,一方面,我陶醉於這份和自然融合的風景美,幾乎一屋一景,不同的屋內展示著同樣濃郁、純淨的藝術氛圍,一幅油畫如此,一桌一椅莫不是美的化身;而室外流動的山光林景,花,五彩繽紛而毫不傲人的綻放著,每一處綠蔭都藏著一首歌,牆角的小草是精靈,教堂是愛情,水池是 碧玉,鳥雀是音符,天籟不只是山風雲雨,而一株株老樹啊,只要你默默聆聽,便會含淚同意,人間也許不是到處都有香格里拉──至少這裡便是一個! 我毫無疑問的相信,在此已住十多年的這兩位藝術家,他們的獨特、或竟可以說不同凡響的氣質,很重要的一部份來自這裡!
這片綠地,雖近在紅塵邊緣,只因一顆心結合了這裡的蒼蒼鬱鬱、點點滴滴,整個人便也浴滿了這份靈氣──只要想想現代城市人已日逐功利到多麼猙獰的地步,剛過六十的傅紅,儘管他的畫作早為全澳幾十家畫廊代理,卻能近乎出世的在此住上十五年,直到這三年才和外界「社交」;孤獨如梵谷,又享受著高更在大溪地的生活;是的,有福人總有過人的一面。 後來,他請我們到附近的家中小憩,看到不少畫作,用的是油畫,題材以花樹人物為主;色彩構圖都讓俗子姊嘖嘖佩服不已。 其中一幅和人一般大的,畫的是中年裸女,白底炭筆,卻栩栩如生,充滿立體美感;這顯示出極紮實的素描功力,和非比尋常的獨創性。 據他相告,這些畫,都是觀察結合想像力的產品;像那幅裸女,他頗為快意的告訴我:當對方擺好了姿態,便可以離去了──他點點銀白頭髮,全記在這了! 從他的臉上,我完全可以想像畫家年輕時是多麼自負才華,有千丈豪情(似乎還是名躁一時「星星畫會」中的一員);如今,那藹然的笑意、穿林來去的悠閒風度,加上不時流露出三分稚氣的親和感,和藝術家特有的小迷糊,每每讓人忘了他大師級的成就,一如在此,你會忘了時間存在。 是的,時間像一個孩子,會因入夜大街的霓虹和喧聲而迷失,也會因觀看一顆星星、一頭松鼠、一朵水蓮,而屏息消失在樹叢裡•••
可愛的子軒,我相信她以女性的敏感,更能感受這份天地人之靈犀。 從她贈送我的那本散文集「墨爾本:世紀的錯覺」,文彩的細膩感性,你會以為作者該是來自江南水鄉的靈秀姑娘,否則••• 這,當然是另一種錯覺。 子軒是北京人,168公分高,唸得是我最羨慕的北大!她在日子正當青春之際便移居來此,一直保持著苗條身材;與當代許多能幹的職業婦女一樣,做過許多工作,也戀愛、結婚、成為單親媽媽,經歷了她這一代女人的大部份經歷、艱辛、養育、和午夜窗下的寂寞──也因這種種的憂歡,使我更相信、也更敬佩這位,這位綁著長辮子的女作家,她的真情率性固然源自古老的血脈,一份繚繞不散的靈秀,和單純,絕對和這片好山好景有關:當我們一路漫步,傅紅剛剛告訴我這裡除了自然來去還養有一對孔雀,而且就在幾秒鐘後看見其中一隻,正自得的在庭園池邊佇立;我高興的拿起相機便拍──有趣的是發生了,不知是否因美人出現,孔雀居然叫了起來! 曾聽說孔雀遇到比牠美的就會展翅開屏,和對方比美,我便半認真半玩笑的說:「看來牠遇到對手了!趕緊過去比比美吧,」 說歸說,我們這一群人還是往前走去,沒想到可愛的辮子姑娘啊,居然真的跑過,蹲在孔雀前•••而孔雀•••居然真的張開了翅膀••• 這是她天真的一面;等我們在畫家家裡閒聊時,她又殷勤的讓座泡茶,忙裡忙外的,顯示了她另一面的熱情;直到另一群朋友來訪,而俗子姊一再提醒我待會還跟人有約••• 我又不想走,卻不得不離去了。 這山、這村、這人、這份近乎透明的天然美啊! 我好幸運、好幸運好幸運••• 最幸運的是,我知道自己並沒有真的離去。
(2005年12月1日寄自悉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