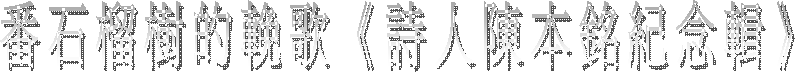
2000.9.28
新大陸詩雙月刊2000年12月第61期
|
新大陸詩訊 ● 原《新大陸》詩雙月刊創辦人兼主編之一的詩人陳本銘,不幸於今年九月廿八日因癌症病逝於美國加州阿罕布拉市仁愛醫院,享年五十四歲。詩人生前對海外華文詩壇(特別是越南和美國)貢獻良多,直至去世前猶創作不輟。詩人喪禮於十月八日在洛杉磯中華殯儀館舉行,采佛教儀式,詩友前往致祭者衆,備極哀榮。 ● 另遠在越南的詩友亦同時爲陳本銘在胡志明市天虹大酒店頂樓舉辦燭光追悼晚會。《新大陸》本期並出版《詩人陳本銘紀念特輯》。
|
|
陳本銘簡歷 ◎李雄風撰
詩人"藥河"──陳本銘,一九四六年出生於越南堤岸,原籍廣東省恩平縣。曾就讀於博愛學院、戴高樂法語學院、明德大學,畢業於美國洛杉磯 LA Trade Tech. 學院美術設計系。
陳本銘少年時,愛好中國畫,更醉心於現代詩的創作。爲六0年代越華文社的活躍份子,和當時的銀髮、趙中中、尹玲、吉子、斯冰、秋原等交往熱絡,家中成了文人的聯絡站。
本銘篤信佛教,曾和當時的年青法師甯雄、惟日、今三以及畫家陳賓陽、張達文等籌組"華宗佛教青年會",參予廣肇醫院的重建及創建正覺學校,並曾執教鞭作育英才。
七四年進入新聞界,七八年和夫人李美庭結婚,女兒約緹於七九年誕生。後來無辜被捕勞改。八九年獲得特別庇護來美定居,和詩友陳銘華等人創立《新大陸》詩刊,推動海外現代詩運動。九四年初次癌症手術養病,九八年再做治療擴散手術。日後身體雖日漸消瘦,而詩作卻增多了;直到2000年九月廿八日,和癌魔搏鬥多年後與世長辭,留下給文友無限哀思。
"文章千古事",陳本銘一生對現代詩的執著奉獻,將會隨著詩的傳誦而永遠留在人文的記憶中……
|
陳本銘遺作十一首
心 經
(心經段落)
經卷裏住有
一首未完篇的詩
漬有唇瓣的致瑰血印
離叛的網道交駁在行字間
幹預著我的早課
(心經段落)
那人在南方的南方
那人在西方的西方
那人在
無論哪里的哪里
都駐錫在我血液的氧內
任何時刻
使其紅
便澎然紅起來
使其成浪
便捶擊我的木魚
以錚的語言
反彈自我面向的岩壁
(心經段落)
天雨衆花沾染我身
月白袍服鍍上夕陽顔色
心經攤展在夜露的蕊心
記憶中的一朵淚
沿著時間荒蕪的大臉
從西貢某個市鎮
漂流至阿罕布拉的下城
(心經段落)
我攤展自己
向天空如一卷經文
衣袍卸在落花之上
謐靜 好大的鏡面
可以
照我河床底下的休憩
照我族人海上
比驚濤更驚駭的神色
流落的魂魄在水中
舉著棱骨的手漂浮
看每夜升起的月
落下的月
油然記起故鄉野地
漫遊的燈籠
炮擊之前
冉冉落下的照明彈……
(心經段落)
木魚時時裂著傻笑的口
一副數學家的態度
默算你一捶一擊
敉平受想行識的暴亂
經常的來客
──致死亡
面對著你,我仍然活在,無異幽了你一默。
當我不在的時刻,卻幽默了自己。
我知道你會來
你會來 遲或早的問題而已
因爲你是經常的來客
企圖偷竊我的記憶
趁著完全柔軟的一刻
有時候 你坐坐就走
或者我們以沈默聊聊天
但你的眼神總那麽專注我的
等待它光采殞滅嗎?
而且拒絕我預備的飲料
我知道我家的
茶 帶點香味的暖
咖啡是燙口的濃鬱
而你屬於冰冷
我昂高的談興讓你沒趣
當你訕訕地要離開
我只好打住話頭 說
:有空再來
九八年十月十一日
從一匹頭髮想起
從一條頭髮的彎度
白成蘆花夾道的鄉路
轉折回到曾經國土
你在彈窪裏吊唁倒影
無以名之的遊魚冒上來
爭噬著
你戰時的少年臉孔
從一管頭髮的密度
中空成越洋的隧道
時間 站在彼端
蒙著臉露出凝神的眼睛
看你在浪的白牙出走
鹽漬在銹蝕的身軀
風不停撩撥昔日的黑髮
一片流亡的土地
龜裂著
你中年麻痹的臉孔
而後從一匹頭髮想起
那人在井前滌洗的體態
虹和拱橋的線條
在木杓的水聲裏拔起
你後現代的扭曲塑型
九八年八月十五日
釋
我的背面是一爿藍
沒有投射的影子
影子 一逕地動亂著
企圖掙脫我腳跟下的疑纏
在天光下自由行走
清淺的綠在背後
葉子借著風
把晨間顛覆爲午後
露珠摔下來
雀鳥四散飛起
時間
爲了釋放自己
碎了一地
九八年六月十八日
一口窗的五種景致
一、霧封
雲的姊妹們
絕早便湧去窗臺
隔著玻璃喧囂
那些白晰而擠得變形的臉
如著了魔
在一場米高傑克遜的演唱會裏
我把帷幕落下
免得那些尖叫煽情
慫恿我捨身躍下
二、雨來
序幕是輕雷
隱隱沈沈鼓的定音
惹得蹄聲 馬匹
被風勢所驚而嘶喊
這便是兵法裏的拂曉攻擊麽?
趁夜來思鄉失眠
鐵和血漸次解溫於
誰家越錚
的一曲邊疆晚雨裏
*〈邊疆晚雨〉是越戰時期南越政府禁止公開演唱的歌曲之一,理由是靡靡之音會瓦解將士們的抗戰意志。
三、月升
似乎
所有的聚光燈都一一熄滅
賽事完了
勝者敗者從熱熾
和灰冷裏整頓賦歸
縱然
The game is good game
徒然拉鋸了好幾個OT
最後還是暮鳥四散
只有旁觀如我者
發覺那黃澄澄的
球 不因寂寞而
冉
冉
自升
九五年三月廿三日
四、晴放
陽光
先是一記鈐印
猛地捺在
左上角
的白色建築和棕櫚之間
遠山悠悠從夢裏返回
還略添宿醉的紫淤
俄而 陰陽立判
賓主分明 佈局是
上方留著無極的青空
懸住
腳下千鈞的房子和樹
這便是你
由時間背後
寄來的明信卡麽?
風暴數天
怪不得色差顯得那般兀突
九五年三月廿四日
五、日正
靜止還原於靜止
喧鬧騷動是沒有倒影的
凝鏡在日正當中
似乎只有
一些蒸發的意象
企圖搖動景致
時間 固體的一條水
滯流於感覺間
我突然想起時下一窩蜂的詩
題旨如落花
墮溷墮茵儘管煞有介事
不妨從題目略開去吧
水落在下
石出在上
你說
所謂隱題詩者
當如是讀
九五年三月廿四日
後記:九四年五月底患直腸癌,手術後每月必須住院四至五日作化療。醫生說療程一年。今年三月底照例住進阿罕布拉市的仁愛醫院,算算時間我在這裏已十進十出了。院內清靜,每個病房建築格局和擺設大同小異,但都有一口大窗可供遠眺近觀外邊景致,這組小詩就在不同的病房面對每口不同開向的窗醞釀寫成的。每次入院,我都背了一個背囊而去,那樣子像是去露營,囊裏除了必需品和衣物外,全是書籍、詩集和校選給詩刊的稿件。我住的是單人房,一切活動都不會影響別人,讀書、看電視、聽音樂、寫詩、校稿皆自由自在,唯一的牽系是靜脈血管裏拖著針藥,長長的塑膠軟管盡頭連接兩座藥控器,使我頓覺人的軀體皮囊不過是在死和生之間漂飛的紙鳶,而生和死的那種牽系往往關係薄弱,??須輕輕一斷,豈非更大自在。
九五年三月廿八日
番石榴樹次篇
偶爾轉側 葉影
便變更剌青的位置
額上 臂上
甚而恣意齧著
弧度袒露的背彎
那是一株時常結果的
番石榴樹
澀時淺青 熟時
絳紅帶有澄黃的核籽
他唯一癖好
從午後到黃昏
收藏琴聲和
耳語的隱私
然後
拖著露臺的倒影
送你上遠眺的樓頭
我摩托車的後燈
明滅在夜霧
以外 層層橡木林子
九五年三月十五日
榴 槤
迥腸的三公里路上
我和雨競相疾走
我想。
在雨裏回來真好
最少你不覺
風塵狠狠橫越
我著意修飾過的臉上
忙不疊印乾發緣的漬水
寬衫晾在
木樓當風的窗檻
在雨裏回來真好
我想。
那忙亂是一種沁透的憐惜
你竟然失覺了
挽回來的一匝香息
三公里外的
留連在
爐火的背光面
九五年
之 前
──給DT
洪水之前想及火
城破之前想及愛
灰燼之前想及手
手是昨夜撤離的夏日
執著一莖自焚的玫瑰
越過季候的邊界
河涸之前想及雪
燈滅之前想及雨
死亡之前想及你
你移動在光影反差裏
掠起遠近記憶的囂塵
透逾宿命的藩籬
這一切
這一切之前已經許諾
時間窄門中
我們牽手走過呼和吸的斷層
水 殮
我喜歡
癢癢的唼喋
一千萬張
吻別的唇瓣無言
吞吐成漩渦
吸我入你腑髒
再世時
我滿意自己是汽泡
仍然所謂
虛無主義
我喜歡軟軟的沈陷
一浪浪
搖我入睡
搖搖 搖著說
漾開去發膚肢體
飲酒寫詩的
腦神經
淪爲你的支流
或者主流
我滿意
湯漾的分解
貼切生前身世
我喜歡這樣
溫溫柔柔的磨蝕
遠行
其實並不離去
九一年八月十七日
螢 火
來不及驚叫
刷一聲
天 便黑下來了
??因爲想及西貢
故鄉
停電的雨夜
來不及說Cheer
一口酒便將
月亮
骨嘟灌下肚裏
你我
便可以回去
這樣
打著螢光
手電筒
九0年七月十一淩晨
第八日
……上帝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
──創世紀第三章第三節
翌晨,我著手
展開我的創作
以痛苦爲骨
喜樂爲肉
欲和潔淨
爲生命紋身
並且趕及在子夜來臨前
竣工,
是爲第八日
一九八九年
張錯‧秋恨
每次離別
都是當年慣用方式
不著言語 □只
一泓霧裏上路的眼色追隨
──陳本銘〈行香人〉
想不到過了中秋,你就走了,那種恣態,頗似張愛玲,沒有愛戀或怨懟,只有,我想,是對人生一種無奈與漠然。九月廿八日晨你走,我一無所知,當晚深夜乘機赴台。十月回來,檢閱舊報,因副刊曾告知四日會上一篇短文,抽閱之下,赫然發覺我倆同台演出,只是這次你以身殉,以訃聞方式告知世人你已遠遊,並且一去不返。
方寸大亂之餘,我強行收拾悲痛,並以一貫沈默與冷酷,開車上路。已經過了午後時分,造化弄人,天不讓我們見最後一面,我默然無語,一一處理日來擱置已久的公務。世間諸事本是如此,你在悲苦別人在快樂,但是快樂的別人不但無知於你的悲苦,同時還期待你與他們同樂。相反,有時難得樂在其中,喜上眉梢,卻要講解莎翁四大悲劇,那又是另一種大煞風景心情。暮色深沈,慢慢沈澱著我們交往回憶,雖是短短數年,卻是香醇清冽,頗堪宿醉。
當然要從《新大陸詩刊》說起,這是一本在美國唯一定期出版詩刊,當初你和陳銘華倆人就是台柱擔綱。我看到不只是詩的愛戀,而是詩的堅持,猶似愛情,相悅愛戀容易,日子堅持便困難得多。在困厄的時代,人文沈淪,功利交煎,許多所謂堅持,更經常流入孤芳自賞危機。然而記得那夜和內子赴約,和你與銘華相會,一夕長談,讓我另眼相看。因爲聽到的不止是海外詩人艱苦歷程,或是越南華文詩歌辛酸成長,而是一段不折不撓學習與追尋。我長年海外飄泊,相交作家數以百計,然而許多時候,往往是你知道他們地方來歷比他們知道你的多。即使來自臺灣本土,那種脫節情況也會令人目不忍睹。中國現代詩發展,自五十年代台灣便是一股主流,雖然一道曾與五四傳統脫節,成爲白色恐怖犧牲品,然而血濃于水,藕斷絲連,曾何幾時又是從無到有,帶動中國抒情一脈傳承。
驚訝的我,面對著你們倆對臺灣現代詩壇種種往事的熟悉,侃侃而談,遂而思考到另一個更嚴肅課題:詩人語言可以以國籍劃分,但同一語言的創作,國族藩籬便需突破而追求民族溶和。其實海外詩人那分得出那麽多越華、菲華、美華……?如果同屬華語系統,即使文化背景殊異,也無足影響共用有的互補共性。固步自封或自大於自己源流,將更自囿於更大局限。同樣,許多海外華人文學,往往著眼於共相的“海外”,而不知全世界殊相的“華”,才是力量的凝聚與挑戰。
寫到這裏,秀陶來電,談及與你種種往事,感觸良深。在洛杉磯,我和秀陶,算得是碩果僅存的臺灣詩人,共同分享臺灣現代詩一段過往,那種感情也算得是相濡以沫了。在美國,無論西岸或東岸的城市,臺灣詩人數位均以基本奇數計算,如果能算以偶數的兩個,便算得是衆多了。但在洛城《新大陸詩刊》凝聚的一批海外詩人,有如百川彙海,亦頗曾熱鬧一時。最能令人緬懷是一九九五年九月九日中秋,籌辦了一個〈以詩迎月:今夜星光燦爛〉的中秋節現代詩朗誦晚會,遠道來自舊金山的紀弦、康州的鄭愁予、西雅圖的楊牧、聖地牙哥的葉維廉,以及洛城本地的你和銘華,我和秀陶,在長青書局分別上臺朗誦詩作。由於銘華和你的努力及協調,不但把活動辦得出色,更出版特刊,把那夜誦讀詩作及詩人介紹編印成冊,讓在座聽衆能夠以閱讀補朗誦之不足,我曾這樣記述:
其實這次現代詩歌朗誦晚會的詩人組合,已展露繁複文化背景結合的端倪。許多詩人不止具有臺灣詩人身份,同時亦是海外詩人,另外,這次參加演出的洛杉磯本地的新大陸詩社成員三人,除秀陶原有的台灣身份外,其他如陳銘華、陳本銘更帶著越南華裔詩人身份,他們與臺灣及中國大陸的詩歌運動更息息相關,血肉相連。
是的,就是這一夜的中秋,以及它的永恒,帶給我長久不息的震撼顫動。張愛玲逝世於前夕,我經常願意這樣想,如果她知道,並且還存活,一定也願意,以平常百姓心情,做一個普遍在座聽衆,以詩歌來洗滌市居煩俗的心靈。至少,我的朋友胡金銓那晚便赫然在座,全程參與,沒有高談闊論,只有默默聆聽。
而那本特輯封面,就是由主修美術設計的你來設計。許多人沒有留意或不知道,那晚在長青書局門前迎風飄揚一面簾旗,有如牧童遙指杏花村的酒館,也是你的貢獻。
你的病情我早有所悉,因此格外留意你處世與詩的呈現,那夜除了本文前引的一首對生命如履薄冰的〈行香人〉外,你還讀了一首短短的〈風想〉,並引用禪宗“非幡動,非風動,仁者心動”的典故後──
衣衫獵獵
摺疊驟起的鐘聲
早課經文兀自翻騰
如夜來輾轉一燈
靜默焚燃肉體
應無所住的
花
落在潔亮腦袋
阿彌陀佛
早年飄灑的
發
自在無礙
我的朋友閻雲醫師在“希望城”醫院工作,曾告知兩刃之劍的“化療”效應,我想,就有“如夜來輾轉一燈,靜默焚燃肉體”吧。其中亦包括脫髮,因而讓詩人想起──花與發,皆是空相,“落在潔亮腦袋”。
後來發長回來了,儼然沒事人一樣,依然自由飄灑,打球、寫詩,做喜歡做的事,我所知大概如此,極爲有限,飄泊的我,常常覺得莊子的無情,實是至情。這一群海外飄零的人,有國難投,有家難歸,有如魚群涸於陸地,與其相濡以口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因此,我經常保持著一份不得不如此的遙遠,但望能有知音,于相忘中保持一份不敢相忘的信念。然而事與願違,譬如年初開始曾被一連串病魔纏繞,雖是折磨,亦無大凶,然而近乎半年的折騰與困擾,讓我有如隱入山中雲深不知處,而不見諒於他人。到了深秋,在露水濃郁夜晚,常有一種秋恨,那種感覺,就像李商隱的一首〈暮秋獨遊曲江〉:
荷葉生時秋恨生
荷葉枯時秋恨成
深知自在情常在
悵望江頭江水聲
荷葉榮枯,有如生命許多歡聚與離恨,然而春去秋來,江水長流,生命的許多情份,仍然倚賴著一個短暫無常肉身!這真是最大的諷剌與無奈。朋友,這篇〈秋恨〉裏和你說的話,比數年相交所說的話加起來還要多。你是廣東人,我奔喪來遲,就讓我引唱一段白駒榮的〈客途秋恨〉來送你──
涼風有訊,秋月無邊……今日天隔一方難見面,是以孤舟沈寂晚景涼天……耳畔聽得秋聲桐葉落,又見平橋衰柳鎖寒煙。觸景添情,懊惱懷人,愁對月華圓。
黎啟鏗◎ 瀟灑而來 瀟灑而去
本銘,你走了。你走得突然。雖然你的走是在大家意料之中,我們總有一份不甘不忿,不舍不依。我們更佩服你能夠把一場一般只能玩六個月的生命的牌局,漂亮地足足玩夠六年又四個月。雖說癌是穩贏的莊家,你能夠以有限的本錢,以小搏大,憑著堅毅的勇氣以及不撓的鬥志,按牌理亦不按牌理,打出了一張張出色的牌。我們知道,你有信心打贏,正如你相信日新月異的醫學科技終能戰勝癌症惡魔!只可惜你極度虛弱的身體等不到有新藥發明的一天。隨著時間的磨蝕,你的賭本愈來愈少。而按照遊戲規則,賭本輸光了就必須離席,縱然你預知下一局你就會拿到好牌把生命贏回來。人生就是這般的無奈,失望也罷,哀痛也罷。來到美國,你千辛萬苦,好不容易捱到了美工系大學畢業,正準備幹一番事業,卻霹靂地從醫生那裏得知患上癌症這個殘酷的事實。癌,擾亂了你生命的節奏,粉碎了你人生的美夢。一如在越南,你曾經被共產黨關進監獄,複被轉押至偏荒的地方去接受勞改。面對人生的橫逆,命運的播弄,你卻始終保持著對人生的希望,對生命的憧憬,對理想的追求,對正義的堅持,對寫詩的熱情,對愛情的執著;浪漫瀟灑,樂天知命。而你一生坎坷的遭遇,正好加廣加深你對朋友的熱情真誠,對貧弱者的關懷,對被欺壓者的同情。更值得一提的是,你那種不屈服,不妥協,不容忍,不畏縮,不逃避的性格,是衆多朋友所欣賞的一條漢子。
本銘,你真的走了。癌一直纏著你不放。六年來從未間斷的化療,雷射療,放射療等等,一切可行的療法都已經試盡,你亦被折騰到苦不堪言。但是你從來不哀鳴,不怨歎,不頹廢,不放棄。甚至當你得知癌細胞已經擴散到腦部的時候,你仍然信心滿滿的相信自己還有十年可活。你拒絕死亡,正如你拒絕放棄對癌症進行的殊死搏鬥一樣。
記得在你臨終前的一晚,我還跟你在電話上交談,你說你感到很疲倦,恐怕後天不能去見王育梅和她另一位也患癌症的朋友,要我代你取消約會。是你太太後來告訴我,那天晚上我們通話之後不久,你便陷入昏迷狀態,翌晨送院搶救不及,病逝于阿市仁愛醫院。
安息吧,本銘。安息吧,詩人。每個認識你的人都懷念你。你只是放下了多病的軀體,並沒有帶走你燦爛的音容。你的性格,你的作品,將永遠深植在衆多親友和讀者的腦海裏。而你快速的告別方式,比之經年累月呻吟床榻的病人,何嘗不是你修來的福氣。也像你的性格:永遠拿得起放得下,瀟灑而來,瀟灑而去;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萬峰‧悼藥河
我仍沿著江湖的春水*
你卻駕乘蓮台的彩雲
還記得
少年十五二十時
同年 同硯 同行
我仍沿著江湖的春水
你卻駕乘蓮台的彩雲
曾經是
青年的共同志業
課室 操場 教鞭
我仍沿著江湖的春水
你卻駕乘蓮台的彩雲
最難忘
盛年 歲月被蹂躪
散離 尋覓 渺然
我仍沿著江湖的春水
你卻駕乘蓮台的彩雲
意外地
中年天涯再重逢
暢懷 愉悅 激勵
我仍沿著江湖的春水
你卻駕乘蓮台的彩雲
突然間
長年與癌魔搏鬥
養病 奮起 長逝
我仍沿著江湖的春水
你卻駕乘蓮台的彩雲
低吟著
四十年草堂禪唱*
蓮池 極樂 再
會?!?!?!
九月二十九日於臺北旅途
*本銘兄曾為我寫過兩首詩:〈沿著江湖的春水〉與〈草堂禪唱〉。
非馬‧未成熟的秋
──悼本銘兄
就讓被摘下的
你
這樣子在我心頭
青澀
也許有一天
你臨終的手勢
瀟灑如落葉
飄旋
你最後的歎息
滿足如熟果
墜地
而我的心
秋日般
寧靜
2000年10月12日於芝加哥
心水‧哀吊詩人藥河
昨夜鈴聲說你風一樣
飄走了,我恍惚神離
苦苦追憶六月三日那天
洛杉磯重逢,我們歡喜了
整整一個永恒的下午
輾轉床笫期待那
“整畝城市的燈火”
沒有被你一手撚熄
今早我彷如夢遊者
希祈在空間另度磁場裏
再碰上你,好把你每種表情
神態聲音細細刻印
我尋尋覓覓,總想將兩次相聚
縫合在心底,忐忑的抽出
你的詩集捧讀。總是難信
死別來得如此突然
離去之前,你用生命
“孕育的一首詩”是否已面世?
後記:括弧引自藥河詩句,闊別二十多年的詩人西牧深夜來電,驚
喜中卻傳達藥河噩訊,心如電殛。在越南神交,九一年旅美初遇詩人
,今年六月再蒞洛杉磯知藥河已和癌魔抗爭數載,精神頗佳,不意詩
人英年早逝,如風飄走。關山遠隔,未能送殯,謹以此詩遙祭詩人在天之靈!
二千年十月八日於墨爾本
榮惠倫‧風裏的驀然回首
──悼念藥河船長
杏花村的酒早已熟了
烹茶的冷泉卻冷著
不在乎拗折天下人嗓子的*
那漢子 兀自不在江湖
坐看水雲鄉
山山的憔悴襲袖而來
風裏 驀然回首
曾經的飛觴酒令 潑墨詩籌
笛卷琴停歌歇
秋遊的鳥銜住多病的菊
蝴蝶夫人醉醉的扶著黃花瘦了
一溪楓落 化千只的船隊
船上旌旗笳鼓 軍容浩蕩
數千羽衛 萬衆兵甲
帳裏 獨不見孫吳
(一冊航海日誌
出發自湄公河的水湄處
巡弋至 南加州的港灣
漂泊了逾半世紀的煙硝流離
以及笑拈些些灑脫的情迷
終於告別了地球儀的切線
寫上句點 再沒有電子郵址
也錯失了羅盤座標與星圖)
您 亙是存在是虛無
亙是星辰是河嶽
是嶺外的半壁大川
是一灣江流一帶的荻花
一奕棋便足足圍觀一個千禧
您真的叩訪了五柳先生 是嗎?
或者已驛馬六朝的棧道
篋裏的 晉帖 宋詞 唐詩呢?
兀自敻遠的滄溟 水田阡陌
月冷三更 情懷舊雨
臨一瓣心香 怎耐得住
那萬籟的露寒
*摘自《四方城》詩集藥河自題。
千禧年十月脫稿芝加哥
藍兮‧番石榴樹的輓歌
──悼念詩人藥河
十多天前你還伴著另一半,歡度伊的芳辰,
而你竟在自己生朝前獨個兒走了。
清晨醒來
總得把頭
朝向軟枕
輕叩
就叩這一下
感謝昨日
整整的一日
是賺來的
你說
豁達就看到坦途
還可以寫詩 駕駛
和打籃球
走時想定必瀟灑
偶爾也會因體力透支
摔交的時候
優閑裏愛翻閱宋詞
陽光在番石榴葉間灑下
挺詩意的庭院
滿庭的葉影
恣意的在你額上
臂上 或背彎上
剌青
今晨你忘了叩謝
賺來的昨日
你已在枕上
折騰了一夜
無眠
這回真的走了
也不揮手
你摩托車的後燈
明滅在夜霧
以外 層層橡木林子*
*最後三句是藥河佳作〈番石榴樹次篇〉結尾三行。
林德功‧燃燈的人
──紀念本銘兄
我不經意的望向天空
一片白雲輕輕飄過
懶洋洋的氣候
這一刻人生的主題已不重要
朋友走了,後園的紫菊還盛放著
還來不及告訴你
朋友走了,如一本徐徐合上的書
再沒有新的篇章大家傳誦
去年我來洛杉磯
亮麗陽光中有你暖暖的問候
詩人笑得仍然燦爛
而且計劃,回故里走走
探望你心中一直記挂著的
再生的城──西貢
千絲萬縷的故事都始於此
美麗而且四季如春
適宜戀愛,亦適宜失戀
詩人也不免疑疑纏纏
鴛鴦蝴蝶畢意只爲了賦寫新詞
讀書、寫詩、寫畫……
這大約是你最滿意的日子了
戰爭什麽時候淡入以及爲了什麽
很多人不知也不想知
“答案,我的朋友
在風中飄揚
答案在風中飄揚”
反戰的歌重覆地唱
像岩穀的迥響發人深思
想一想,戰爭無論對錯
總是叫人流淚……
此刻你已不再寫畫
工筆的蓮花開在心中
有人四處奔走如驚慌失措的灰鴿子
有人只遺下零碎的日記
書信和蒼白的軍裝照片
並且將自己的名字
雕上了冰冷的碑石
路人經過望望
還不知什麽一回事
那人已匆匆走完了一生
希望與朋友,就如好的天氣一樣
令人可以舒適的過日子
洛杉磯是你最後駐腳的地方
而我一直歎服
寫詩未敢言倦的你
緣何此際,你放棄了詩
放棄詩等如放棄了一切
或許你只是換了另一角色
逍遙自在,把詩點燃成燈
“譬如一燈燃餘燈
其明轉多……”
黃奇峰‧詠 蝶 ──悼藥河
生命的嚴冬尚在遙遠
您就追隨秋的涅盤西航
短短的一生
留下令人思念的翩翩躚躚
追求詩美的飛天
沒因現實的花蜜少而喟歎
衆生在您的眼瞳裏
沒有輕重貴賤之分
默默接受命運的擺佈
從未怨天尤人
悄悄地您來,好一道天虹
悄悄地您走,乘著蓮台的彩雲
我們吟詠您的生命詩行
您的風采永在我們的思念
輓 詩 二 帖
西牧寄自多倫多
藥石難轉靈 惡疾招天魄
河山悲淚落 流向雨中餐
劉保安寫於加州
藥石難回天 可憐惡疾折斯人 六載翻騰未嘗怨苦
河山應落淚 今賸圓檯共殘椅 滿庭葉影替誰剌青
陳澄海‧老友之死
有一條河流
名爲生命之苦澀
沿著歲月的斜度
邐迤入海
這旅行的人
從容整理生命的行囊
似無一丁點迷思
好讓這趟行程
亦帶點喜悅
其實
他才告別西貢的繾綣
苦難亦未遠離
卻又流入另一永恒的傷口
這中年的宿命
的確如此無奈
那是一九九九年八月下旬的故事
我與他在熾熱的洛杉磯並面
他熱情揮手,衣著略顯蓬鬆
歡宴間
偶而會說
這裏的風情其實也很慵懶
女人都很濃妝
這次他決定離開加州
忘掉五十歲以前虛構的風華
只是不曉得老友走的時候
是否還帶著河流對兩岸的依懷
了無牽挂
2000年十月於臺北
懷玉子‧悼念藥河
走了藥河 西貢雨夜有如翻開日記的黑洞 混沌淒清
撒下網頁撈到的竟是直腸癌?,如何去追悼
Key in你的名字E-mail到我們的懷念
那漢子寫詩成疾?,把脈方城四壁早已無可救藥
過盡千帆,你已駛入湄江現代詩的歷史長河
十二人詩輯?的對奕尚有半局殘骸,怎麽說走就走
面對任何惡魔也不能拍拍屁股就一了百了
是拂曉攻擊或退守陣地都要備妥炸藥
免得敵軍潛越對岸的白藤河
春節從巷戰而肉搏,兩軍交鋒於和談的聲東擊西
匿藏閣樓的詩句竊笑拉夫的警官,炮聲隆隆的西貢
反正都要投下炸彈,那還管是誰的士兵陷於沼澤叢林。雨
是唯一存活的投機分子。守候明天不知死活的漫漫長夜
倉皇辭廟──詩是通過移民新大陸海關的僅有
洛杉磯是不勝負荷的床,纏綿顛覆我的裸體,宛如
一場無聊的戰爭。醒來一腳踢翻
排山倒海撲面而來的鄉愁,往事的密碼被解開
說好要選擇我們共同尋覓兩岸的國慶日
不能老是持雙程綠卡每次都要辦理入境登記
已準備好詩袋和行囊,空下的
籃球場留給誰?垂淚的蠟炬又怎生得黑
你永遠爽約了。剩餘像岩穀的大空洞
異鄉可以流落也可以鬼混
美工藝術許諾了描繪大地初開的混沌
你已經一手撚熄整畝城市的燈火。遺留淒淒
清清
2000.10.18. HCM City
詩人藥河因直腸癌於2000.9.28病逝,我們透過E-mail第二天就知
道他的惡耗。記得1994年我們曾經在LA見面,當時他還在美工學系聽
最後一個學期的課程,還說要安排回西貢和大夥兒相聚的。
“詩疾無救藥,情愁卻成河。”是杜風人對藥河之喪撰寫的挽聯。
也因此觸發筆者寫下這首“隱題詩”的動機。
十二人詩輯、水之湄、像岩穀、空下的籃球場留給誰、我的裸體、
四方城、新大陸詩刊等等……詩集、散文集或詩作,都是藥河出版過、
參與過或寫過的作品題目。
後記:事隔卅餘年,美國前國防部長麥納馬拉(Mc Narmara)寫了回
憶錄;終於公開承認:“美國介入越戰是一項錯誤”。然而,無論從
生命或精神上造成的傷害已經無法彌補;當年我輩詩文同好的朋友,
對警察拉夫(抓軍役)的陰影都會尾隨我們這一代的餘生;因此,何
時才能生活在“免於恐懼的自由”環境中,是我們一直追尋的目標。
而兩岸的統一也是我們近代中國人的理想!讓我們細讀藥河在《四方
城》題壁,他提出了極爲悲痛的警語:“我們都是在人類自造的災禍
中成長。同時,我們亦確信這災禍將會以任何形式繼續存在於人類的
社會。這可能就是我們執著寫詩的最大理由了。”對於藥河的這份執
著,我們謹致以至高無上的敬意。
冬夢‧河水道別詩聲 最後的迥響
──悼念本銘兄
河躺著千千萬萬個未宣的心事
水解開成浪
道別稀僻蜿蜒的去路有否雪劇風深
別忘記添衣禦寒
詩永遠暖熱的不孤寂的伴你同行
聲容的官能皆可表達感受的存在
最接近你想必是一片霽晴
後移的蒼穹
的確易於翺翔易於
迥旋大千世界
響澈晨暮爲你不舍依依送行的佛鍾
後記:一九九八年赴美洛杉磯曾跟本銘兄相晤,多年未見,人略清減唯身體態況尚佳,據其透露部分藥物足可控制其癌病,兩次飯聚後回港。今年臨近中秋佳節的某天,我心血來潮去電給他,正值友人替他作物理治療,緣因清晨下床頓感半邊身軀劇痛,交談間他仍興致甚高圍繞著未來的種種詩事大計。豈料世事無常難測,其心願仍未遂圓,己遺憾聞悉本銘兄遽然離世長辭的消息,悵惘傷惜之餘,謹以此詩祭悼詩魂,還有我對本銘兄永遠的一份懷念。
2000年10月寄自香港
陳國正‧雲不再流浪了
──悼故友藥河
十月有淚洗刷過的天空
流浪的一朵雲疲累了
虹是否你問道的小橋
或乘風歸去
確實你去了,去而匆匆
十二年前是一個錯誤的揮手
的可能
我似看到含滿眸
鄉愁汪汪
如秋荒涼
你的臉
呵,你的臉讀出風霜
至於今夜,淒其蒼茫
風蕭蕭兮
堤城又在雨中
藥河呵,就這樣
你已翩翩走過今世
雲不再流浪了
雲的故事已寫入詩章
留給人
吟
誦
讓山山海海去緬懷
越南28/10/2000
藍斯‧有一條河
尋捕如煙雲般渺著
飛的感覺
而意象中老早就酡醺
驚驀一片翺翔的空間
化作詩
可以不恍不覺
可以唱吟
可以調弄出一條擰也擰不乾的
有一條河
叫藥河
銀髮‧送 行
──悼念藥河
如節日的煙花那樣
開向厚實的夜空
長途巴士
紛紛從總站向東南西北開出
因遲遲才發現的癌症
你被安排到一輛
沒有回程的長途巴士
我 清 楚 見 你 回 頭
唉 你不要留戀自己這輛殘舊的
老爺車了
既被動了手術
又幾乎被放療化療折磨成
一片秋葉
前往西方極樂世界的乘客請立刻上車
請立刻上車
送行的親友
親友
請保留最美好的回憶
最美好的回憶
不要指望重逢
重逢
我清楚見你回頭
猶有不舍的
神色
2000年10月27日于越南胡志明市
杜風人‧藥 河
──悼念陳本銘詩友
二十四載重逢
一握手即切脈
首次 卻也最後一次
觸及你六脈斷層的體溫
脈裏 陰陽之間
虛懸而執著
一根芤而澀的瑈弦
反彈出天籟造化
弄人相生相剋永恒的無奈
再深切觸及
你淒美如詩的心脈
遂發現 瀕臨絕種的詩的DNA
複製了你一生
唯與杜康夜夜獨酌
始斟酌出:
詩疾無救藥
情愁吟成河
注:一九九八年與內人返越路過洛城,藥河、斯冰請飲茶,並載我們到黎啓鏗家小聚。當時藥河的直腸癌在接受化療,我給他把脈並處一方,且指著我那王八的腳說:“走一步算一步,過一天賺一天。”如今,卻害得我要爲他寫詩,奈何!
石羚‧詩疾無救藥 情愁卻成河
詩是不曾死亡的生命
疾病只徒然昇華我軀體
無須看世界自眼前走過
救我繆思沈疑,何必從
藥石著手
情愫題在山山之外的一軸
愁縈
卻又不能買舟歸來,吐
成繭的心事
河川故園-未圓的韻腳
二OOO年悼藥河
李志成‧泅在自己河裏的人
──悼念藥河詩友
往事 一排木柵的
排列著
驀然 你的影子
在當年風雨飄搖中
清晰如螢火
傲桀如那只
在荒野獨行的野狼
真奇怪啊 此刻
我竟能忍受
你咀嚼冰塊的聲音(1)
一如你的不悔
呆憨地追覓
傳說中的衣帶(2)
中年未過 人未疲憊
怎麽先把自己
躺下成河 河水滾滾
你的歌聲
就在水流處升起
四方合攏
彙出一股共鳴的掌聲
那個人
那個泅在自己河裏的人
讓我把你的音影
摺成蝶 安放
在四方城中翩舞(3)
讓我叩開斑剝的城環
當風起雨霪時刻
來到 你幽居的庭園
一壺茶 迎來
一片瑟瑟風雨聲
你我 再次暢談
平生事
2000-10-21
(1)每當冰飲時,本銘有咀嚼冰塊的習慣。
(2)爲詩爲愛,本銘在越居室,名爲“不悔樓”,取其“衣帶漸寬終不悔”之意。
(3)《四方城》是本銘與遠方,達文和陳銘華三詩友合著的詩集名。
秋夢‧三十二行
──悼藥河
大江東去
浪濤肆虐
你這一曲癌化的直腸
你和病魔掙搏
扭纏過多少歲月
雖有靈芝爲伍
亦難抵禦那死神
的逼迫,病榻上
你是一尾被剖割的魚
人生舞臺上
你匆匆退下
不留結局
死亡之前你想及的愛
以及其他
死亡之後,你曾否想到
身後的草冉冉如寂寞(1)
如今啊如今
你的靈魂已脫離
遊走在空間,行止
如風的行止
經過潮濕的蘆葦和乾燥的草葉
帶著沙啞
唏噓的步音
在一線微弱的
燈光下──
你的軀殼,是一道
乾涸的河流
偃臥如一個空洞的人(2)
空洞,空洞(3)
空──洞(4)
我們用悲哀將你緊緊填滿
唉!藥河
(1)(3)(4)是藥河的詩〈空下的籃球場留給誰〉 裏的一些詩句。
(2)艾略特(T. S. Eliot)的一首詩作The hollow men的譯名。
2000年十月廿五日越南
余問耕‧半 局(1)
───敬悼藥河
籃球場上
彷佛 見你接球之後
熟練的左右手交叉運球
瞬間越過迎面而來的攔截
彈起投籃
動作一氣呵成
乾淨俐落
一如你率性流露
盡情演出的詩作-(2)
賽事方半
到底是什麽樣的主宰安排
哨聲響起
你竟出局離場
任四座譁然驚愕
十二先行者的心血有待重定(3)
野狼的嗥聲未徹(4)
繆斯的蜜約頻仍
球場之約未踐(5)
多少心懷未了
你竟遽然撒手而去
剩我獨對球場
憤然追問
放療化療之外
何以再無仙丹靈藥
阻你進入忘川長河
歸來
再續這未完的半局
(1) 半局:原出於張曉風散文集《你還沒有愛過》,悼念其亡友之作品。
(2) 與本銘兄初識于聖心籃球場上,時兄乃老爺隊最年輕最帥者,我爲少年隊隊員。兄赴美後,偶于銀髮兄家得睹照片,始知銘兄乃我慕名已久之詩人藥河。其後書信往返,蒙寄贈《四方城》合集。“率性流露”一語見該詩集中所載其詩觀一段。
(3)一九九六年,藥河兄與越華現代詩壇先鋒等出版《十二人詩輯》,爲越華詩壇第一本現代詩結集,兄本有意重刊。
(4)兄有意創辦《野狼》詩刊。
(5)兄信中有“回堤與你們再打籃球”之壯語。
盧寒星‧揮不去 您寂寂詩魂
──悼念藥河詩友
生命滴答結束
卻是詩魂延續
您總是綻出無奈
卻是我恒遠追憶
愛不再 恨不再
巴黎浪漫不再
羅馬瀟灑不再
吉普賽流浪夢
您曾否一再戳破
洛城一彎殘月
也曾盈 也曾缺
也曾編譜變調的哀歌
千帆之外
曾是您夢幻詩海
彼岸漁燈點點
您的抱負何在
悄悄來 悄悄去
您曾否踏破串串悲哀
詩夢已破
莊周驀醒
總是 揮不去
您寂寂詩魂
2000年十月廿九日越南
餘弦‧寄藥河
秋末很秋
銀髮傳來一個太秋的訊息
西去的你已西去了
天呀! 這麽短促?
你還會“想著……”嗎?
“那麽默然的展開一卷唐詩
便發現了很多的星子到遠方去旅行”(1)
我低下頭
深心隱隱作痛
太短促了
五十五年華
記得你曾:
“用混血語言去打賭明日
用紅臉去爭論你的詩
你的詩內的一隻字眼”(2)
於是落葉堆滿我的心坎
數不清
你曾以多少美麗的句子
撒播著
從南國到新大陸
可惜你帶走的一定更多
金甌的秋夜
沈重的秋雨陣陣
而你陣陣地把我喚醒
“鬥酒、談詩、寫我們的大寫意
而且嗑嗑非常相思的瓜子”(3)
原來是連綿的舊夢
“堤城空著……
許多的咖啡或者啤酒瓶
都不得不靜止”(4)
爲追念你:
悠悠的“藥河”
2000年秋末于越南金甌
(1)(2)(3)(4)是取自藥河於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夜寫的〈想著……〉的一首詩中。
秀陶‧記本銘的喪禮
──2000年10月8日
當我們抵達時看來一切都已舒齊都已就緒。我們當然不知這都是誰的主意,誰的安排,或者誰的陰謀!然而就這個架勢看來,生米是已經煮成熟飯了,一切都不可後悔了,不可逆轉了,一切已不可撤走了,不可以再回去幾年或者幾個月幾天都不可以了。總之當我們一抵達時一切都已經太遲了
也有過一瞬間我弄不清楚這到底是誰的喪禮。我去靈後看你,看躺著的那人一點也不像是你。你從未曾把頭戴進那樣的帽子裏去過,也從不打那樣的領帶在脖子上,至於那樣畢挺的上裝更是……還有面色,是的還有那紫紫灰灰的,那是煮熟後擱置過久的芋頭
靈前十幾個人站在那裏一邊敲敲打打,一邊鬼叫鬼叫地也不知是誦經還是念咒,而後他們就圍著你繞行起來。我看到你的妻在啜泣(他們僅稱她一人爲未亡人,這一整廳的人都亡了麽?),我看到你的獨生女兒也眼紅紅的(他們稱呼她是唯一的遺族,這一整廳的人都是你不遺下的,都是你要帶走的?)今天凡同你有關的語言文字都出了問題,念詩的念不成聲,我站起來想說幾句話,結果也被自己的語言載到不知去了那裏,只有蠟燭仍燃著,香仍在冒煙
才不久以前,我們常把長長的夏午虛擲在圖書館對面那間牙買加女人開的小咖啡店的半樓上。我們咒駡一切令我們深受其害的主義,一切死硬幫幫的意識型態,以及各式各樣的宗教(把他們集中擺出來就比商展還熱鬧),同傀儡戲出臺樣好玩的各種儀式,我們冷峻地在這一切中去找尋他們的荒謬,去找尋他們附生的詩趣。我們全然未理解到我們自己的無聊,全然無知於只要我們內中能□動起一絲愛意,這一切還是可以容忍,還是可以原諒甚至還是有其必要的。就像我今天抱手凝坐著,就像你今天瞑然的靜躺著,細細地咀嚼這一場特爲你而排演的自有人類以來便一日不曾缺失的喪禮
然後我起身繞著你緩行一圈,我一邊踱著一邊默數著我的步子。我存想著這一圈完了,如果落在雙數上,我可以任由你就像那樣躺著不動;要是落在單數上的話,你將乖乖地替我站起來,咱們還有話要說……呵!這時候我是多麽的渴望這世界是真的有神又有鬼呵
Nov. 2000, 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