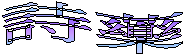
我在一次紐約文化界集會的發言,引起全場嘩然,後報以熱烈掌聲。不久,紐約報紙上刊登一位僑領的文章名為《詩藥》,說是聽我發言後才第一次得知有“詩藥”這個詞語。
其實這“詩藥”,非我首創,早有人這樣說了。
醫學研究說,人在情緒不好時大腦會排出去甲腎上腺素,
其毒性不亞於毒蛇之毒。並說如老人痴呆症、帕金森症、憂鬱症三病首發於人的第一大腦。2000年諾貝爾生理及醫學獎獲得者瑞典阿維德•卡爾森(A.
Ca. rlsson)美國保羅•格林加德(P. G reengard)埃里克•坎德爾(E
. K andel)三位科學家在研究腦細胞間信號的相互傳遞方面獲得了重要發現,提供了治療和預防這三種疾病的構想,方案有四,其中第三方案的大腦療法的第二點就叫做“詩藥治療”。
美國心理學家勒納提出“吟誦詩歌可以改善心理情緒狀態,進而增進身心健康,達到治愈疾病的目的”。“誦讀,更有通過音符來振盪頭部氣血的作用。而這種作用除了調動眼、耳、嘴三個器官的功能外,還通過呼吸及音符振盪等因素,促進肺部、腦神經及腦血管的運動”。意大利米蘭醫院神經科醫生帶領病人朗誦美國詩人朗費羅的《生之禮讚》,刺激病人細胞活躍,使之能安睡、增進食慾。該醫院就詩藥方面有一套完整的治療計劃。西方有德國詩人海涅的《讚歌》可治憂鬱症,英國詩人濟慈《睡去》可治失眠症一說。
這並非新鮮事,其實中國早已這樣了。 曹操讀陳琳的討曹檄文,“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不覺頭風頓愈,從床上一躍而起”。 (見《三國演義》第22回)。陸游亦有詩云:“心扶一老候溪邊,來告頭風久未痊。不用更求芎芷湯,吾詩讀罷自醒然。”
現實生活中有許多例子可作證。最近聽紐約詩詞學會董事說他有一朋友車禍後低智能了,醫生要他吟詩寫字,三年後人恢復常態。這其實是人的心理對生理的作用。
但我一貫對此不以為然,以為不外是老生常談。直到自己不但耳聞而且眼見甚至身體力行了,才悟出其中真諦。
李時珍的《草本綱目》沒有“詩藥”這一味,但那詩可入藥確實一點不假。有我父女為證。
家父活到102歲,直到去世的那天是睡著走的。沒什麼致命的病,只因老了食道功能不好,醫生要動手術幫他進食。當護士告知當日下午要動手術時他卻在上午十一時半睡去了,永遠的睡去了!
父親工作到80歲才退休,一生無別的愛好唯獨愛詩。他與詩人創辦的紐約四海詩社,為紐約最早的漢詩團體。人數不多,當時的詩人大多在餐館衣廠商店打工,他們於1984年發動全球詩賽,從世界各地投來的詩共708首,初選入圍佳作200首,最後得獎的50名,特別獎有三名(其中得優異獎的還是一位南京詩人徐美君)。靠僑團資助居然還有能力頒獎。事後出詩集名為《四海詩聲》。父親是這次詩賽的最後評選人(共三名)之一,當時他96歲。那時的《聯合報》每周有一專欄登漢詩,父親的詩幾乎周周見報。他寫詩寫到100歲。為賀他百歲壽辰,我們給他出了詩集為《韜光樓詩詞文集》。父親遺作,最近登在北京的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的《傳世孤本•經典詩詞》。
記得父親9
6歲時,醫生這樣說:“陳老先生各方面的器官十分正常。這與他寫詩有關。因為人老,腦先老,腦常用就不易老。”這句話我記住了。我想,父親若不因我母親辭世而擱筆,他還可能多活幾年。
我小時候因父親硬性規定要背唐詩,那時幾歲大不知唐詩是什麼東西,還以為是甜的。後來,把它當歌仔唱。因為父親教的不是朗讀而是吟唱,直到現在我還不會朗讀只會吟唱。這樣越唱就越上癮。上癮之後隨著年歲漸增就愛上它了。於是躍躍欲試。不倫不類地也學人家寫古詩,拿給父親看,說“詩”沒平仄,那時還不到十歲懂什麼平仄,以為把一句話用七個字形式出現就是詩。如果自那時起有父親在家教著,那多好。可惜,我11歲半就一個人在廣州長大,家人先到香港後到美國了。以後我學寫詩的路就艱難得多。但在心境不平靜時我仍是從詩中找寄托,有時背幾句唐詩或學寫幾句古詩,心境即時舒坦了、平靜了。
這樣,我就自我療傷。如我在當“準右派”時,聽人們不斷重復的批判稿聽厭了,我在心裡背完唐詩就唱《秋水伊人》,這隱私當時不敢說。
來到美國,甘作人梯而又不甘於埋沒自我,讓我心裡十分痛苦。記得有一年年三十晚,掙扎於飢餓線上的我,晚上打工後回家,適逢當日下了美國百年來最大的一場雪,雪都到膝蓋了。很多人在家吃團年飯而我獨自行走在寒風呼嘯白雪紛飛的紐約街頭,忍不住邊走邊流淚,這時,腦海湧現了如下的詩句----
瀌瀌銀霧重雲破,漠漠西城滾白波。蹈地舞天翻雪屑,飄花飛絮裹松柯。
寒衣難掛避風港,薄履耗尋安樂窩。人有佳肴過歲晚,余惟獨唱採蓮歌。
回家後飯也不煮,先把它記下了。飯後再修改平仄
,詩成了人就一覺睡到天亮,不然我會因此失眠。失眠時真有點“為安一個字,耐得半宵寒”那種感覺。最怕是已耐半宵寒了,仍未得一個字。
為作詩,我燒爛三個電飯鍋,有時竟會拿著空碗往嘴裡送飯。至於連大銻鍋的湯都可以燒焦的,那就別說人家把手錶表當雞蛋拿去煮了。那些以酒代油、以鹽代糖是我烹調的絕招。至於邊炒菜邊唱邊吟的,倒是外子聽慣了,不然,人家還以為痴娘掌廚。詩也害我好生狼狽,於是,家裡就多添幾個電飯鍋、水壺。
我天天晨跑,出發前必讀一首唐詩,然後就邊跑邊背。這是人生一大享受!那唐詩和著跑步的節奏自然合拍,十分有趣。有時看到眼前的景像腦裡又湧出一些詩句。如我在背杜詩《登高》,剛好在冬天,見街上的樹光禿禿的,十分蕭殺,恰逢上百只鳥哀鳴。我停下來在樹下呆呆地望了許久,於是幾句詩在腦海浮動,趕緊跑回家連早餐都不吃先作詩,就這樣寫了《哀鳥》----
忽然一夜冷霜回,老樹驚寒葉遇災。昔日枝盈天帶綠,今朝幹毀地無苔。
失窠聚叫聲尤竭,有翅難飛淚復哀。似訴風神休再怒,繁花艷土報春來。
有時發夢也作詩。半夜爬起來閉著眼把它記下,天亮了繼續作。那《筆上南天門》不少句在夢中跳出來的。
我天天就這樣生活,連年初一也這樣。有一年,命運安排我住醫院。記得有次見醫生時心裡恐懼得很,一量血壓,升到從未有過的140/90,心跳也是從未有過的一分鐘120下。護士說我太緊張。我想把自己放鬆,逼於無法,就背白居易的《琵琶行》。同一天的我再到另一個醫生面前時,一量血壓116/70,心跳一分鐘86下。護士連聲叫:“good”。當她叫我走時我毫無反應,還在背《琵琶行》。它太長,不是一下子背得完的
。
這樣的數據讓我堅信詩的作用。於是在我被送上手術台的那天,我有意在詩中求解脫。天未亮護士把我推進手術房,途經的走廊很長,只聽見輪椅車輪的響聲以及護士的腳步聲,一時感到肅然,不知不覺就發出這樣叫喊:“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我不敢往下背了。
於是,下決心自己做一副對聯,想到朱元璋給屠戶撰寫那副春聯,取其意套成我的上聯“一刀剖開生死路”,我急於想下聯,怕我萬一跟刀走了,這聯語想不出來就死不瞑目。我在琢磨句子的平仄。口中念念有詞,護士在問:“May
I help you”。我不懂英語不回答,還嫌她打擾我。人已躺在手術台,耳邊響著護士在搬弄刀叉的聲音,我一點也不知道怕,還在那兒平平仄仄的。身邊的護士在瞎瞪眼,他們在說:“What
happen?”我終於在麻藥起作用之前作出下聯。不由得高興地念著:“一刀剖開生死路,兩手攥住鬼神情。”
不知後來什麼時候把我麻昏了。開刀後一陣劇痛痛得我從昏迷中醒來,醒來時我第一時間就背我作的那副對聯,背著就忘了痛。害得家人以為我被麻壞了哪條神經。
開刀後第二天被護士提下床學走路。這時痛得直冒冷汗,於是又找詩來幫忙。一步一痛還在哼哼唧唧,回到病床把它記在紙上再反復推敲,出院後再修改,這首《路》就算完成了——
地轉天旋豈有窮,水雲渺渺萬千重。凡間早有艱難步,世路尤存險惡峰。
峭壁何堪人絕履,懸岩哪懼鬼無蹤。崎嶇小道群生走,君影巍然獨壑松。
傷口在痛我就笑:“知道痛就是人在活著。”有人吵醒我,我也笑:“睡在有人聲的地方就不是永恆的靜。”持這樣的心態,一下子就睡著了。只要一到白天就想詩,連餐紙也寫滿詩句,病榻上零亂的詩稿,是我養病唯一的精神寄托。這不,住院六天一眨眼就過了。醫生說我是出乎意料的恢復得最快的一個。
出院途中,人有仿如隔世之感,也顧不得車子顛簸害得傷口更痛,越這樣我就強迫自己作詩,把沿途的感受記下。回到家的第一時間,就急著把這些詩句“吐”在本子上。我往往把這叫做“吐詩”。一旦“吐”了,喉嚨就舒服,心境跟著平靜了。
此後的養病日子,幾乎隔一兩天就作一首詩。我想自己被詩弄得六神無主了。不過,我還得感謝它!是它,陪伴我與死神搏鬥並度過那漫長的養病日子;是它,使我得以康復,贏得了新的生命。
飄來的一兩句未成型的詩句,其實是人生軌跡在我心靈深處的沉澱;是情感波濤在我血液奔流中的積習。它把我深刻的印象、強烈的感受化成一種精誠,一段激情。而這情往往是因我在人生世相中見到的東西而發,或是即興的,或是懷舊的。這種喜怒哀懼的情緒形成一種飄來忽去的心境是那樣的難以捉摸,卻又那樣令我或興奮、或憂鬱、或難過、或喜悅。這時我不得不沉靜下來回味這種突發的情緒,冷靜地把它置於一種客觀的觀照對象。慢慢地分析這種情緒的來龍去脈,它的素質、它的精華或糟粕。
音樂可治病,詩亦然。只要腦細胞在正常運作,趕快背詩,平時背多了,什麼時候用它都有它不同的作用,不要說自己老了記性差就不背了,請看這則新聞:
“廣西馬山縣加方鄉加讓村獨山屯的藍昌榮老人,七年前曾因悲觀失望而尋過短見。就在他萬念俱灰的時候,大孫子給他買回一本《唐詩三百首》。書裡的字雖然很大,但他辨認仍十分困難,臉幾乎貼到書上。當時,他已八十五歲,記憶力衰退,看一首唐詩,幾乎沒留下什麼印象。老人來了犟脾氣,記不住就背下來。孰料,今天背得滾瓜爛熟,明天又忘得一乾二淨。他索性每早四時三十分就起床背詩,而三個小時才能背十句八句,到了白天又忘了。他反反復復地背,每天除了吃、睡,餘下時間全部用來背詩。
五年後,他把《唐詩三百首》全部背會。背著、背著,眼前出現一幅幅動人的畫面。自從他迷上唐詩,精力逐漸充沛,聽覺也有所好轉,還可以走二十餘里路不歇息。如今,他又開始背《新編千家詩》。”
看來,我還比不上這位老前輩。
2007.2.12寄自紐約
北京詩人王耀東2007.8.28箋注●●●
南京張子清教授:
葆珍詩人,寫詩,寫散文,還寫有各種情趣的雜文,她寫了一稿詩是藥能治病,我把此稿下載下來,給一位86歲的老詩人艾砂,他很感動。如果將葆珍散文編一個冊子,在大陸出版,並配上你的幾幅畫面,也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此僅是一個建議。祝好!王耀東8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