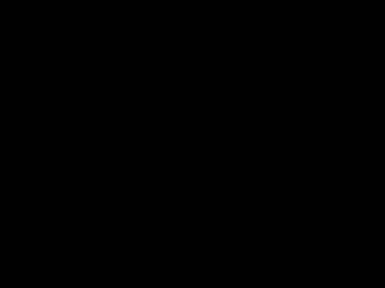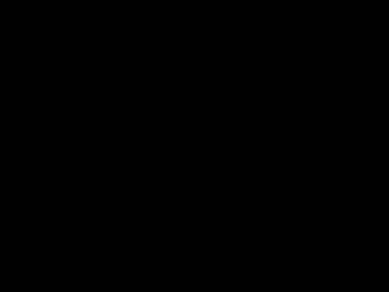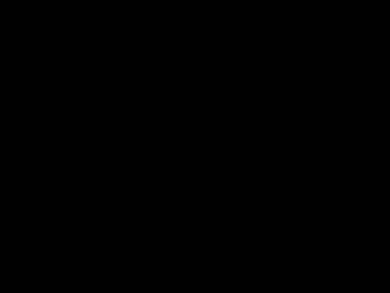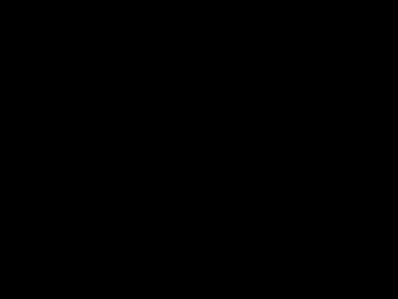|
|
|
前 言
2013年5月25日到休士頓參加兩個會議的活動,一個是給當地的美南華文作協做專題演講"動了凡心",
該會成員大多來自台灣;
另外是給國際新移民作家筆會當評審,這筆會的成員清一色是大陸來的,我是唯一的老移民或舊移民.演講會星期六下午在中國城舉行,新移民作家筆會的會員也全部開了一個多小時的車來聽,反應相當熱烈.他們說早年對台灣的詩很感興趣,在學校時也讀過我的詩,覺得很喜歡,但後來大陸詩界炒來炒去都是那幾個人的名字,覺得有點厭煩,連帶地對台灣其他詩人的詩也冷淡了下來,聽了我的演講後似乎又燃起了當年的激情.晚上給新移民筆會擔任詩會評審時,這種激情似乎還在瀰漫,第一名之外,臨時又增加了兩個第二名,她們(都是女的,以前寫過詩,現在都主要在寫小說,其中的閔安琪用英文寫小說,在美國及英國成為暢銷作家)都說回去後要好好再開始寫詩,深以能得到我的認可為榮,並開玩笑說要在她們的簡歷上加上"首屆非馬詩獎獲得者".我說能點燃大家對現代詩的興趣,是我的快樂與榮幸.
======================================
歡迎訪問 非马新浪博客+微博 http://blog.sina.com.cn/feimablog 非馬的部落格 http://blog.udn.com/marrfei 非馬臉書 http://www.facebook.com/profile.php?v=feed&id=1044066430
非馬藝術世界 The Art World of
William Marr
動了凡心
◆2013.5.25在休士頓美南華文寫作協會的講話 http://home.comcast.net/~wmarr9/2013houston-speech.htm
非常感謝劉昌漢會長和陳瑞琳會長的邀請。我常羨慕休士頓華文界的蓬勃活躍,經常舉辦各種文學活動,相形之下,我們芝加哥就顯得太冷清了。看了這次新移民華人作家北美筆會的贊助名單,我才明白原來這裡不但有一批熱情的作家及讀者,還有一批熱心慷慨的華人企業家。這是很可貴也是很難得的。
首先讓我解釋一下今天這個講題。1998年我參加在香港《明報》世紀副刊上一個叫「七日心情」的專欄寫作,這個專欄由七位不同地區不同背景的作家輪流執筆,記得其中有大陸的余秋雨,不久前去世的香港的也斯,還有台灣的張曼娟等。那時候我正嘗試我的“夾詩散文”的寫作,在每篇文章裡嵌入一兩首短詩,便拿這個專欄做試驗場,聽說反應還相當不錯。後來我把這些文章編成一本書名叫《有詩為證》的散文集,黃永玉先生替我寫了一篇題目叫做「動了凡心的和尚」的序,說“詩人如果是和尚,和尚如果有時動了凡心去拈花惹草,那就是散文。非馬的散文。這就是與眾不同的奇思妙想的散文。”我把書稿交給台北的未來書城出版。沒想到正要買機票回台北參加新書發布會的時候,卻突然傳來出版社關門的消息。後來我把書稿轉換成簡體字,找廣州的花城出版社出版,出版社覺得《有詩為證》這個書名不夠吸引人,建議從黃先生的序裡取出《凡心動了》這四個字作為書名,在2005年出版。前年台北的秀威出版社出版的《不為死貓寫悼歌》是這本書的繁體字版,加上我最近幾年寫的一些散文。
我猜黃先生用這樣一個好玩的標題,多少是在幽默我這個人有點不安份。因為他在序文裡還說:“非馬是個奇人,是個寫詩寫散文的非馬,又是個原子物理學家的馬為義;還是個做雕塑和畫畫的美術家,這就似乎是個企圖搶掠多類行當飯碗的剪徑強人了;一個充滿憐憫心的強人。”
其實我並沒有甚麼大的企圖或野心。當年在台北工專(也就是現在的台北科技大學)念書的時候,覺得課程太枯燥,年青的心靈需要文藝的滋潤,便和幾位同學創辦了一個叫《晨曦》的文藝刊物,由學校供應紙張,我們自已編寫自己油印自己發行。碰到稿源不足的時候,作為主編的我就寫些東西包括散文小說詩歌去填補空白,我的第一首詩便是那時候的產品。工專畢業後去接受預備軍官訓練,然後到台南一個新兵訓練中心當排長,訓練一期又一期的新兵。有一期的新兵裡頭有一個出版過一兩本散文集的文藝青年,看到我在帶兵打野外的時候也偷空閱讀文學書,便提起他經常發表作品的一個文藝刊物,並介紹我同主編認識。後來又經由這位主編同當時住在台中的被稱為天才詩人的白萩見面。但在我離開台灣來到美國留學之前,我只發表過一兩首徐志摩體的詩。
在美國的頭幾年,忙於學業及工作﹐又要談戀愛結婚生小孩﹐沒多少空餘的時間去接觸詩。後來生活比較安定下來﹐剛好白萩那時候在主編帶有濃厚鄉土味道的《笠詩刊》,希望我能利用地利,盡量多譯介一些剛出版上市的帶有泥巴味汗酸味人間味的詩集,每期留了大量的篇幅給我。就這樣,從美國詩開始,後來又擴大到加拿大、拉丁美洲以及英國詩人的作品,還有英譯的土耳其、希臘、波蘭法國和俄國等地的詩,幾年的功夫我一共翻譯了將近一千首,相信這些譯詩對台灣詩壇的發展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可惜結集成書的只有幾年前台北書林出版的一本叫《讓盛宴開始--我喜愛的英文詩》的中英對照詩選,以及一本法國現代詩人《裴外的詩》(Jacques Prevert, 1900-1977)。
在我翻譯的美國詩裡面,有一首詩經常提醒我並警惕著我,那就是女詩人狄金森(Emily Dickinson,1830-1886) 所寫的〈我是個無名小卒!你呢?〉:
我是個無名小卒!你呢? 你也是個無名小卒? 那我們可成了雙──別說出來! 你知道,他們會把我們放逐。
做一個名人多可怕! 眾目之下,像隻青蛙 整天哇哇高唱自己的名字 對著一個咂咂讚頌的泥淖!
它告訴我,做一個自由自在的平凡人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另外對我有相當大影響的是美國意象派詩人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1883-1963)。他是一個小鎮上的小兒科醫生,他的許多短詩便是在看病的空檔用打字機敲打出來的。雖然他從未正式參加過任何派別,但他可能是美國詩人當中讀者最多的一位。我很喜歡他一首叫「場景」 (The Act) 的詩:
玫瑰花,在雨中。 別剪它們,我祈求。 它們撐不了多久,她說 可是它們在那裡 很美。 哦,我們也都美過,她說, 剪下了它們,還把它們交到 我手上。
我常引用這首詩來說明我對現代詩的一點看法。我認為一首好的現代詩,應該留給讀者足夠的想像空間。詩人的任務只是提供一座舞台,一個場景,讓讀者憑著各自的背景與經驗,隨著詩中的人物及事件去發展,去想像,去飛翔,去補充,去完成。它可能是生活中的一個片段,一個人物剪影,一段對話或一個心靈風景的素描。不說理,不自以為是地去作闡釋或下結論。因為我們的經驗每人不同,每天每時每刻都不同。讀者可根據各自不同的經驗與當時的心情,去獲得不同的感受。這樣的詩是活的詩,不斷成長的詩,歷久常新百讀不厭的詩。像這首詩,作者沒告訴我們詩中的男女主角是什麼關係。是夫妻呢?或是情人?剪下玫瑰花的「她」,是年華己逝的女人,看不得別人美呢?還是抱著憐香惜玉的心情,想讓盛開的玫瑰,在我們心目中保有最美好的形象與記憶?而「我」為雨中玫瑰求情,是純粹的愛美呢?還是另有隱情?比如說想到了新交的情婦。如果是後者,那麼女主角絕情的一剪,還把剪下的帶刺的玫瑰花交到「我」手上,便大有殺雞儆猴的味道了。總之,短短幾行,可能性卻無窮。這便是詩,豐富耐讀的現代詩。
一邊翻譯一邊吸收營養,漸漸地我自己也開始寫起詩來。在不是故國的地方寫詩,面臨的最大問題,除了文化的差異之外,便是:用什麼語言寫?為誰寫?寫什麼?這些問題當然是相互關聯的。當時雄心勃勃的我,確有用英語寫詩,進軍美國詩壇的念頭,但很快便體悟到,如果思維仍習用母語,那麼最自然最有效的詩語言應該是自己的母語。用第二語言的英語寫詩,無異隔靴搔癢。語言確定以後,自然而然地,漢語讀者成了我寫作的對象。當時美國的漢語報刊不多,刊載現代詩的副刊更少,而大陸的門戶還沒開放,因此台灣的讀者成了我的主要對象,旁及香港及東南亞等地區。對這些讀者來說,美國的題材雖然也許可能產生一點異國情調或新奇感,但不可避免地會有隔閡;寫台灣的題材吧,對住在美國的我來說又缺乏現場感。在這種情況下,寫世界性的題材成了比較好的選擇。深層的原因當然是我一直相信,任何事物,只要深入它的內部,總可以找到一些能同時感動許多不同種族、不同膚色、不同歷史、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年齡、不同性別或不同職業的人的東西。作家的任務,便是挖掘出這些事物的本質以及廣義的人性,想辦法把它們完美地表達出來。下面這首短詩便是我當時的一個嘗試:
共傘
共用一把傘 才發覺彼此的差距
但這樣我俯身吻妳 因妳努力踮起腳尖 而倍感欣喜
一位詩評家在談到這首詩時曾指出,雖然我們可把它看成純粹的情詩,一對年輕的情人撐著傘在雨中擁吻的甜美鏡頭,但更可把它推廣去涵蓋所有的人際關係。如果社會上的人與人、團體與團體、國家與國家、宗教與宗教之間,都有這種相互體諒、彼此調適愛護的精神,我們這個世界一定會更祥和更可愛。
我寫詩寫得最勤快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美國華文界,八十年代是詩的黃金時代,至少對我個人來說是如此。陳若曦主編的《遠東時報》副刊、王渝主編的《僑報》副刊以及曹又方主編的《中報》副刊,都大量刊登過我的詩作。特別是陳若曦,她登得快,我也寫得勤。
前幾天我收到馬來西亞一個大學女生的來信,說她正在研究我的作品,要撰寫論文。她問我認為自己的詩大多屬於什麼類型?我要她參考廣州花城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這本由海南大學的唐玲玲周偉民教授編著的《非馬藝術世界》,書中分別由詩、散文、翻譯、繪畫與雕塑各方面來檢閱我的藝術世界,並把我的詩分成八個不同的主題分類。但我告訴她,不管是什麼主題,我的詩都是“動了凡心”的結果,也就是說,它們都植根於現實,同大多數的普通人的生活經驗息息相關。
另外有一點要提的,是許多讀者開始的時候可能會對我的詩的形式不太習慣。我的詩一般都很短。這同我對詩的追求有關。我希望能用最少的字,打進讀者心靈的最深處。我的詩有時候只是一句話,而詩句的分行也比較特別。通常我的分行是基於下面這三個考慮:(1) 內在節奏的需要;(2) 突顯我要強調的字眼;(3)造成詩意的岐意或多解。比如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大學校園裡流行脫光衣服裸奔,引人注目。我有一首叫「裸奔」的詩:
裸奔
如何 以最短的時間 衝過他們 張開的嘴巴 那段長長的距離
脫光衣服減輕重量 當然是 好辦法之一
可沒想到 會引起 傷風 化以及 諸如此類的 嚴重問題
把「傷風化」分行,就有造成岐意或多解的企圖,並達到驚訝震撼的目的。
下面我就根據《非馬藝術世界》書中的主題分類,用一些作品來談談我對現代詩的看法:
1◇幽默與諷刺
我一直覺得中國現代詩一般都太嚴肅正經,令人敬而遠之甚至望之生畏。生命裡當然應該有嚴肅的時候,但整天緊繃著臉,也未免太辛苦了。因此除了一些令人笑不起來的天災人禍外,我都盡量在詩中加入適當的幽默感。下面是我試寫的幾首帶有幽默或諷刺意味的詩:
2001年2月9日倫敦路透社有一段消息,說是有一對用手銬扣在一起的陌生男女搭乘飛機前往紐約。如果到2月14日情人節那天他們還這樣子一直鎖在愛情裡,他們每人將可得到7200美元的獎金。我不記得這是哪一個公司為他們的產品耍的廣告花樣,只記得我為他們寫了下面這首詩:
以鋼的堅貞 金的激情 我絕對相信 他們的愛 至少會維持到 情人節
1986年菲律賓總統馬可仕夫人伊美達(Imelda)逃亡到美國,人們在她的後宮裡發現了她的三千雙鞋子,為此我寫了下面這首「長恨歌」:
長恨歌
後宮佳麗三千人 三千寵愛在一身 ◎ 白居易
讓 千千萬萬 土裡土氣的種田腳 龜裂膿瘡的拾荒腳 疲累絕望的流浪腳 去哇哇大唱 他們的長恨歌
後宮佳麗三千雙 三千雙既佳且麗的鞋子 只寵愛一雙 伊美達的 腳
通貨膨脹
一把鈔票 從前可買 一個笑
一把鈔票 現在可買 不止 一個笑
通貨膨脹原來的意思是貨幣貶值,物價高漲。但在這種時候更可能發生的情況是,你手裡的鈔票會吸引更多賣笑的臉圍上來。笑貶值了,人也貶值了。
前年廣東佛山有一個叫小悅悅的女孩子被車子撞倒,路過的行人與車輛居然沒有一個停下來伸出援手救她,後來還是一個撿垃圾的把她像垃圾一樣撿起來,送到醫院也沒救活。我寫了下面這首詩:
活來死去 ◎給佛山車禍的小悅悅
麵包車前輪重重輾過 麵包車後輪重重輾過 卡車前後輪重重輾過 她都還輕輕活著
視而不見的眼輕輕掠過 冷漠的心輕輕飄過 風言風語輕輕拂過 她才重重死去
2◇社會性
幾年前在芝加哥一個中國文藝座談會上我曾經講過這樣的話: “今天一個有抱負的詩人不可能再躲到陰暗的咖啡室裡去找靈感。他必須到太陽底下去同大家一起流血流汗,他必須成為社會有用的一員,然後才有可能寫出有血有肉的作品,才有可能對他所生活的社會及時代作忠實的批判與紀錄。”
下面這首詩都是我們常看到的社會現象,包括經常發生的槍擊血案:
明星世界
自編自導自演 真人真事的 肥皂劇 每天 從每個角落 血淋淋 搶著演給 好萊塢 看
1983年台灣有一個中學女生因受不了惡性補習的壓力,跳樓自殺,我為她和許多同她一樣為了升學而被功課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學生們寫了下面這首詩:
惡補之後 ──哀跳樓自殺的台灣女生
惡補之後 妳依然 繳了白卷 在模擬人生的考試裡 他們給妳出了一道 毫無選擇的 選擇題
生吞活咽下那麼多 人名地名年代生字符號 公式條文定義定理定律 終於使妳消化不良的腦袋 嚴重積食 使妳不得不狠下心來 統統挖出吐掉
而當妳奮身下躍 遠在幾千里外的我 竟彷彿聽到 一聲慘絕的歡叫
搞懂了!終於搞懂了! 加速度同地心引力的關係
1987年汽車城底特律的華裔工程師陳果仁,因細故被白種工人誤認為搶飯碗的日本人,活活用球棒打死。事後白人法官祗判罰款的微刑了事,引起了全國華裔及亞裔的嚴重抗議,我寫了這首詩:
狗一般
有罪! 一個白人手裡的球棒大叫 黃色有罪!
就這樣 一個黃人被狗一般活活打死
無罪! 一個白人手裡的法槌大叫 白色無罪!
就這樣 一個白人被狗一般活活開釋
談到種族歧視, 1961年我剛到Milwaukee的Marquette University念書的時候,有一天手裡拿著報紙的廣告去找公寓,一個房東老太太看了我一眼說:“我們不租給有色人種。" 那時候美國還沒通過公民權 (Civil Rights) 的法律,無可奈何只好在心裡暗罵一聲妳這個死老太婆,妳請我住我還不一定要住呢! 後來我寫了下面這首諷刺存在於美國社會的種族歧視以及我們黃種人在這個社會中的尷尬地位的詩:
創世紀
當初 人照自己的形象 造神
這樣 上帝是白人 下帝是黑人 至於那許多 不上不下帝 則都是些 不黑不白人
希望虔誠的教友們不會太介意我借用聖經故事開個小玩笑,諷刺諷刺那些唯我獨尊的種族歧視者的心態。
3◇童心愛意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我曾為台灣一個叫「布谷鳥」的兒童詩刊譯介過一些世界兒童詩,同時自己也寫了幾首童心比較強的詩。
夜的世界
從角落裡 怯怯 向夜的世界伸出 觸鬚的天線
這些小傢伙 他們在偷偷收看 你的甜夢哪!
螢火蟲
不聲不響 把個遙遠的仲夏夜夢 一下子點亮了起來
沒有霓虹的迷幻 也不廣告什麼
夏晨鳥聲
有露水潤喉 鳥兒們有把握 黑洞裡睡懶覺的 蚯蚓 遲早會探出 好奇的 頭
上個世紀20年代便落戶於澳洲菲利普島(Phillip Island)上的企鵝,是世界上17種企鵝中體積最小的。身高只有30幾公分,體重約1公斤,羽毛灰藍色。被人們稱為「藍色小企鵝」 (Little Blue Penguin) 或「神仙企鵝」 (Fairy Penguin) 。 我們曾在菲利普島自然公園沙灘上看這些神秘的小企鵝天黑時從海上飽食回岸的景觀,是一個令人難忘的經驗。為了避免企鵝受到相機閃光燈的傷害,遊客一踏出遊客中心,便一律禁止使用相機與錄影機。面對可愛的小企鵝成群結隊回巢的奇景,只能把這一幕烙印在記憶的深處。
藍色小企鵝 ──澳洲遊記之二
為自由狂歡 一整天它們又在免費的海上大酒吧裡 流連忘返 終於喝得酩酊大醉 一個接一個 摸黑上岸
渾然不覺我們窺伺的眼睛 它們在沙灘上列隊操練 左__右_ 左___ 右__ 努力把踉蹌的腳步 化為優雅的波浪動作 在抵達家門之前
芝加哥有一個有名的作家叫史塔慈*特蔻(Studs Terkel,1912-2008),寫過關於經濟大蕭條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口述歷史,他說他從來沒有說過「我愛你」這三個字,他說他能感到它,但就是無法說出口。我也是這樣,在生活中很少說過「我愛你」或諸如此類的話。我太太常說我是世界上最不羅曼蒂克的人,但我有幾首可稱為情詩的東西是為她寫的,包括下面這首我們剛到美國中西部頭一次碰到下雪時玩雪的詩:
雪仗
隨著一聲歡呼 一個滾圓的雪球 瑯瑯向妳 飛去
竟不偏不倚 落在妳 含苞待放的 笑靨上
後來又寫了這首「秋窗」 :
秋窗
進入中年的妻 這些日子 總愛站在窗前梳妝 有如它是一面鏡子
洗盡鉛華的臉 淡雲薄施 卻雍容大方 如鏡中 成熟的風景
耳環
左右 拱護的 一對衛星 叮噹搖響 妳燦爛的笑聲
而在陰雲遮住妳的臉 我隨時會迷路的夜晚 是它們準確地標示 曾經溫柔亮麗過 妳月亮般的 存在
4◇人文關懷
這一類的詩我寫的比較多。通常是聽新聞報導所得到的靈感,或許可稱為「新聞詩」。
電視
一個手指頭 輕輕便能關掉的 世界
卻關不掉
逐漸暗淡的熒光幕上 一粒仇恨的火種 驟然引發 熊熊的戰火 燃過中東 燃過越南 燃過每一張 焦灼的臉
在電視上我們常看到非洲饑荒或戰禍的報導,許多小孩被餓成皮包骨,慘不忍睹。下面兩首詩寫的就是這些可憐的小孩:
非洲小孩
一個大得出奇的 胃 日日夜夜 在他鼓起的腹內 蠕吸著
吸走了 猶未綻開的笑容 吸走了 滋潤母親心靈的淚水 吸走了 乾皺皮下僅有的一點點肉 終於吸起 他眼睛的漠然 以及張開的嘴裡 我們以為無聲 其實是超音域的 一個 慘絕人寰的呼叫
生與死之歌 ——給瀕死的索馬利亞小孩
在斷氣之前 他只希望 能最後一次 吹脹 垂在他母親胸前 那兩個乾癟的 氣球 讓它們飛上 五彩繽紛的天空
慶祝他的生日 慶祝他的死日
每年冬天在紐芬蘭島(Newfoundland Island) 浮冰上出生的小海豹群,長到兩三個禮拜大小的時候,渾身皮毛純白,引來了大批的獵人,在冰凍的海灘上大肆捕殺。每天每條拖網船的平均獵獲量高達一千五百頭。這種大屠殺通常持續五天左右,直到小海豹的毛色變成褐黃,失去商用價值為止。
每年年初,美加各地報章都會為此事喧嚷一陣。其中使我久久不能忘懷的,是刊在《芝加哥論壇報》上的兩張照片。一張是一隻小海豹無知而好奇地抬頭看一個獵人高高舉起木棍;另一張是木棍落地後一了百了的肅殺場面。下面這首詩寫的就是這些小海豹:
獵小海豹圖
牠不知木棍舉上去是幹什麼的 牠不知木棍落下來是幹什麼的 同頭一次見到 那紅紅的太陽 冉冉升起又冉冉沉下 海鷗飛起又悠悠降下 波浪湧起又匆匆退下 一樣自然一樣新鮮 一樣使牠快活
純白的頭仰起 純白的頭垂下 在冰雪的海灘上 純白成了 原罪 短促的生命 還來不及變色 來不及學會 一首好聽的兒歌
只要我長大 只要我長大…
這首詩曾經引起台灣環保者的熱烈反應,還被台灣作曲家雷光夏譜成歌曲演唱並收入她的唱碟。
下面這首詩是我幾年前在美國國殤日那天看到電視上的報導後寫成的:
國殤日
在阿靈頓國家公墓 他們用隆重的軍禮 安葬自越戰歸來 這位無名的兵士
但我們將如何安葬 那千千萬萬 在戰爭裡消逝 卻拒絕從親人的心中 永遠死去的名字
下面這首詩是許多年前我們到華盛頓玩,參觀越戰紀念碑,看到許多人用手指描著刻在石碑上他們親人的名字後寫成的:
越戰紀念碑
一截大理石牆 二十六個字母 便把這麼多年青的名字 嵌入歷史
萬人塚中 一個踽踽獨行的老嫗 終於找到了 她的愛子 此刻她正緊閉雙眼 用顫悠悠的手指 沿著他冰冷的額頭 找那致命的傷口
5◇哲思
每個詩人的寫作習慣都不一樣。有的人倚馬萬言,有的人對著稿紙或電腦冥思苦想。我寫詩的靈感通常是在清晨欲醒未醒的時候浮現。這些靈感是我平日對某些有趣的事物思考醞釀的結果。下面這幾首詩表達的是我對一些事物的看法和體悟,也是我對人生的態度:
路
再曲折 總是引人 向前
從不自以為是 唯一的正途 在每個交叉口 都有牌子標示
往何地去 幾里
每個人的目的地不同,走的路當然不可能一樣,也就無所謂非走不可的唯一正途或絕對的真理。如果大家都有這樣的認識與胸懷,我想人類歷史上一定會減少許多不必要的糾紛與戰爭。
我在寫作時,總是儘量避開前人甚至自己已經說過的話或使用過的意象,站在不同的位置從各個角度各個方向用全新的眼光審視眼前的事物,希望能找到一些獨特的觀點與詩意。1973年的〈鳥籠〉﹐便是在這種認知下的產品:
鳥籠
打開 鳥籠的 門 讓鳥飛
走
把自由 還給 鳥 籠
這是我自己比較喜歡的一首詩,好像很少人這樣看待過事物,特別是鳥籠。正如大陸旅美作家劉荒田所說,它「象徵兩個互為依存互為對立的實體。讀者與論者儘可以見仁見智,將它們解讀為靈與肉、理智與感情、個體與群體、自由與奴役、社會與個人等相反相成的概念。」而我也在網路上看到它在不同的場合被引用去詮釋各式各樣的關係--夫妻、情人、上司與下屬、父母與子女、學校與學生、政府與人民等等。不久之前我還收到一封電郵,是一位女士寫的。她說接觸這首詩時還不到二十歲,是它讓失戀中的她豁然省悟解脫出來的,之後每當她遭遇到煩惱困擾時,“把自由還給鳥籠”這詩句總自然而然地在她腦海中浮現。在這詩裡,我把「走」字單獨放在一節,便是企圖造成一種海闊天空無牽無掛的自由感覺。而最後的鳥籠分開成兩行,可理解成鳥籠,但更可理解成鳥和籠。鳥自由了,籠也自由了。
1989年我又寫了「再看鳥籠」:
再看鳥籠
打開 鳥籠的 門 讓鳥飛
走
把自由 還給 天 空
詩後附有注解說:「多年前寫過〈鳥籠〉﹐當時頗覺新鮮﹐今天看起來仍不免有它的局限。因為把鳥關進鳥籠﹐涉及的絕不僅僅是鳥與籠本身而已。」劉荒田的詮釋是:「天空的自由是靠鳥的自在飛翔來體現的,鳥籠剝奪了鳥的自由,歸根到底是剝奪了天空的自由。開鳥籠,形諸邁向開放與民主的社會,便是打破種種禁忌,使老百姓增加許多自由﹐人的思想可翱翔於廣闊的天空,人的才智有了施展的廣大空間。此詩蘊含的不但是博大的悲憫情懷﹐更是富有社會學意義的省思。」
1995年﹐我又寫了〈鳥•鳥籠•天空〉:
鳥•鳥籠•天空
打開鳥籠的 門 讓鳥自由飛 出 又飛 入
鳥籠 從此成了 天空
將它寄贈給一位在密西西比河畔經商、自認為被困在牢籠裡的詩人,勸他通權達變,做一隻「自由飛出又飛入」的鳥; 飛出則神遊詩的世界,飛入乃操持商務,人生責任與自身志趣並行不悖,到了這一境界,所有的障礙都不復存在﹕「鳥籠成了天空」。很高興看到這位得到自由的詩人周正光先生今天也在座。
6◇鄉愁
我十三歲離開廣東隨父親及大哥到台灣去念書,不久以後便同留在家鄉的母親及其他家人斷了聯繫,幾十年不通音信,鄉愁之重可想而知。在這方面我寫了不少的詩,其中一般人比較熟悉的有「醉漢」及「黃河」:
醉漢
把短短的直巷 走成一條 曲折 迴盪的 萬里愁腸
左一腳 十年 右一腳 十年 母親啊 我正努力 向您 走 來
黃河
挾泥沙而來的 滾滾濁流 你會找到 地理書上說 青海巴顏喀喇山
但根據歷史書上 血跡斑斑的記載 這千年難得一清的河 其實源自 億萬個 苦難氾濫 人類深沉的 眼穴
1980年我頭一次回家鄉去探望離別了三十多年的母親及家人,回來後寫了一連串的詩,這裡是其中的三首:
重逢
深怕沖淡了重逢的歡樂 親友們彼此提醒 「過去的就讓它們過去吧!」 然後別過頭去 偷偷揩掉 到了眼角的淚水 然後在臉上 用力撐開 一張縐摺的笑容 像撐開 久置不用的一把陽傘
泡功夫茶是我家鄉潮州特有的風氣,小小的茶壺塞滿了茶葉,用滾燙的開水沖泡,然後倒進小小的杯子裡飲用。不習慣的人會覺得很苦很澀嘴。
功夫茶
一仰而盡 三十多年的苦澀 不堪細啜
您卻笑著說 好茶 該慢慢品嘗
大家也許都知道羅湖是當年從香港進入大陸的一個門戶。下面這首詩是我在回香港的火車上,恍惚的腦裡以邊界的羅湖車站為舞台,演出的一幕時代悲劇:
羅湖車站
我知道 那不是我的母親 我的母親 她老人家在澄海城 十個鐘頭前我同她含淚道別 但這手挽包袱的老太太 像極了我的母親
我知道 那不是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 他老人家在台北市 這兩天我要去探望他 但這拄著拐杖的老先生 像極了我的父親
他們在月台上相遇 彼此看了一眼 果然並不相識
離別了三十多年 我的母親手挽包袱 在月台上遇到 拄著拐杖的我的父親 彼此看了一眼 可憐竟相見不相識
7◇旅遊
幾乎每年我們都會選擇一兩個地方去旅遊。我發現旅遊是觀察世界刺激詩思的好方法之一。1992年我們到意大利去旅行的時候,意大利通貨膨脹非常嚴重,貨幣貶值得很厲害,銀行早晚的匯率都不一樣。
特拉威噴泉 (TREVI FOUNTAIN) ——羅馬遊之五
根據電影『羅馬之戀』的情節 每個希望重遊羅馬的旅客 必須背對這噴水池默禱 並拋擲三枚銅板
池子比電影裡看到的小得多 又剛好碰上禮拜一噴泉同管理員一起休假 看不到海神駕海馬車驅波逐浪的雄姿 我們仍急急用力拋出 三枚面值五百里拉的硬幣
但願它們在落水前沒太貶值
皮薩斜塔 (PISA TOWER)
一下遊覽車我們便看出了局勢 同大地較勁 天空顯然已漸居下風
為了讓這精彩絕倫的競賽 能夠永遠繼續下去 我們紛紛選取 各種有利的角度 在鏡頭前作出 努力托塔的姿勢
當地的導遊卻氣急敗壞地大叫 別太用力 這是一棵 不能倒塌更不能扶正的 搖錢樹
倒塌或扶正後的塔大概都不會吸引太多的遊客。
在布達佩斯一個猶太教堂傍看到納粹受難者密密麻麻重重疊疊的墓園,觸目驚心。後來看到位於布拉格猶太區內的舊猶太墓園,更是擁擠不堪。兩萬座墳墓擠在一個小小的墓園內,有些地方居然堆疊了十二層!原因是歷史上有很長時期,猶太人不論活的或死的,都不准越出猶太區(所謂的 ghetto) 一步。
猶太區
這是他們活動的地方 活人 不准越雷池一步
這是他們不活不動的地方 死人 不准越雷池一步
1994年我們到黃山遊覽的時候,山上正在建造新的賓館,雖然有吊車,但只載人,所有的建築材料都用人工挑上去。看到那些挑夫滿頭大汗搖搖晃晃的樣子,給了我很深刻的印象。
黃山挑夫
每一步 都使整座黃山 嘩嘩傾側晃動
側身站在陡峭的石級邊沿 我們讓他們粗重的擔子 以及呼吸 緩緩擦臉而過 然後聽被壓彎了的腳幹 向更深更陡的山中 一路搖響過去
苦力 苦哩
苦力 苦哩
苦力 苦哩…
最後的“苦力苦哩”是象聲,更是表意。
我想大家也許去過南京夫子廟,在廟前的夜攤上吃過東西。看到廟外燈光輝煌而廟內暗淡的情景,我當時心裡不免有所感觸,想起孔夫子的話:“ 朝聞道夕死可矣”,寫成了這首詩:
南京夫子廟
飢腸轆轆燈光發昏的廟內 子曰 朝聞道 夕食可矣
廟外 燈火輝煌熙熙攘攘 到處是聞香而來的食客
瀑布 ──黃石公園遊記之一
吼聲 撼天震地 林間的小澗不會聽不到 山巔的積雪不會聽不到
但它們並沒有 因此亂了 腳步
你可以看到 潺潺的涓流 悠然地 向著指定的地點集合 你可以聽到 融雪脫胎換骨的聲音 永遠是那麼 一點一滴 不徐不疾
曾經有人問我,為什麼能以業餘的時間作出那麼多的成果,我總用這首詩的最後兩行作答:“一點一滴,不徐不疾”。
8◇動物
我曾用十二生肖的題目,寫了一組動物詩,借動物之名來寫人類。
鼠
臥虎藏龍的行列 居然讓這鼠輩佔了先
要把十二生肖排得公平合理 只有大家嚴守規則 只許跑,不許鑽!
龍
沒有人見過 真的龍顏 即使 恕卿無罪 抬起頭來
但在高聳的屋脊 人們塑造龍的形象 繪聲繪影 連幾根鬍鬚 都不放過
馬
有時他們不得不 狠下心來 把跛了腳的 心愛的馬 射殺
挺直腰杆 英姿勃勃的 騎士形象 不容破壞
羊
沒有比你更好應付的了 給你什麼草便吃什麼草 還津津反芻感恩不盡
即使從來沒迷過路 也不相信靈魂會得永生的鬼話 (永生了又怎麼樣?) 你還是仰臉孜孜聽取 牧羊人千篇一律的說教
而到了最後關頭 到了需要犧牲的時候 你毫無怨尤地走上祭壇 為後世立下了一個 赤裸裸的榜樣
山羊
夜觀天象 在山巔 光禿禿的巉岩上
奎星犯太白 不利於西川 可憐的是我們這些無辜的牛羊 又要跟著遭殃
在山巔 月黑風高的巉岩上 一個飄著銀鬚的老者 因識破天機 而咩咩大哭
由於用漢語寫作,我同美國詩壇幾乎沒什麼接觸與交往,直到1993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參加了伊利諾州詩人協會。這個協會是一個民間組織,每兩個月聚會一次,主要是批評討論會員們所提出的作品,並組織各種活動如到養老院及醫院等場所去朗誦、舉辦成人及學生詩賽等。入會後不久我便被推選為會長,任期兩年。這段時間我陸續把我的漢語詩翻譯成英語,並在1995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英文詩集《秋窗》(Autumn Window)。使我決定出版這本書的是阿岡國家實驗室的一位美國同事。他說很喜歡我的詩,尤其是那首〈鳥籠〉詩讓他想起了留在立陶宛的父母,因此一直鼓勵我出版,他甚至願意在費用上助我一臂之力。我當然不會接受他的錢,但他的鼓勵給了我不少的信心。下面是這首詩的英文版:
BIRD CAGE
open the cage let the bird fly
away
give freedom back to the bird cage
說到這首英文詩,還有一個笑話。另一個美國同事說他也很喜歡這首詩,只是不知道它的真正意義何在。有一天他興沖沖跑到我辦公室來說:“我知道了!”我問他知道什麼? 他說我知道你的鳥籠詩的含義了。辛普森是鳥,我們是鳥籠,把他釋放了,我們也自由了! 那時節法庭正在審判足球明星辛普森(OJ Simpson) 殺害前妻和他前妻的男友的案件,每天電視上都是無止無休的法庭現場直播,大家都很厭煩。後來辛普森被判無罪釋放,才結束了這場鬧劇。不過最近辛普森好像又為了別的案件在法庭及電視上出現。
《秋窗》這本英文詩集出版後反應相當良好,《芝加哥論壇報》用了兩頁的大版面刊登一篇圖文並茂的評論報導,幾個當地的報紙也紛紛報導介紹。銷路相當不錯,第二年就再版。不久我加入了成立於1937年的芝加哥詩人俱樂部,成為唯一的非白人成員。一個詩評家甚至把我列入了芝加哥歷史上十位值得收藏的詩人名單之中。
隨著網絡的興起與普及,我自己也製作了一個個人網站《非馬藝術世界》,展出漢英雙語詩選、別人對我的評論、翻譯、每月一詩、散文以及我近年來從事的繪畫雕塑等等,同時也在網上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各種網上刊物及論壇上張貼作品,交流的範圍也隨之擴大,甚至有來自以色列的詩人要求授權翻譯我的幾首詩;日本著名詩人木島始也從網絡上同我取得了聯繫,用我的詩為引子,做漢、英、日三種語言的“四行連詩”,在日本結集出版;一些美國詩人團體及詩刊也來信邀請我擔任詩賽的評審或詩評小組委員等等。這些都是網絡帶來的方便。幾年前,伊拉克戰爭引起了美國詩人們的反戰運動,在網絡上設立網站,讓詩人張貼反戰詩,也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詩人的響應與支持,我曾擔任了一段時期的漢語義務編輯,我自己的那首「國殤日」的英語版也被選入了《詩人反戰詩選》,並被引用在一個叫做「戰爭年代的聲音」的記錄片裡。而《越戰紀念碑》的英文版則被美國公共電視台(PBS)拿去張貼在一個叫「戰後的越南故事」(Vietnam Stories Since the War)網站的第一面牆上,並且被許多退伍軍人團體的網站所轉載。
除了陸續將我的漢語作品翻譯成英語,並在前年出版了第二本英文詩集『在天地之間』(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之外,最近幾年我也嘗試著從事雙語寫作。無論是由漢語或英語寫成的初稿,我都立刻把它翻譯成另一種語言。我發現在翻譯的過程中,一些文字上甚或文化上的異同,往往會自動浮現出來,使我對原作(不管是英語或漢語)能採取一種比較客觀的批評眼光。這種相互激盪反復翻譯修改,使詩的表現達到最佳平衡的過程,至少對我個人來說,是一種非常奇妙有趣的經驗。
接著談談我的繪畫與雕塑:
九十年代初期,我同我太太一起跟幾位來自中國的畫家朋友開始學畫。在這之前,我雖然對繪畫很有興趣,卻一直敬而遠之。原因是我從小學開始,美術就是最差的一門課,每次勞作都做得一塌糊塗。所以我想這輩子大概只能像我對音樂一樣,站在旁邊做一個欣賞者了。剛好詩人畫家楚戈從台北來美國開畫展,經過芝加哥到我家作客,談到學畫的問題時,他說每個人都是天生的畫家,只要肯學,誰都能畫,他自己就是一個好例子。這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後來我又自己摸索著學做雕塑,發現雕塑的隨意性及自發性更強,更能滿足我的創作慾。我在一篇題為「學畫記」的短文裡說過這樣的話:“詩同畫之間最大的不同,我想是它們的現實性。詩所使用的媒介是我們日常生活裡的語言。語言有它約定俗成的意義。所以我覺得詩(甚至文學)不能離開現實太遠。如果我在詩裡使用「吃飯」這兩個字,即使它們有比吃飯更深一層的意義,仍應該多多少少同吃飯有關。否則讀者會摸不到頭腦,不知道你在說什麼。繪畫不同,它所使用的媒介是線條及顏色。我在畫布上塗一塊紅色,它可能代表一朵花,可能是太陽下山時的晚霞,也可能是一個小孩興奮的臉,更可能是戀愛中情人火熱的感情。所以我覺得繪畫不妨比詩更抽象,更超現實。懂得欣賞現代藝術的人不會盯著一幅畫去問它像什麼?正如我們不會去問一朵花一棵樹或一片風景有什麼意義。只要它們給我們一種美的感受,就夠了。當語言文字在一些感情面前吞吞吐吐甚至保持緘默的時候,繪畫及雕塑便為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表達方式及途徑。”不管有沒有成就,我發現學畫以後,對色彩及光線更敏感,也更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這些多多少少都影響並豐富了我的詩思。
我曾在芝加哥和北京開過幾次個人畫展及參加過幾個合展。我的第一次個展就是在劉昌漢會長從前在芝加哥開設的畫廊裡展出的。這次陳瑞琳會長寫信要我帶幾張畫照來給大家看看,說這樣能幫我省些說話的時間。所以就隨便選了幾張帶來,向大家討教,順便也請畫家兼畫評家的劉會長批評指教。我有一個詩友兼畫友目前在北京的宋莊藝術村擔任美術館的館長,他說要為我在北京開一個個人畫展,時間可能在今年的十月。所以回去以後還得加緊準備。
下面就請大家看看我帶來的幾張繪畫及雕塑的照片。
秋窗, 夕照, 我的蒙娜麗莎(意大利畫家達文西蒙娜麗莎的微笑,巴黎羅浮宮), 醉漢, 獨飲, 日出, 新西游記, 篤篤的馬蹄, 歌女; 在花園裡; 夜總會; 靜物; 貴妃醉酒; 舞蹈; 夢之圖案(2卷)封面畫; 夢之圖案; 秋樹; 秋景; 貴婦; 裸像; 少女; 馬的架勢; 舞姿; 吊兒郎當; 母馬與小馬; 無語問蒼天; 斜躺的老人; 休息; 帶項鏈的女人; 穿短裙的少女; 幾年前在公共圖書館的展出.
最後我想再說幾句話:
我一向認為,不管一個人的職業是什麼,花一點時間接觸文學藝術是很重要的。美國前任桂冠詩人泰德•庫舍(TED KOOSER,1939- )曾經在內布拉斯加擔任過一家保險公司的主管,出版過十幾本相當暢銷的短詩集。他說寫詩帶給他許多好處,在一個電話紛響、文件亂飛的雜亂世界裡,寫詩使他恢復了心靈的秩序與安寧,是一種免費卻無價的高尚娛樂。
根據非正式的統計,光是在芝加哥這個城市,便有不下於一百位的「詩人主管」(包括企業界及政界各部門的主管)。他們利用空檔──咖啡時間,午休時間,搭乘火車上下班的時間── 把一天中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思,用詩歌的形式在紙上或電腦上記錄了下來。他們各有各的寫詩理由。有的是為了紓解工作壓力;有的說寫詩使他們嘗到了創作的樂趣,得到了心靈的自由與滿足;有的說寫詩使他們保持情緒的平衡,知道什麼事該輕鬆馬虎什麼事該嚴肅認真;更多的人說寫詩讓他們能更客觀也更靈活地看待問題,做出較佳的決策,因而提高了他們做為主管的工作表現;更有人說寫詩使他們的心變得更柔和,更富同情心,更易於與別人相處溝通;當然最重要的是,因為寫詩的緣故,他們能用比較天真好奇的眼光,在本來可能是平凡灰暗的世界裡,發現即使是一草一木,都充滿了生命的光輝與神奇。活水在他們的心頭流動,生活不再那麼枯燥無聊,家人、朋友、同事、鄰居甚至街頭巷尾的陌生人,都一個個變得面目可親了起來。
當然不可能每個人都寫詩,但花一點時間讀詩應該是大家都可做到的。我常引用英國作家福特(Ford Maddox Ford,1873-1939)的話﹕「偉大詩歌是它無需注釋且毫不費勁地用意象攪動你的感情;你因而成為一個較好的人;你軟化了,心腸更加柔和,對同類的困苦及需要也更慷慨同情。」詩歌如此,其它藝術也如此。
http://home.comcast.net/~wmarr9/2013houston-photos.htm
( 八幀選四 )
美南華文寫作協會會長劉昌漢
詩人非馬前輩演講神情
會場一角:周正光伉儷及之群(非馬夫人/中)
同部分聽眾及國際新移民華人作家北美筆會會員合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