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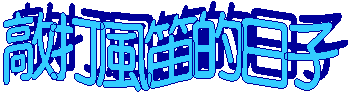
![]()
寫在風笛詩社的成立
|
你聽過風笛的聲音嗎?很民謠風的;是不?也許在以後長長扁扁的日子,你一定不會寂寞,像屋外一片燦爛的世界,木葉那麼光輝,現象那麼潔凈,很高興你斯刻的感覺,想像中的一切不必定是醜惡的,有時一件平凡的感情,內涵的深度會產生火花。不知為什麼這個季節竟使我們的風度互相吸引住,天空底下,你會把隱藏的胸膛坦露開來,讓陽光走進去,你會把你疲憊的心喚醒,重新出發;因為有一支號角,已經開始它美的衝刺,一隊在精神上的信仰有所認定和執拗的行列,已被激起強烈的反應,敲打出一種說服力的象徵,但一切力量都在默默的忍耐中表現出來。看見那枝竹笛嗎?如斯簡拙的一節斷梗,風來時,也曾嗚嗚作響,飄流著鄉愁的意味,那麼心靈上的。 當六個人圍坐在我的小樓,(昨夜東風,望盡天涯路),樓外正漲滿灼亮的陽光,風搖響門檻垂掛的風鈴,但都被路過的車聲沉寂得微渺了,加上我們濃濃話語的蒸沸,似乎只感覺鈴聲來自空谷的沓沓。坐我對面的,荷野的位置可以望出欄柵外的樹,樹叢上的白雲,再高遠,是一片青空。青空平靜無事。敘述一些家常近況,各人有各人的姿態,溫文的荷野似笑非笑的為他的時間表搖著頭,除了把白天交給數字,晚上的時間又交給補習的學子,卻把情人的約會欄填空了,莫怪乎黎啟鏗取笑說:這是所謂春天,非常的春天。 怎麼──這是春天?誰知道春天是怎樣來的?誰知道你以怎樣的顏色與感覺把灰樸樸的生命漆得如斯新鮮和繽紛,繽紛是表象的,新鮮是情緒的,這原因是接受那驟然突臨的白鴿所代表某個意義的麻木的驚喜,鐘聲自千里萬里外一直敲到我耳膜震盪的範圍,久年厭惡和愁苦的積習似乎還不能一下子全然改變,心中的悸疑也局部佈滿了焦渴的額紋上。誰知道春天是怎樣演出的!當我企盼最切的時候,又恍然忘記所以其然的理由及那種微妙的心情,你能為我解釋這斗室內曾經的山水的過疲與長嘯的瀟洒是何種程度的悲壯嗎?這悲壯是我們長期以來循一種無依無靠的信念延續下去,也許這悲壯已成為虔誠,成為我們飄泊的一代精神上莊穆的宣示,你怎能斷然拒絕這種遺傳,這種風暴式的敲打,你怎能因中國的隔絕連自己的良心與民族的尊嚴都摒棄在內?歷史上的民族意識永遠威赫的存在著,國家的屹立,無論她的庶民如何卑顏和羞恥的被覆蓋在特定的生活方式,屹立的象徵是始終不滅的;唯有在苦難中才能生長出一朿怒火的力量,唯有在建設的必需才能獻身一顆沙粒。但被祖國隔絕的痛苦,這悲壯的深刻縱迸出生命怒吼的一句長嘯也表達不出的。我們年青的新的一代就是在表達不出的感受中發見自己的生命竟是一株脆弱的蘆葦,在狹窄的觀念中走著狹窄澀苦的道路,也於斯種體驗的狙擊下,個性之泯滅愈來愈接近邊緣,我們的命運整年無休止的飄泊。飄泊。飄啊飄飄飄飄。泊泊。怎麼──這是春天?春天在誰的相思裏?誰的相思在伊的髮辮上?髮辮上停著誰的髮結蛺蝶?你的眼波,像是要捕捉一個飛逝的彩色蝶翼的記憶,那裏面躲著一個純真的瘦影與一片如雲的愛情‧‧‧‧。 我小樓的窗子向南向著一條長長的你望不斷的街道,一排樹站在對面那邊沉思,一排又老又醜的樹倒也新綠油然。這是春天。燕子還在北方。你仍是不歸的相思豆。鳳凰樹的台南你的台南寄出的航空郵簡,伍圓郵票上你瀟洒的名字,一九七號的信箱,那是使人難忘的風濕症,風濕著我的念,最初最痕跡宛然的;你的遙遠就是一塊香口糖,相思也咀嚼不相思也咀嚼,咀嚼咀嚼你幾時擲來的歸期。 水湄的下午,雲色漂得天空晶晶發亮,我再次把六個茶器撥滿了溫熱的殷勤,偏偏李刀飛喝的卻是一杯微涼的烹茶,他的說話有時很吸引人的注意力,但我總想起他把遲到的理由訕訕一笑地拖過不談的表情。異軍緘默好久的說:──風笛。好嗎?那是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一日星期天的下午,吃了大半天的茶。風常把敞開的窗櫺吹攏起來,在屋內釀造淺淺的蔭影,我不時把窗推開,漏進有點傾斜的光線;別讓這個日子輕易地破滅,我們都想著。於是討論的氣氛一直很濃,提出很多欲待解決的問題,也非常過癮的孵出一個未來的輪廓。心水兩度走到門傍,一面俯首望望蟄伏路邊他那輛熄火不動的車子,一面問我日曆上的火圖是否我畫的?又伸手撫觸那朵將滅未滅的紅色顏漆的火,以及背底深藍色的絨布;我畫的是一幅夜色的煙火。去年一帖瀟洒江湖的日曆畫面被我換上了今年的煙火,沒有甚麼新的釋意,只不過是我生命境遇有所感觸的心情一段練習曲的表現而已。人生是一部讀不完的畫,越翻越薄,我是夾在其中未完成的一頁,怎樣才是完成?譬如煙火乍燃乍滅,夜色沉寂依然,像撕不破的黑色布帛,不因霎時的光亮而裂它的永恆;我們的衍求莫非一剎那燦麗超越時間空間而又回歸人類最高層次的哲性之感動?我們追尋人生的目標不單只具體的現實的到達,形而上的收獲更加是充溢生命的美的完整。寫詩,就是生命的美的表現。 我們這些風浪過的臉,興奮冷靜的匯結個體的表現成為一個焦點,成為敲打風笛的金屬性;我們對詩的執著,恒感受鳳凰火浴的超昇的透明燃燒體,那種心靈共鳴的撞擊。記得你說過:我的存在就是我的繼續。這也是為甚麼我們朝廿世紀中國七十年代踏上我們飄泊的芒鞋,以回歸的精神,在異鄉瘦長的土地,忍不住的春天便霍然爆開一朵傳統的煙火,升自我們開闊的胸膛。 喧呶喧呶的春天煮熟了整個下午的風景,六個少年坐在小樓的風景中,另外六個少年坐在小樓的風景外,你深深的眼波,為甚麼總把一頃一頃的無限向視域之外拓展?為甚麼總忘我的走入無限?遠方,將有十二顆騰昇的星,呼吸一個共同的天空,將有牧春的孩子敲打他們的風笛,這是一個剛出芽的歲月,我們是歲月的臉。 日影漸傾,斜斜如離弦的箭,弓手的怒髮,猶不肯履離窗外,窗外如焚。將要告別的時辰,我收住一團飛馳的思緒,看茶器零落的空著,杯腹無語,應該再添盛一回茶罷。我道及西牧現仍在某地的訓練營守著寂寞,守著白萩的詩句:《望著遠方的雲的一株絲杉》的孤苦,大家都湧上流浪心情的嘩笑,多麼年輕的笑聲,飛揚、鏗鏘、蓬勃、歡樂的,也帶點蒼涼的味道;蒼涼蒼涼,想起在戰地寫詩的生命,血都熱騰騰的。而我們的詩,卻寫不出雄壯和憤怒,寫不出悲哀和進取的氣概。你的詩是怎樣的詩?你不羈的舒伸是怎樣的悲壯?你的歌在誰的胸膛燃燒?你的河山在誰的內裏形成?敲打啊!甚麼是黃河長城?甚麼是順化西貢?甚麼是中國?甚麼是越南?甚麼的鄉愁仍纏綿你僅有的意識?落淚吧!兄弟。姊妹。如果我們還有眼淚,為甚麼不奔流出一條洶湧? 天空泌出一個黃昏的形象,像要墮下而又漲高,它的幾隻手指擱在欄柵和壁上,一隻洞穿窗櫺,宛若一片發光的黃葉,自覺的抓住一個崩開的意象。曾經與我圍坐吃茶的臉們,一張張都飛到哪裏去了呢?我想叫出他們的名字,在黑夜來臨之前,辨清他們掛在天空的方向,啊!莫非他們就是那些美麗的星辰?一盞盞的點亮他們的生命。茶器零落的空著,我拈起其中一杯仰首,彷彿喝下我們的遠景,看敲打風笛的日子飛翔‧‧‧‧。
1972.2.11風笛詩社的誕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