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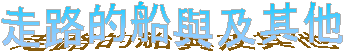
|
履離向南小樓的曾經,一盅菊花茶以後的曾經,一切形象都幌失幌得仍遺留些痕跡,仍不甘一切像煙消雲散的那麼虛無。畢竟我們都擁有相同的信念去堅持開闊的步伐。畢竟我們都瞥見懸掛的前景在遠方也並非全屬於遠方晰晰如你形體之飄昇及飛揚:一切都是真實的,我們都不以為已失落了那種寫詩的感覺,我們冷靜的 近乎神祇意識的去詮釋詩、散文,及探索和思維心靈呈顯的那種昇華過程。 而我仍在百里之外捕風捕雨,蕭蕭風雨的白日及夜及空盪盪的寂寞無際無涯的孤獨,生與死的意識在轉瞬間拽去拽回,什麼都來不及回憶,若那痛楚在胸襟上花般燃燒,若那洶湧的液體流成一條河,意識是如斯的微妙,而醒來塵世上已千年?呵仙。呵古老的中國。呵北京人。我已遺忘你神話的雛形?我豈是在等待你的初醒? 一切都是真實的,風裡雨裡,我像一隻船穿過漠漠的空間,棲宿時青衣一片濕冷,我在荒木野灌下挖坑棲宿的經驗,母親,您又搖幌的白髮滿簇眼沾著淚粒,絲絲絮散之白黏連著串串的光影,最悲處也只幻化一句暗泣夾在無能寄出的信套裏,沉重的郵戳,喊呼年節歡慶中失去我的名字。我像一隻船,掬你有蕩然的感覺,那麼又何苦排采一組實體的攝影五月其上我們的色彩,五月其上我們歡欣的語談,若已惘然,惘然更好,古人在繽紜詩詞中醒來仰望,我們卻找不著刻上甲骨文的碑石。 遇見你五月一個午後,搖扇子的五月,風輕輕,樓子留落下好些年青你我的忘言,相信再也不能其實又何必的記憶,瀟瀟洒洒的江湖起來吧!如風如雨你是風風雨雨所無能掩遮的一隻船。我撥開你朗朗笑語,撥開你滿臉的陽光,發覺拈著肩上的塵土薄薄一層與我一樣風塵的了。問好你。問好天氣。你說悲不悲?還是喝一口淡淡的茶,圍攏相對的靜坐一面,翻開手中我們不經意正讀的書,第幾頁?隨欲的提上一句思索又隨欲的扔棄。並不為什麼的站立,看窗外雲飄葉搖瓦蓋停落沽沽的白鴿三五,然後整齊衣衫。呵!幾時我們再走進潑墨的空間去尋找一株竹一株蘭去寫現代的詩的散文去意念去感覺去境界去精神我們未發現的涅槃去架構我們的骨樑。 於是你成為一個未能祟拜的偶像,只因你輕易的未能在形象上著色及淡漠 的表情以及某些你無法矯飾的動作,低眉垂坐,你還是不很真實的表現了自己,你的內在世界仍不圓滿的接受太多外界的幅射;但這就是我們,我們這一代落落磊磊的真相。而你也透露出一種映象一種彼斯共通性的憂懼,那就是我們這一代的失落感。你或許會指出,形色上我們各各表現了自己的風貌,在最黑暗的夜空中,我們是一撮撤向虛無的空間之欲待滅熄的星火。我們都燃燒著:以我們全心全意的生命。——民族,你莫非也在燃燒? 站立起來,你向我告別,五月。我解衣坦胸,船船船船,你裸裎的美麗,黃昏後,等待第一顆星遲遲升上,船的夜泳是美麗的:我在靜境中守候划過的槳聲,槳在手上,姿勢在意念裡,你的方向呢?甚或我們竟無一條可渡之岸,也並非沒有,而是我們的習慣疏忽了原來的意義,只懂得表相功用及相互利益關係,或者我們以為隨波與溯流就是我們奮鬥選擇的象徵,就是真誠與隨俗的裡表;但在斯時,我唯是思索及祝頌有一條長長的岸在你航向的遠方出現,那是必然觀念的,雖然我們未必能安全抵達彼岸朝風迎立,船的蕩然,我依可想像出你的微笑是酣眠的真實浮雕在逐波衝浪的船椽上。如斯,又何用懷疑我們寫成的歷程又何用風騷的留落下一些刻意的腳印呢!你能否拾撿起船駛過的痕跡高舉而炫燿我們的光輝!自古以來,船是那麼真實的走它自己的路。 握著你手,你的形象便升爬我的廣額,像極一面旗幟的飄昇雲的飄昇意念的飄昇成長與世界不停飄昇,恰似我己然忘記的名字一齊飄昇,我不再去記憶我們曾說過些什麼,那不頂重要,實而我並未告訴你一些什麼,但你已感覺我心靈的跳動是如何的輕如何的重,你悄息轉過身子,將履離這孤高的小樓前你曾想過些什麼?我也欲言又止的暫停下自己浮出的念動,一切都不必挽留,若你是船你是槳,若我是一條長長的岸,遠方已朝面走來。 一切都不再記憶。一切都是真實的。
◎風笛散文專號三1974.8.13披刊於南方成功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