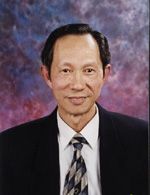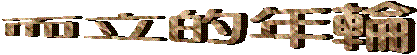|
|
樹的影子和人的影子疊著疊著就把一個春天交給另一個春天。 人的影子在不斷的變,把別種姓氏妻過來以後,就有四種童音打破你處男的清白。你遂是鬧市上不帶手銬的囚徒。 賭注傾囊的擲下,然後瀟瀟洒洒的走開,誰也不過問你勝你敗。憐憫和同情是許多種虛偽裡的虛偽,人總是生活在虛偽裡而卻又拼命否認一切;人人如此,你不你就是怪物。你在乎也如此,不在乎也如此。 當女子美美你的眼睛,美美你的心靈,你要如何用非處男的身體去回報一眸成春的感情,你的感情很「柏拉圖」,曾在蓮池畔,凝對千瓣春紅呢喃一個把你遺忘的名字。 很古典很中國的一個名字。 噢!中國中國,遙遠遙遠的地方。你只能在地圖上告訴子女們你曾經居住過的家鄉,而後痛苦的忘卻在納稅表上原籍欄格,所填寫的一個代表風雨不息的國名。 子女們不懂中國,中國更加不懂他們,什麼都可以洒脫,獨獨摔不開這個死結。 你又在無病呻吟,網住了又掙扎,然後再衝進另一網裡去;眾生嚮往彼岸,有多少眾生能夠成佛? 你是個不具「般若」的低等動物,不能自渡,佛怎能渡你? 包含四種智慧的「般若」,居然會淺淺的動起你的心;關於經是「經」或是「鏡」,也令你茫然過好一陣子。你想著的是那麼題外得可以使講經的和尚發笑,那和尚的風範和咬音清脆的一口潮州方言,確實迷你如斯。你有時間而又放得下你此刻的人生,你真想立刻出家,隨他雲遊八方。 你連讀書的時間也少得可憐,你更不會去讀經了。你想想而已,和尚很快又在你匆忙的來去中淡忘。 現實是一把鎖,宗教也許是失落的鎖匙,拜佛或信主的人最終可以找到他們的極樂之地或天國?地獄獰笑著打開黑門迎接你,蛆蟲迎接你,生命的終站對於人並沒有兩樣,只有活著的用儀式去區別。 你的「更年期」會來到很早,早熟早蒼老,這是自然規律。多麼不該想到死亡的問題,多麼不該有疲憊的倦意。非處男的三十整數是很青春很活潑的,應該是人生的二分一甚至三分一而已,但你卻獨對孤燈敏感不屬於你年輪的問題。 責任是世間的繭,你不該破蛹。走過的路路過的方向,錯和對,喜悅或痛苦都像夜來香的味道,飄來了又逸去,生命的書不能重讀,愛情也是。 你應該有所作為的,做一個成功的商人比詩人更容易,介於兩者之間的矛盾和不被認可的毅然惑常有鎚心之疼。詩質和市儈的衝突是絕不融洽的兩面極端,什麼時候你才能從極端的兩面回歸,而立或不惑,還那麼茫茫無期,你在或已不在? 想起相信掌紋相信生命線的女子,纖纖弱弱的依附你,你堅強的抗拒迷信,那份柔情卻使你羞慚於獨對瓣瓣蓮花。把一生幸福隨便的交給女子,誠然危險,但當你感覺不幸或溢淚時,被吮乾淚水的溫暖融化。纖纖弱弱的女子的力量就如此堅強的恒常縛你囚你依附你。 千蓮千瓣千根烏絲皆化為水,你再也撈不回走遠的沉沒的時間。 樹輪千年,樹影不變。人的影子疊著疊著就把一個春天交給另一個春天。 春天變不變?你變不變?
一九七三年五月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