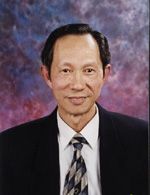|
|
歲月悠悠,轉瞬來澳已二十五年,四分之一世紀的改變很大,當年牽著才五歲的小兒子明仁走出墨爾本機場,今日他已是銀行經理;那個性格內向的老三明哲才十一歲,怎想到他會成為美國「電腦科技公司」的高級行政董事,終年奔波於東南亞各國,父子難得會面。嬌柔的女兒已為人母,為我養育了一對甜心般的乖孫女伊婷和伊寧,而叫我爺爺的大孫女如珮也已上初中了。 二十五年,彷彿如夢,也頗似是昨天,回首往事,那段怒海逃亡的夢魘如影隨形。晨起散步,和內子婉冰回顧前塵往事,想到荒島十七天,家人和全船千二百人都能平安渡過苦難,除了感謝老天爺的慈悲厚愛外;亦感激祖上積德,先父母多行善事,才使兒孫逢凶化吉,絕處重生。也憶起在荒島上遇見的活菩薩,若他不出現,也真不知斷糧之後的日子會有何災難發生了? 巴拿馬註冊八百噸的「南極星座」舊貨輪,在公海上被四艘漁船上一千二百多個男女老幼越南難民登上,在南中國海面航行了十三天,被馬來西亞海軍無情驅趕出大洋後,終於在印尼平芝寶島(Pengipu Island)觸礁。微曦中發現陸地,我們大喜,及至天亮登陸,始知是個無人的荒島,而輪船前倉底已被珊瑚礁觸破;海水湧入,令船傾斜了三十度,成了棄船。大家唯有狼狽不堪的上岸,就在沙灘上棲風宿雨,整整十七日夜,我們能生還重活於世,實在是個奇蹟。 貨輪上的食水庫幸未被海水混淆,在我領導發施號令下(貨輪航行三天,因我協助船長統計人數,而被難友們公推為總代表。見拙書「怒海驚魂」有詳細描寫。)工作組天亮即去提水上島分派,每天每人只得半公升。地近赤道的荒島,每日氣溫達攝氏四十六七度,那半升水,僅夠活命;中午大家唯有全家老少都浸泡在海水裏幾小時,以逃避毒日的照射。幸而老天可憐我們這大班苦難人,往往午夜天降甘霖,雖然都成了落湯雞,人人不怨反喜,爭相抑首吞飲甘露,還拿一切奇怪狀的容器盛雨水。 淪落荒島八天後,人人所帶的乾糧,都將不繼,食量較大的年青輩,早已忍受飢餓折磨了。海中魚群頗多,可惜逃難時誰會想到帶釣魚工具呢?空手又無法撈魚,只好「望魚興嘆」了! 那晚月明星稀,半夜守更人員忽然鳴鑼示警,我在夢鄉中被喚醒,沙灘上所有難民皆翻身而起。火堆映照中但見七八個黑人拿著漁具木棍,吱吱喳喳指著我們;我們起初以為是海盜,瞧到只不過七八人,又無武器,大家膽子也大了。雙方漸漸靠近,忽聞其中一個膚色較白者用潮州話不斷的重複者:「令時沈米朗?」 「令時沈米朗?」(你們是什麼人?)真是世界上最悅耳的聲音了,我精通潮語,立即越眾而出,大聲回話:「阮時加己朗!」(我們是自家人!) 原來他是印尼土生的華裔,也是這艘漁船的主人,那幾位黑人是印尼土著漁 夫。他姓許,有個長長的難記的印尼名字,互報姓氏,言語能通,消弭誤會後,他對我們這千多落難者,大表同情,立即命令漁夫到船上挑來多籮鮮魚。 逃難將近二十多天,已經沒享受過海鮮了,大家睡意全消,分到魚後急不及待的生火燒魚。處處火堆,香味洋溢,什麼怪魚也有,沒見過的有點怕,但許先生要我轉達,任何在海中捕撈的魚,知名與不知名,都可以放心食用。 當晚傾談,許先生竟看上了觸礁擱淺的破輪船,問我是否可以交易?我真的想也不想的立即滿口充諾,帶他去見那位會說閩南話的芬蘭船長,(我當時不會講英文,因是閩南人,可以和船長溝通,才誤打誤撞為他解決了點算全船難民人數,而成為逃難時的領導。)船長的條件很簡單,只要把他和水手團載去新加坡就行了。而我則要求給我們三四天的海鮮。許先生很真誠,他說我不提,也會留下來打魚,供給大家海鮮,因為「我們是自己人」。 那幾天,我們過著人生最幸福的日子,天天烤魚燒魚,分到的魚,各式各樣,有大有小,奇形怪狀見也沒見過的都有,海底真是個大寶藏啊。大家食的魚,都不加任何調味,要配料也沒有,只好原味入口,雖然有些微腥氣,但在斷量時刻,有此天下至美之海鮮,夫復何求呢? 幾日後,許先生在黃昏時準備妥當,向我告辭,說再不走,漁船燃料用盡,他們也要淪落荒島了;他應允一回到漁港立即向印尼當局報告我們的遭遇和所在荒島的位置。貨輪船長也來握別,他帶同六位水手隨許先生回去,以免被印尼海軍拘捕,控告他非法運載人口,被判「蛇頭」之罪。他也保証平安回到新加坡,即刻打電給官方,要我們安心。 目送他們的小漁船消失在水平線上,我們不免惆悵,卻也只好把希望寄託在他們身上。至少、我相信許先生那顆菩薩心腸和貨輪船長的專業道德,他們回到陸地,必定會向有關當局反映。 難挨的苦日子再渡過了幾天,那天微曦初露時,海面視線內突然冒出大戰艦的影子,全島難民歡呼。不少父老跪地叩謝菩薩保佑,絕境逢生,也有人相擁喜極而泣。當日,印尼七千噸級的戰艦把我們一千二百零四位男女老幼救離荒島,運往丹容比娜島的橡膠園內難民營地。 悠悠時光飛逝,那位在我們淪落荒島幾近斷糧時出現的許先生,別後我再無緣與他重遇。每一念及,他對我們全船的恩德,只能以「活菩薩」形容;在定居新鄉二十五載後,僅撰文以感其大恩。
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五日於墨爾本無相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