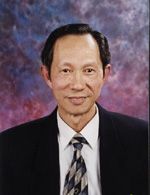|
|
夢繞湄公河畔 稚齡時期我是在出生地越南湄公河畔巴川省度過,記憶縹緲如夢幻,那些應有的歡笑淚痕彷彿傾倒了半瓶塗改液通通被抹掉;殘存的是震撼我幼小心靈的死生輪迴,宛若烙印深深燒焦腦細胞,偶爾回想好像仍有淡淡的煙硝自久遠的歲月裡飄蕩。 法蘭西帝國仍然控制著印支半島,以解放國土號召的抗法游擊隊簡稱越盟,要救國搞革命必然是流血的事兒。我家對開不遠處是座軍營城堡,進出的多是威猛高大的紅毛兵,自是法帝國的遠征軍隊。 這座建築在小丘坡地的城寨成為越盟游擊隊攻打的主要目標。月黑風高驟然廝殺狂呼、混著卜卜槍聲劃破沉寂夜空,也往往擾人清夢;朦朧中被雙親拖拉下床,一家人平躺地板待黎明曙光,照明彈好像煙花,只是少了歡愉氣氛,代替的是恐懼憂慮的沉默。 旭日東升後,曦光裡空氣變得靜寂,門外早起的勞動平民已開始奔波,昨夜似乎是我小腦袋的一個夢魘;然而戶前玩耍拾取的銅色彈殼卻又證明槍聲確切破空呼嘯。父母的神色冷冷,無心對稚子解釋,徒然增加了我埋藏心底的徬徨感。那天許多嘈雜的人群尾隨著大隊紅毛兵,押送著數十個猶如乞丐身份的越南人經過門前,瞧熱鬧的追隨者越跟越多;挺著鼓圓大肚的媽媽佇立店舖邊,傭人許是受不了誘惑,牽著我的小手往人堆裡擠。我遂成為長長隊伍的參與者,沒多遠、便見到濁水洶湧的湄公河了。 那些赤身露體雙手被捆的可憐男女被押向河流,成百上千的群眾鴉雀無聲;好像人人喝了啞藥或被紅毛兵的剌槍點了啞穴般。佣人將我抱起,視線始可觸及河畔一字排開的人,紅毛兵突然舉起步槍,一個兵對準一個被捆綁的人背後;幾十條長槍整齊劃一,幾乎同時扣機,子彈呼嘯的震波仍在空氣中迴旋。 那班男女背後腦袋開花東歪西倒伏身沙灘,紅毛兵在吆喝聲中收隊。圍觀的群眾向前奔跑,議論聲紛紛響起,那些被槍斃的是法殖民帝國眼中的死囚,越南人民的民族英雄。他們暗殺或者偷襲法軍失敗被捕,刑場就在湄公河畔。 就義的越盟同志們的屍體不知橫臥多久,我看到的是鮮紅的血和一具具伏躺不動的人身。死亡張牙舞爪,活生生的人驟然卜的一聲被子彈射入,血流如泉,命便結束了。那年我六歲,死亡像隻怪獸過早的前來,深深的困擾著我稚嫩的心靈。午夜夢回,那些汩汩的血漿塗染著屍體像幻燈片,明滅閃爍不時映現,成了我幼小腦袋揮之不去的夢魘。 幾天後,店鋪早已按著軌道買賣,那班橫臥沙灘的幾十具屍體想也被拖走,一切正常到仿若只是我的幻想?我將心中疑慮向比我小兩歲的弟弟講,他茫然難解;同伴沒人見到,也不肯相信那些超越他們年齡的可怕而醜陋的事情。成人們各忙各的,無人肯花費時間關心一個幼童的問題,夢魘遂成為我孤獨咀嚼的秘密,輾轉襲擊對我糾纏不清。 挺著圓圓鼓脹肚子的媽媽完全將我們兄弟倆交給傭人,她經常撫著肚皮喃喃自語。愉快時候也偶然拉起我的小手按在她隔著衣服的大肚外,告訴我裡邊是個妹妹,很快會來和我們玩耍。似懂非懂的點著頭,靜下時也自個兒理不出個結論,想不通的是媽媽肚子裡如何能藏著個妹妹? 那天店鋪裡特別忙亂,人進人出,媽媽卻不見露臉?傭人不肯給我進房,說小孩子不能進去,因為媽媽在生妹妹,我頗難明白的是為什麼媽媽生妹妹時,爸爸可以走進去走出?我卻要待在房門外。自然也想像不出媽媽是如何能生妹妹? 再問時、傭人嘟起嘴,呼喝著要我別多話。爸爸的樣子好凶似的,更不能去纏他,只好將串串難懂的問題吞嚥進肚內。 媽媽的呻吟聲驟然傳出房外,聲音漸漸張揚,混雜幾位從沒見過的阿姨、姨婆什麼的那些人的說話聲。爸爸進進出出像好忙碌,其實他什麼也沒有做,只是不安的進出,想來當時他也不清楚自己為何要如此? 後來、也難再記憶是過了多久之後?媽媽比我更頑皮的大吵大叫,她又尖又剌耳的音波蓋過房內一切聲浪,如洶湧的大海浪濤滾滾向前,把前邊那些細微的波濤全吞噬了,只餘下她嘶聲喊叫,海浪翻騰震耳驚懼。 佣人將我兄弟拉到大廳裡,但全屋空間均被媽媽的聲浪掩沒,弟弟哭了,我感到害怕,張開口連連呼叫媽媽不要生妹妹了,不要生妹妹了、、、、、、。 我細微的聲響引不起任何反應,突然、一聲清脆的啼哭破空亮起,媽媽的恐怖嘶喊已止息。那聲波像魔術師的戲法,哇哇連綿,人人喜形於色,奔走相告,傭人將我緊緊摟抱,笑著告訴我,媽媽生了胖弟弟。 奇怪,明明說要生妹妹,臨時又改成了弟弟?不多細想,我已可以和弟弟一起奔入房內,見到新弟弟沒穿衣服,裹著毛巾閉緊雙眼,好難看的樣子。我很失望,已經有了弟弟,又是另一個弟弟;媽媽一心想要生個女兒正如我盼望妹妹的心情相同,當年媽媽必定也很失望? 三弟誕生後,戰爭並沒停止,越南人民抗法爭取獨立的革命如火如荼,天天有不少越盟被拉去河畔處死。我們遷離巴川省,搬到南越首都附近的堤岸華埠躲避戰火。 離開出生地巴川省後,湄公河滔滔奔流的濁水仍然日夜不停的湧動,流走了歲月。抗法戰爭終於在一九五四年「奠邊府之役」大捷而把紅毛兵趕走。不幸越南又分隔南北,引爆長達二十一年之久的二十世紀著名的「越戰」。 兵燹連綿中成長,及至戰爭結束,舉家逃奔怒海,湄公河越離越遠,兄弟分散澳洲、瑞士與德國三處洋域,父母也埋骨歐洲杜鵑花城小鎮。 悠悠水聲,刺耳槍聲和初生弟弟哇哇啼哭混雜的幻夢偶而被勾起,再無緣重逢的湄公河景象歷歷在目、、、、、、。
二零一四年七月仲冬於墨爾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