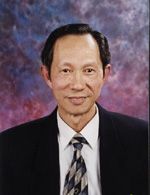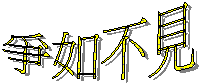|
|
當時輕別意中人,山長水遠知何處? 高樓目盡欲黃昏,梧桐葉上瀟瀟雨。 晏 殊
梅嫂每天清晨準時來到寺廟值日,先在神壇前上三炷香,再將供奉多日的水果收拾,或留或扔;打掃後就回到櫃檯敲打算盤,把開支帳目整理。沒有香客時,偶然讀讀舊報刊、有時也神遊太虛打發空餘時間。 髮際飄霜青春早逝的梅嫂,個子適中體態清瘦,瓜子臉型依稀顯現當年風華倩影;如今卻一臉苦像,沒人知悉其內心世界。她也從不加入三姑六婆說三道四的是非堆裏,閒話也就無從落在她身上。 一對兒女早已獨立離巢,老伴往往與她相對無言,在人前卻口沬橫飛,每日早出晚歸,多年婚姻都在冷戰線上,若非為了子女,已早早了斷這場千錯萬錯的無奈夫妻關係。 蕭波俊逸的影子,在寒夜擁衾夢迴時,仍糾纏不清;那年山盟海誓,卻因戰爭日益迫近,在他家人強行安排下要他偷渡赴港再轉去臺灣升學,一段好姻緣竟被拆散,留下的是無窮無盡的相思、、、、 陰差陽錯出嫁後,千山萬水遠隔,她早已把相思深埋心底;越戰結束,苦難開始,逃奔怒海,定居澳洲。惡緣造成的夢魘日夜困擾,看到別人幸福、內心的黃蓮苦汁只有和淚吞。 這些年在廟宇內做雜務,早晚焚香給菩薩,除了祈禱一對兒女平安外,就是給千山外的夢中人祝福。也偶然興波,求菩薩安排,令她能在夢裏和他再見。但卻沒想到的觀音大士顯靈,那天奇蹟竟然會出現、、、 星期日清早,深冬的寒氣仍未消失,廟宇寂寥,才開廟門未久,竟有數位香客伴入廟,那對男女匆匆觀望後便先行離去,只餘虔誠者對著神壇跪拜。 梅嫂垂首正在整理賬目,香客高大的身影已挪近櫃檯,耳際陌生的聲音: 「小梅,妳還好嗎?」 梅嫂手足無措的有點驚慌,這個親密的名字,不知已有多少年月再無從聽聞了,而這陌生人竟然會如此出口相稱?除了他,還有誰知她少女時的小名? 梅嫂抑頭,依稀如夢,當年那張俊美少年郎的臉龐雖已不再,郤還有抹不掉的輪廓。她呆呆的望著這個陌生者,相思數十載的男人竟會驟然出現,是真是假如幻如夢?一時間竟悲從中來,多少歲月的思念,多少失眠長夜輾轉,多少辛酸頓湧,淚水已失控,淚眼迷糊中輕輕的啟唇: 「是你,怎會是你?」 「是我,一直在找妳,只想見一見妳,沒想到一幌就幾十年了。」 空氣凝結了,梅嫂挪開老花眼鏡拭乾了眼角的淚痕,幽怨的彷彿在自語:「太遲了,為什麼為什麼要在幾十年後呢?」 「不遲的,能夠重逢,知道妳平安已不枉我老遠從美國趕來。」 「當年為什麼為什麼你那麼狠心一走了之?」她不覺悲從中來,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思無時無刻的糾纏,真沒想到悠悠數十載後,在黃昏晚景才再相見。 「做為亂世人,我們有時是很無奈的;妳和家人都好吧?」蕭波對著那張被歲月折騰到比實在年齡更蒼老的淚眼,有點手足無措。 「子女都好,唉!一切都太遲啦!你有幾個子女?她好嗎?」梅嫂痴痴的眸光射向他。 「我沒有結婚,那會有子女。」蕭波臉上揚起自嘲式的微笑。 「哦!對不起,你又何苦呢!、、、、」梅嫂低下頭,深深被震撼著;絕沒想到他竟是如此的一個痴情郎,心中甜甜濃似蜜。 「妳別誤會,不是因為妳,而是我的生理問題;我的伴侶是一個美國男士,我們相處得很好。」他平靜的彷彿是轉述別人的事。 「你騙我,年青時你不是很正常嗎?」 「我一直都很正常啊!性取向不同,那能說是不正常?」 「為什麼你不早對我說?」梅嫂心中的千般苦再次湧上,眼前這個人竟然是她午夜夢迴深心思念的情郎,如今活生生的站在面前卻對她講,他是同性戀者?天下有如此荒唐的事,竟發生在她的身上。 「我們分手後,再無法連繫,又如何對妳說呢?何況妳早已嫁人。我找妳,只是為了守諾言,當年盟誓我們要再見的、、、、」 梅嫂忍不住的淚水再次沿著臉頰滾落、、、、、、 、、、 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九日仲春於無相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