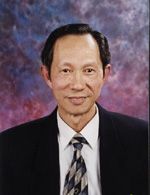|
|
四 姨
認識四姨完全是因為阿承的關係,十年前我忽然收到一封從馬來西亞悲痛島的函件,要我擔保來澳洲的求救信。阿承是我在越南工廠裡的舊職員,正巧他姓陳,和家母同宗,算是表弟,便向移民居申請他來澳。 手續順利且快速,兩個月後接納他移民來澳洲。原來當日移民官曾到悲痛島接收難民時,已獲准的他竟拒絕單身赴澳,要求准許他和四姨一同移民到澳洲。 我再次收到阿承的信,假如他真的這樣做,誰也會感動。他們在逃亡途中遇海盜,被恣意掠奪搜刮,他身上的三錢黃金和幾百美元,都被強搶了。正欲趨前拼命,未料雙脚被身旁的越南婦人緊緊抱着,努力掙扎,竟難于脫身;及至海盜退走,他才清醒。當時若非四姨奮力阻止他,定會被凶殘的海盜殺死。如他獨自移澳、留下無人照顧的恩人四姨,問心難安。請求我幫忙,讓他倆能同移來澳洲。 那樣有情義的阿承,頓使我刮目相看。至於四姨的背景,我是茫然無所知,欲幫忙也無法度,僅有勉力而為了。 不久、我接獲坎培拉移民局善心的官員來電,問我是否願意也擔保阿承的「姨母」,並附上那位越婦姓名年齡等等資料,和申請表一同寄來。相信是阿承的故事感動了這位移民局官員,回澳立刻和我連絡。 我願意作擔保,填好表格即日寄去首都。三個月後、我終於在機場和久別的阿承重逢,也見到素昧平生的四姨。 四姨約五十來歲,較健碩身型,是一位很傳統有禮的越南人。他倆把我當作恩人千般道謝,令我很不好意思呢。最讓我高興的是她是烹飪能手,常為我等烹調美味的越南菜,撫慰我和內子的鄉愁。滷肉、春卷、酸湯、牛肉粉、米碎飯、甜品等等;讓彷彿仍身處舊家園,重回堤岸。棄國拋鄉多載,家裡忽然有位好廚師,每日享用不同的佳餚,那份福氣,使朋友們羡慕不已。 阿承經我介紹,也到工廠上班。終於、他另租公寓,和四姨搬往新居處了。兒女們對亞婆搬走,皆悵然不捨。猶如上餐館,每天習慣了四姨的美食,被寵慣的腸胃,對內子的簡單飯菜,深感失望,孩子和我皆有同感。 四姨跟着阿承,也叫我Anh Hai、即越語大哥。她有着一雙明亮的大眼睛,慈祥的五官,總是帶淺淺的微笑,是一位可親的長者。她待阿承仿如母親,對我的兒女猶若孫輩般。本來她是和女兒孫子一同逃奔怒海,不幸在碼頭被越共發現,當場拘捕。掌舵的技術好,冒險衝出火線。每次講述,四姨皆眼含淚光,幸好有阿承依靠,未至老死於島上。 他們租住的公寓,離我家僅五、六公里,逢年節或假期都一同聚餐。其實當四姨來我家煮飯,孩子們皆爭着教這位喜愛的亞婆說廣東話,聰明的她學會簡單的會話,連英語的普通對話,也學了不少。四姨廣東話越來越好,她說是租看香港無線台的連續劇學會的。 阿承在西貢淪陷後才結婚,那時是我駕駛花車迎親。他太太是芳鄰,婚後育有一女,比他先逃亡,聽說已隨家人移至美國了。勞燕分飛之苦,使已安定且成為澳洲公民的阿承,仍未填表申請家庭團聚,我多次催促,阿承唯唯諾諾的不想進行。我猜大概夫婦分離太久,感情已淡,或是另有隱情。 暗中詢問四姨,她說他倆早已散伙,雖未正式離婚,夫妻形同陌路了。他僅想取回女兒撫養,但被拒绝,故他常常難舒雙眉,沒膽再談戀愛了。 一個三十多歲的精壯男人,長年禁慾是沒法的。四姨試圓為他牽線,他總是拒绝。漸漸四姨對阿承的婚姻,緘默不再提起了。間或、我會勸阿承該盡夫責和為人父的天職,四姨却頓歛笑容的躲到廚房,讓我頗感納悶。 四姨聯絡了一些越南朋友,皆居住南澳。於是、四姨努力說服阿承,搬遷至南澳阿德雷得市。我和兒女們到火車站送行、依依揮別,以後只能在電話中相互問候了。 數年前我陪兩位遠道而來的故舊往南澳觀光,再見阿承和四姨;他們是租住一房一廳,房內是一張雙人床,阿承解釋說:客廳梳發椅拉出便是床,他是睡在客廳裡。我們在那享受了幾次海鮮晚餐,四姨也趁機大顯廚技,忙得不亦樂乎。 那晚、四姨拉我到庭前,悄悄對我說:“大哥、阿承變了,三天有兩夜沒回家。在餐館任職,竟然和老闆娘有染,這位風流寡婦也快五十歲啦!真是老不要臉。我最近常和他吵,請代勸勸他吧,若仍如此,我只好回越南了。” 飲食男女,這種關係我也難於置喙呢。深心明白愛情是盲目的,若墮進去,就是醜婦也會像西施。只要阿承喜歡,女大於男也是沒錯呵! 阿承自然不肯承認,反說是四姨胡亂吃醋。這回答使我非常吃驚,四姨怎麼會吃醋?再追問時,阿承自知失言,匆匆轉變話題。說他的妻子曾帶幼女來澳洲,留了十天,便帶女兒回美國了,因為她不能接受和四姨同居一室。我沒法了解他們之間的恩怨,惡緣善緣皆有因果,局外人是無法結論,我只好沉默了。 四姨真的回返越南,走前打電話向我辭行,聲音悲切,也讓我牽動離愁,像是已和阿承鬧翻。看來那位香港寡婦已令阿承不能自拔了。我僅是瞎猜,也未敢求證。 那天、突然接到美國的電話,三更半夜忽被鈴聲驚魂。拿起話筒正要數說這冒失鬼,對方已先道歉,並甜膩膩地說:“是大兄嗎?我是曉梅”。稱呼我“Anh Hai、大哥或大兄”的人很多,竟忘記是誰?粗聲問:“曉梅是誰?是那一位?”,“我在德州,以前在越南時,是你的鄰居,住右邊最後一間,我結婚時是由大兄駕花車的,怎麼忘了呢?” 原來是阿承的太太,何故來了又走,我終於想起她了。一串激動的聲浪傳入耳膜:「他不要我了,竟然和老狐狸鬼混。我已聽到這緋聞,但並未相信。那次澳洲之行,老狐狸親口承認,故意把我氣走。大兄、他是變態才會要一個老太婆而放棄我們。我今天只想問問大兄,他倆仍在一起嗎?從越南糾纏到外國,真是不要臉呢。」 曉梅的話讓我大吃一驚,但睡意濃濃的我思想也混亂,僅好聊了幾句,迷糊地再進夢鄉。 不久、聽南澳友人告知,阿承已飛去歐洲。前年聖誕節曾收到賀卡和寫上電話,但從此失去聯絡、音訊渺渺,連四姨和曉梅也全無消息。冬去秋來,我忙着生活,漸漸把他們淡忘了。 去歲末我赴德國探親,沐浴在皓皓白雪的冬景裡。因妻喜愛雪花,天天陪她在棉絮飄飛,枯枝顫舞的銀色世界中散步,談談行行不覺間已到小城市中心。妻感酷寒難耐,趕快進去一間咖啡館,在近窗的角落坐下,眼瞳驟然一亮,微長黑髮襯一張瘦削面容的男子,竟是阿承;身旁蒼蒼白髮的胖婦人,正是四姨,兩人複雜的表情是蘊含錯愕和慌亂;彷彿是被人撞破奸情,雙雙臉泛紅霞。 他鄉能意外重逢,我們難掩興奮,立刻更換座位一起共坐歡聚。 「四姨、妳不是說回越南共聚天倫嗎?怎麼會移居德國?」我打破沉默。 「Anh Hai、我已來了一年多,因為不放心阿承,他吃慣了我煮的菜,我不在時他瘦了幾公斤呢。」 「你們現住那裡?」我問。 「住不來梅市附近,今天餐館放假,陪四姨來這逛逛。沒想到會遇見大哥大嫂。」阿承的面上有點忸怩不安。 「甚麼時候回澳洲?」我隨意問問。 「還未打算,這裡安靜,認識的人不多,免去是是非非。真是意料不到,跑來這麼遠,依然會遇上大哥。」 閑談了半句鐘,臨別時彼此交換了德國的電話。本來欲往其居所探訪,可惜四姨和阿承完全沒意思邀請,且又沒給地址,我也識趣不開口,阿承用車送我倆回弟弟住家。看着汽車消失在茫茫的雪地上。我的心境好難過,那麼有緣在澳洲聚首,這次又有緣重遇,這麼熟悉的故人,竟把昔日濃濃的友誼淡化。明知他倆在逃避世俗的人和事,可惜逃到了天涯,還是讓我碰見了。 至此、才相信曉梅的話是真的,她說不甘心也想不通?我更難於明暸,難道四姨的烹飪廚藝,便可令阿承拋棄家室向她稱臣嗎?
二零一五年元月三十日重修於墨爾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