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水
良 師 益 友
之四
游啟慶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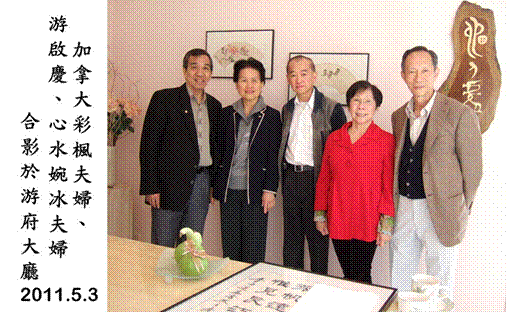
將近半世紀前、在堤岸華埠駕花車為內子婉冰的堂兄葉蘇迎親,在喜氣洋洋的婚禮上初識新郎的同學游啟慶;眼前這位猶若白面書生般的仁兄,清瘦身軀擠在迎親隊伍內,若非偶而發出響亮爽朗聲音,幾乎像不存在的幻影。
翌歲農曆新春越共發動總進攻,戰火禍及華埠,先岳父母為了安全舉家搬去“國民學校”內暫住。前往探視始知游君為該校教師,與婉冰二妹同事。當時並不知這位瘦弱書生已是飽學秀才,且還是位年青書法家呢。
故園淪陷後三年另四個月,我帶領內子及兒女們投奔怒海;逃過大難汪洋餘生,於半年後獲澳洲政府人道收容,從印尼難民營移居新鄉墨爾本。不意在史賓威難民暫時定居中心竟再遇到游君,更沒想到的是我們在新鄉尋工時,都被同一家汽車零件大工廠Repco接納為藍領操作員工。
在不同車間流水線勞動,每日午餐必在餐堂內踫面;雖然只有半小時的用餐時間,我們幾位同聲共氣的同事自然而然共用餐桌,彼此閒話家常或談論時事,說笑戲謔聲浪大,常引來洋同事們側目。大家最愛聽游君講述笑話,只不知他腦袋內如何能裝載那麼多奇譚怪聞?
我們車間內十餘位來自印支半島的華裔難民工人,游君與我是被大家視為“有點墨水”的書生。我能“吹水”的無非是國際時事新聞,得益於每日下班在工廠門外花四十仙買回一份英文晚報。我對英文一知半解,強迫在晚飯前閱讀及查字典(當年尚無中文報紙)。縱然不能完全掌握細節,卻也對世界各地發生的重要事故有些印象。
沒想到這份機器操作粗工,造成我右手肌肉患上「肌肉疲勞損傷症」,因工傷被廠方調到零件倉庫擔任分配零件的輕工作;當然也幸虧我的那點膚淺英文通過工廠經理的測試。離開車間的勞累粗工後,除了午餐仍依舊與同事們共桌外,其餘的早、午兩次飲茶短暫休息,就只能在倉庫內與洋同事相對;及至我在1993年我另覓新職離開該工廠,彼此才終斷了每週至少有五天在廠內共用午餐的歡樂時光。
三十餘年前“維省印支華人相濟會”由葉保強先生召集,籌備創會時、游君與愚夫婦皆參加了籌備會,該會成立後我們自然都成了首屆理監事會內的成員了。每次到墨市中心會所開會,往往都要游君順路到寒舍接載;從蝸居至墨市尚要三十餘分鐘路程,正好在車上東拉西扯,幾十年來晚上應酬只要順路我們必定同車前往,至到游君他遷不再在史賓威郊外居住。
墨爾本印支華裔社區過去幾十年來至今,每有活動幾乎都是由游啟慶擔任大會司儀,他出口成章,風趣幽默、經常是詩詞典故隨口而出,因此成為墨市僑社著名的金牌大司儀,提起他的大名,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反而他書法家的銜頭竟被自己無礙的辯才口才所埋藏呢。
寒舍掛著一幅中堂書法,精美棣書揮毫的是蘇東坡念奴嬌詞,下款撰寫「啟慶特贈以償十年字債並乞正腕、於一九九四年。」一九八四年在工廠閒談時,我沒忘記每天共用午餐的老友是書法家,鄭重求字並獲他應允。誰知這一等竟整整等到十年後,才能將游君墨寶拿去裝裱鑲入鏡框,從此掛在客廳;與廖蘊山居士的對聯、廈門曾伊鴻先生的草書「心如止水」、紐約書畫會朱雲嵐會長的山水國畫相輝映。
游君聰慧好學、天生異稟,博聞強記而能過目不忘,他朗朗上口的所有詩詞歌賦,我年青求學時及離校後,都曾先後閱讀過背誦過。可是、任我讀過多少遍背誦了無數次,仍然無法深記腦海。而游君腦袋卻猶若電腦般將過目的古典詩詞存檔了。要用時、腦筋一動即時浮現而順口道出。這點能耐實在萬中無一,曾對老友說,若退休撰作文章,必定事半功倍,引經據典時不必如我,要尋找資料始能引用。
幾年前游啟慶先生在墨爾本郊外的博士山市開班教國學、這位早歲為人師表如今再開講古文,真想報名就讀,成為他眾多學子中之一呢。所謂學無先後達者為師,我雖已發行十部各類文學著作及兩冊已完成編輯尚未出版的散文與雜文集,被華文文壇詩壇稱為作家、詩人,說來慚愧,在中文修養尤其是傳統國學,游啟慶先生確是我衷心敬佩且能做我良師的益友呢!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於墨爾本無相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