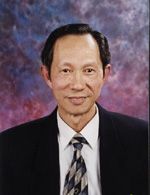|
|
澳華黃玉液小說創作的文化蘊涵
姚朝文 (佛山科學技術學院中文系,佛山 廣東,528000)
摘 要:本文試就澳華作家黃玉液(筆名心水)的小說創作爲個案,來探討澳大利亞華文微篇小說和長篇小說創作中的文化情結。作者依據早年的越南生活、海上漂流以及現居澳洲的生活經歷爲背景,熔異域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於一爐。澳華小說創作已經成爲澳洲文學森林中的一座別致的花園。薪傳華文文化的情結實屬難能可貴。但發揚、推廣華文文學的艱巨使命則十分不易。海外華文作家的文學創作,更多顧及的是延續民族文化而不像大中國範圍內的作家或執著於求新求異、與衆不同,或爲了關注於市場銷路的得失。 關鍵字:澳大利亞華文 微篇小說 長篇小說 華人文化情結
海外華文文學,在東南亞、北美、歐洲、澳洲等這樣非常廣闊的一個區域裏,逐漸形成了國際規模,成爲與中國文學(包括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澳門的文學)相區別的一個漢語書寫的文學範疇,一種與中華文學的形態景觀頗有差別的異類形態。隨著華人\移民潮的擴散,華人地球村的形成將成爲不爭的事實。中華文化與異域文化相結合,世界性的海外華文文學已日漸羽翼豐滿。但就中國大陸對澳大利亞華文小說的研究而言,對那些從大陸去澳洲的留學生文學或新移民文學比較受關注[1],對澳華老移民的華文文學創作則比較忽視。筆者願在此探討從越南漂流到印度尼西亞,然後又移民到澳洲的澳華作家黃玉液(筆名心水)的小說創作,來揭示一些爲中國大陸不甚瞭解的異域奇葩和歷史真相。
一
勾勒與傳神 他於2000年出版的微篇小說集《溫柔的春風》中,有許多篇目都能以詩性標題吸引讀者。如《水燈夢》、《夜來幽夢》、《望盡海角》、《溫柔的春風》、《柔情似水》、《銷魂獨我情何限》 當然,這些抒情意味頗爲濃厚的標題,能夠調動讀者的前理解,去猜測小說將涉及的主題指向。他筆下的標題很少直接揭示該篇小說的具體內容。在小說情節的進展中,先給讀者設置一種懸念,當讀者看完全篇再回首,發覺題目與文章揭示的中心有著耐人尋味的意蘊關係,揭示出一定層面的社會、人生哲理。 如《緣分》,單看題目,已猜到多半是言男女之情,小說開始處簡單介紹了女主角萬圓的年齡、性格、職業、婚姻感情等一系列基本情況,然後寫她暗戀公司的新經理,以爲相隔兩地也能走在一起,緣分已到。誰也不曾預見到篇末來了一個大轉彎,自己的意中人原來是有婦之夫。到此,再看標題,緣分,其實是有緣無份!
又如《會長》著重表現主角老沙的虛榮心。他憑藉小人式勾當出任全澳沙氏宗親總會的會長,其實當中的成員全是他家的親屬,硬是湊夠人數來成立總會。到結束時,作者借老沙的口道出了富含諷刺性的心裏話:做會長真過癮,一點都不難啊
作者固然反映的是海外澳華社會部分人士的心態,其實這個題材所折射出來的民族性格、社會特徵乃至人性的某種普遍性是十分明顯的。從民族性的角度看,中國大陸讀者可以讀出:原來不只中國有這種一心想出人頭地、把自己淩駕在他人之上的華威先生變種,至少在世界各地的華人社會(當然包括澳華社會)裏,也有這類大活寶。其他民族的人也會看重自己在族群裏的身份、地位,因而也會垂涎於當權的暈光效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可以想見。但華人與非華人的不同似乎在於,非華人(比如歐洲人、日本人)通過競力、競技、競智來勝出,而且與宗族、政治上當權相比,他們更看重工商實業、金融財富。而我們華人種族,在歷史上就是宗族、宗法社會,不尚個人的突出能力,而是依靠血族、宗親、裙帶關係來向上爬。不是憑科技、工商強大,而是全民一心奔官場,官本位,學而優則仕!三教九流之優都是爲了當官,當官成了人生價值的體現,成功與否的標誌。不當官就不能出人投地,就一無是處。在這種民族偏狹甚至病態價值觀念的驅使下,當不了父母官(尤其寄居海外,身爲次等民族),也要當個宗族官、做人上人,才覺得榮耀。《會長》篇幅不足500字,揭示的民族劣根性卻十分深長。
二 曲折的故事,豐滿的人物 生活中,藝術家因各種物象、事件的觸發,常發生心理波動,造成失衡,並引發適當強度的情感。宣泄情感,以恢復心理平衡,便是顯動機的主要內容。[3](P141) 黃玉液的小說作品,較多反映社會生活中的人性問題,故事呈示線性發展脈絡,富有立體感,但由於微篇小說篇幅的限制,往往需憑藉以小見大的方式來反映作者對社會擔負的責任感。他選擇身邊的瑣碎事情,涉獵生活中的情感問題,表現某個社會層面的人生百態。他再加以移花接木、騰挪想象,力求做到故事性強,人物形象又鮮明突出。 (一) 家庭生活。如微篇小說的《大聲公》、《球》、《諾言》、《笑容》 、《戒賭輔導》等。其中《大聲公》主要講述夫妻雙方間的情感關係。丈夫老柴,綽號大聲公,因幼年生活環境養成了聲震屋瓦的說話習慣,對妻子兒女說話時也同樣積習難改,雖然並無惡意,但確實讓家人難以忍受。妻子阿柔終於氣憤至極,怒斥他不許再大聲講話,否則就分手。此後大聲公的聲音如蚊子般細小,家裏從此靜寂無波浪。小說反映了家庭生活中夫妻雙方的感情問題。這類題材從一個側面顯示了現代社會男權的衰落與女權雌威由量的積累終於達到質的飛躍的現實。這一篇小說的特殊之處表現在,作者選取一位多半生中逆來順受的老婦終於開始理直氣壯地維護自己早已喪失掉的尊嚴和自信。這就很有表現力。我們可以推想到,傳統負累比較少的青年婦女們的女權意識將會是何等的高漲。《大聲公》很有代表性地表現了家庭婚姻生活中新的女性形象。 (二) 社會生活。這方面包括社會上男女情感交往問題,過去和現在的生活環境問題等。關於男女情感交往,通常是兩方皆未婚,或其中一方已婚,涉及親密關係、萍水相逢、工作關係、朋友關係等,如微篇小說《水燈夢》、《迎親記》、《朋友妻》、《阿甜》、《英雪姑娘》 。其中《水燈夢》是講述我在泰國一年一度的水燈節與來自臺灣的袁萍萍水相逢,放水燈祈願的事。《迎親記》是寫喪妻數年的老曾,讓兒子回國迎接年輕的新母親,但這位未來繼母與兒子年齡相仿,兩人觸發了愛情火花,兒子奪父愛而擁繼母爲妻。這些都刻畫了男女之間的情感波瀾,細膩的情感描寫,將這一社會群體的情感交往,通過各類典型事件來表現,躍然於紙上。 另外,黃玉液的小說反映的社會問題,有其早年在越南生活的經歷,也有他處身澳洲的人情世態及回祖國探親的印記。如《丁夫造橋》 ,寫澳洲富商、愛國越僑丁夫榮歸越南胡志明市,想造福鄉民,捐資三十萬澳元興建橋梁,爲防止貪官作梗,他決心親自監督與承投工程公司簽約,便呈文連同計劃書向政府審批,誰料,從地方送到中央,再由中央返回地方,審批浪費了整整6個月,蓋有三十個印章的批文才下來,又退回原來接受審批的地方坊委:沒有先例,各級機關都不敢負責。丁夫氣憤地當面撕掉批文,省下了三十萬捐資。這篇小說,很有代表性地反映了政府體制和各階層權貴的弊端。 選擇特定環境裏的特定典型,將這一典型人物融入整個小說的故事情節當中,再讓他與小說中的配角等發生關係,讓典型人物活靈活現,躍然紙上,産生扣人心魄的藝術效果,具有比較堅實的藝術價值。比如《會長》裏的老沙成爲會長後,每逢酒宴聚會,必擠身貴賓席。小說的字裏行間,流露出諷刺、幽默的筆調,這增添了小說的的思想性和藝術含量。《賈歪教授》中,這種筆法表現得更爲明顯,移民澳洲的賈歪教授在文壇上舞文弄墨,卻錯字連篇,連自己的姓賈也錯誤理解爲假,充滿諷刺喜劇的趣味。作者以自己生活的文化圈子爲基本框架,加入澳洲文化因素,用以呈現澳洲華人的生存狀貌。 可以看得出,長篇小說《怒海驚魂》以作者的親身經歷爲原型,是一部自傳體長篇小說。小說描述包括元波一家在內的一千二百多名難民,在越共排華浪潮中舉家投奔怒海、流落公海,棲身荒島的逃難歷程。作者在書中《自序》裏情難自禁地說:南極星座完成了救人的任務,殘骸在平芝島旁漸漸沈沒,千多位幸運的乘客有緣讀拙書,必定會說這不是虛構的小說,而是真真實實的記錄文學。 [4] (P3) 作者如何選材,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小說的成敗與否。黃玉液的小說,揉合了社會哲理、人生感悟、生活情趣、多語種方言口語的特殊表達以及詩性品質於一體。兼具歷史真實性與文學藝術性的創作方式,使得作品的感染力大爲增強,讓人印象深刻,回味無窮。
長篇小說的結構一般可分爲開端、發展、高潮、結局4個部分。但是微篇小說卻是例外。一般來說,它不需要完整的過程,可以取其中一、兩個富有表現力的側面,將故事的高潮或結尾展示出來就可以了。微篇比之長篇,除了要求語言更精煉、更簡潔外,構思要更精巧。 小說開篇的鋪陳對於全篇小說功不可沒。心水的小說開端,首先會介紹相應的情況,如人物主角介紹、故事發生的背景等,步步引入,迅速吸引讀者的興趣,自然地將讀者帶進一個境地。如微篇小說《戒賭輔導》,一開始就引出了主角妮娜,然後交待了主角周圍所處的立體環境。妮娜因老伴已離,四個兒女忙忙碌碌,孤寡斷腸、寂寞難熬,唯有將時間耗在老虎機上,小說將妮娜的主體感覺全盤托出,建造了一個很好的環境框架。《怒海驚魂》的開頭更是與書名相呼應的鏡頭:狂風怒號,刮起浪潮一個個拍擊著海面的一艘小漁船,躲在艙底的七十多個人在懼怕裏有份共同的感覺,那就是:天威難測。迅速引入立體的海上環境,彌漫著濃濃的驚險氛圍。在接下來的段落裏,出現了主角元波及其一家人。情節自此展開,他們與其他小漁船上的難民交足金條,上了八百噸級的南極星號,輪船正式排水開航。這樣,小說中的大環境初步形成,爲下面故事情節的開展作了很好的鋪墊。 長篇小說情節的發展,一般是通過與主角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人物或事件來推動,營造出適當的環境氛圍,慢慢地激化矛盾,在開端的基礎上加深鋪墊的力度。微篇小說進入矛盾激化狀態卻直接了當得多。《戒賭輔導》的發展是通過一個傳言的引入激發矛盾,無窮放大的消息妮娜玩老虎機已到了嗜賭如命的地步。於是,兒女們對她的關懷變得足以超越正常的程度,尤其是老三的一句話:宛若老娘偷了他的生意本錢去賭場般[2](P49),還有幼女更是暗地裏向她借錢。至於妮娜是如何沈迷老虎機,兒女們是如何商討對策等具體細節,全部略而不提。 《怒海驚魂》中的主要情節是,黃元波當了船上難民的總代表後,儘量爲難民們謀利益,公平分配有限的糧食,協調難民之間的矛盾,爭取與聯合國難民委員會聯繫、協商難民安置問題以及難民們在船上、平芝島上的種種曆險故事。以此線索爲主幹,引出一系列的人物,通過這些人物與元波的關係,漸漸的構築了情節的框架。由船上生活中産生的矛盾到難民們心中抱怨這種逃難日子,都希望早日到達彼岸,核心問題是圍繞難民的 求生、鬥爭、安置。這些環節爲多樣的矛盾衝突支撐起較大的情感空間。 長篇小說情節上升到高潮,的確能讓讀者手不釋卷。《怒海驚魂》中的高潮部分全部依託情節發展的一個新契機:黃元波獲悉新來的船長要將全船難民棄置荒島,與得力助手密謀在下船上岸時來一招回馬槍,反抗船長的殘忍對待。後來輪船抛錨了,便開始了在荒島的生活歷程。一直到印尼軍艦來接收爲止。故事情節性很強,足以吸引讀者的思緒,一接觸便難以再放下。 微篇小說《戒賭輔導》的高潮卻是兒女將妮娜送去戒賭輔導中心後老太婆的真情告白:自老伴死後我孤寂苦悶,他們從不關心我死活;推敲計算如何早日承繼我名下近千萬的財産。我每天去賭場花費一百元打老虎機,志在消磨無聊餘生,縱然天天輸完,一年不過三四萬。我還能玩多久還能輸多少?他們怕我把千萬家財押注,我那些九成是物業。先生們,打老虎機是我如今唯一的安慰,那班畜生,居然連最後這點娛樂也要我抛棄,不過份嗎? [2] (P50) 小說到這裏,已將各種矛盾有效地激化了,讓妮娜吼出了心中怒氣,也引出了前文提示出來的兒女對自己的突然過分關心的真正原因。在反映生活真實側面的基礎上,讓讀者眼前一亮,頃刻明白了前面的不少鋪路文字以及要反映的人性主題,這樣步步爲營地吸引讀者,確實讓人愛不釋手、欲罷不能。 黃玉液的小說結構有一個特點,就是高潮與結局聯繫很緊密,往往給人一種剛揭示出小說的主題就面臨收筆。這在微篇小說中尤爲明顯。微篇小說的結尾,是整篇文章的關鍵,是影響全篇的關鍵所系。在《戒賭輔導》的結尾,妮娜說: 要輔導的,是這班son of bitch,不是我。 妮娜!你沒錯,打老虎機對你來說確實是娛樂。你繼續享受好了。社工微笑著說。 老太婆笑吟吟的出來指著兒女講:要輔導的是你們,不是我,一齊進去啊! [2](P50) 由矛盾高潮到小說的結局,往往能三言兩語就能提要鈎玄。 省略號在篇末的出現,更能讓讀者感覺意猶未盡,讀出省略號裏潛在的豐富意蘊。如微篇小說《英雪姑娘》,,主角我在德國小城因一次偶然的機會邂逅了一位麗人,名叫英雪。全文幾乎都籠罩在兩人的交往中,讓讀者爲他們的美好幸福而默默祝福,誰知道結尾處卻是: 我依戀的望著她,像怕她突然隱沒般,忘卻己年逾知命,忘了離婚後對異性的咒誓,難分難舍的握別時,英雪的話如利劍穿過我心臟:伯伯,明天我就搬去漢堡市姐姐處,謝謝您陪了我幾小時。她說完開門送我。 英雪!你剛才叫我什麽?我手足冷冷。 我稱您伯伯啊!家父的年齡和您接近。 返教堂祈禱,我望著聖母,想念著英雪 [3] (P54) 這樣的結局讓讀者的接受心理有很大的反差,通過前文初步感覺到作者的創作目的是由何而發,到收筆前的一刻,筆鋒一轉,意外的情景,既讓人惋惜,又回味無窮。 當然,有些作品也順著故事情節的發展而採取自然結束的方式。這在長篇小說《怒》中尤其明顯,難民們都被救上印尼軍艦後,小說就奏響了閉幕的樂章: 一聲雄壯而響亮振奮人心的汽笛劃破空宇,千多雙手掌立刻瘋狂的鼓拍,七千噸級的巨艦排水前進,歡呼聲摻雜了許多喜極而泣的淚水,大家再次互相擁抱、握手。此去的一天行程再無風險,大難不死,重生的慶倖漲飽了大家的心房。 婉冰抱起阿文,元波接過明明,左手盈握阿美,一家人歡笑著加入領晚餐的隊伍裏 [4] (P263) 這樣的結尾,令人掩卷沈思,心靈也受到淨化,産生對未來的希冀、對幸福的憧憬。
四 交融的語言 語言是文學的第一要素,一切文學作品都要求語言的上達,小說的語言更追求鮮明生動、栩栩如生。 (一) 口語與書面語相結合 書面語言固然精確凝練,但是也不夠自然、生動、活潑,適當採用一些富有生活氣息的口語,容易讓讀者産生與作者同樣的共鳴,讓小說反映的特定人物親切動人、躍然紙上。適當的口語是敍述與表達的重要輔助元素。 《賈歪教授》中的教授被問話時,理直氣壯地回答:我沒冒認啊!中文名片清楚說明我是假教授,大家都叫我假教授,不行嗎? [3] (P64)充滿生氣與個性的形象語言浮現在紙上,讓人更容易感受人物形象。又如微篇小說《會長》的開頭:老沙原名是沙陳有,曾經因爲諧音被誤會爲沙塵友,意爲驕傲不可一世之人,無妄之災被打,鼻腫臉青傷勢不輕時,行兇者才狠狠抛下:睇不過你條沙塵友,抵打![3] (P23) 敍述的語言也適當的使用口語化,與對白相得益彰,頓時,小說就變得形象生動,栩栩如生。 《怒》中出現很多口語,因爲該故事情節主要依靠人物間的對話來實現,結合書面語描繪,盡現小說所反映的逃亡故事的各個平面。 如介紹海盜張出場: 我姓張,張飛是我的老祖宗。有東西派還囉嗦什麽鬼?誰有問題等下來找我。[4] (P17)先聲奪人,極富個性,形象生動。 (二)詩化的語言 作者精于短句描述,採用詩化語言,兼以較熟練的文言文作爲依託。這些儒雅的書面語和駁雜的多種方言錯綜行文,形成了大俗大雅的文體風格。 詩化,是將創作主體的感受轉化成語言形式的創造,可以給人近乎直觀的美感。詩化語言,更能提高作品的藝術境界。微篇小說的語言力求直觀、簡潔,人物的話語不必全寫,表現的事件不必盡寫,在閱讀過程中,從那些字句中想象出人物形象的神采,從而領悟出比言語更加多的意外之象、象外之境,宛如空筐式結構論中的二度創作[2](P37),更能打動讀者的心弦。 如《笑容》中盈耳皆是閩南對白[3] (P21)也不管廣東侄媳能明否?[3] (P22)。又如《傷逝》短句也很明顯,文言文等詩化語言琅琅上口、甚是美妙:自古天妒紅顔,弱不禁風的當世才女傷寒感染後,竟魂歸天國。[3] (P27) 古人精明,至理之言,必有其因。[3] (P27) 長篇《怒海驚魂》則主要從風景描繪、人物刻畫上體現口語化的對白。晴空無雲,水天一色青藍,水平線浮現出的山色灰淡朦朧;一輪紅日經過整天照耀,已收斂了灼熱,紅著個圓臉滾進山背後。 [4] (P49)詩化的語言中,不乏充滿五光十色的詞語,讓海中夕陽在讀者心中産生美麗的情思,慌若身臨其境。面對茫茫大海,極目遠眺,粼粼波光,浪花輕揚,激起萬千個白皓皓的水泡[4] (P124) 蘇珊·朗格就曾說:當人們稱詩爲藝術時,很明顯是要把詩的語言同普通的會話語言區別開來。通過這種嘗試,人們就會愈來愈深入到語義學、心理學和美學組成的網路之中。[5] (P203) 因此,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描繪女性時,總能以一種充滿美感的詩化詞語,用來勾勒女性的線條,短短的幾筆,就足以將一位麗人展現眼前,並能讓讀者對主角的性格、心理特點等有初步的瞭解,達到中國詩與中國畫裏傳神寫照的藝術效果。 酌量採用一點言簡意賅的文言文表達法,也能夠使行文富有節奏感,琅琅上口,平填幾分語言修辭的韻味。 (三)維繫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柢,並以聖賢之句、民間俗語作調劑 黃玉液是久別中華大地的華人,儘管如此,作者通過各種途徑瞭解、學習中國文化的精髓,心中自然産生了對中國幾千年優秀傳統文化的追求。在小說創作上,吸收中國傳統文化是很自然的事,在其作品中不難發現有古代聖賢之句,民間明哲之言,維繫中國文化傳統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如《空門內外》中邪師說法如恒河沙,《丟臉的人》中上得山多終遇虎,《夜來幽夢》中鐵公雞,《傷逝》中小登科、大登科,《怒海驚魂》裏符伯所言吉人天相,等等。 (四)以普通話(京味)作爲基調,巧合地穿插其他語言(粵語、越南語、閩南語等),體現當下環境色彩。 《怒》中的衆多對白,運用多種方言的地方不少。當然,這需要作者費心思來取捨、穿插,對體現當下人物的個性顯得非常重要。原汁原味的話語腔調,能將人物驟然浮現於書卷上,其中也有一些大膽粗俗的方言俚語。粵語如: 輪船上的吵架聲:惡人我見得多啦!未見過似你口甘,哼!殺人都夠膽講出口。[4] (P10) 又如我唔信,冇口甘大只蛤乸隨街跳,話唔定同埋我地一支水。(注:廣東俗語意爲沒那麽便宜事,後句是說不定和我們同樣。)[4] (P13) 通過簡單的而極富個性的人物語言,就已拉近了讀者與作品的距離,吸引讀者的興趣,牽引讀者的思維,而且令人難以忘懷。 作品中的語言味道,讓人感到在作者的交際圈中存在熟悉的北京人的語腔和語調。作者所從事的職業是涉及大衆傳播的領域,這種得天獨厚的多方位視角環境所積攢起來的優勢,讓作者大大地增加了見聞,優於其他同類爬格子的人。 上述作品的讀者範圍主要包括祖國大陸、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澳洲,甚至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華人圈子,普通話是大部分讀者的母語(中國大陸),穿插方言更是源于作者的生活背景(如澳洲華人圈)及受到東南亞地區的影響。 如《笑容》裏面因爲閩南話而造成的誤會,將幼秀誤認成夭壽,《會長》中主角的名字沙陳有因粵語諧音的關係被認爲是沙塵友,而遭到毒打。 作品所呈現出來的語彙中,通過主人公原型的個性豐彩、生活經歷的不同、所接受的文化藝術修養的差異,注入澳洲華人的思維方式與生存狀態的思索,從而自成一格。 閱讀黃玉液的小說,很容易讓讀者感受到,這種語言風格既真切生動,又新穎別致,可謂手雖釋杯,唇齒留香。 (五)宗教語言 作者出於藝術取材的考慮,對涉及宗教的故事題材,適當地根據角色的需求,或場合的需要,加入宗教語言,能讓人感到小說真實可靠的生活背景,而且能增加多角度多層面的觀賞性。 幾個微篇小說很能說明這一點。《空門內外》阿彌陀佛、施主、功德等佛家的語言,更能體現出家人的度身性格。小說中半鹹半淡的佛家與俗家相結合的語言,三位元和尚對著女色、酒肉等皆顯出與六根清靜相背離的態度,可謂酒色財氣樣樣齊的禿驢,更能體現這幫假和尚的各色面具。讀者感覺新鮮,易於把握文字,融入小說所述的環境中,讀後印象非常深刻。《第六戒》,是涉及天主教的,寫的是主角王神父與一位教友木太太從無到有的感情糾葛。敍述的語言中也運用天主教的詞語與感情色彩。如是她告罪時細碎的聲音、主日彌撒的告解均由他負責,木太太,你回去念三十次天主經,心中不可再生妄想,主要赦免你,阿門。 [23 (P96)。又如《告解》中: 神父!我叫馬嘉烈,虔誠向天主告解,祈主赦免所犯之罪。 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門!馬嘉烈,你犯何罪?[3](P130) 對白的語言更容易體現其中的宗教特色,一定程度上能呈現當時具體對話環境的氛圍,增加可信性與感染力。
五 提升的空間 作家的幻想世界不僅是建立在敍述行爲之上的,而且還需要這一行爲與現實生活保持一段距離,若即若離,而這一要求使得敍述行爲逐漸擴展成爲一門運用言詞的特殊技巧。[5](P220) 黃玉液的微篇小說集中於家庭與社會。而且作者以自己的經歷爲小說題材的支撐點,如在南越的悲傷、亡命海上的艱險、澳洲駁雜斑斕的生活 這些題材都是很吊人胃口的,能讓人感到耳目一新,能讓讀者更多地瞭解越南與那個時代的歷史。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藝術創作過程中,配以自己的主觀情感,所反映的社會現實問題則是需要讀者加以明辨的。如關於涉及越南題材的描寫,個人的憎恨,反映在作者對當年的越南執政黨(越共)的態度上,如《怒海驚魂》中的對越共的敍述,微篇小說《丁夫造橋》中的對越南的政府機構問題的描寫。 關於澳洲華人生活圈子的描寫,是作者創作題材的一個重要方面。從作者的角度來反映當下社會生活中的醜惡與弊端,通過詼諧的言語揭示問題的真相。 好的敍事文本講究的是情節的引人入勝、環環相扣,甚至離奇曲折。只有情節的出人意料才使故事充滿生命力和未可預測的魅力。[5](P223) 好的歷史或現實的題材,如《怒海驚魂》,的確能讓作品在讀者心中繞梁三日,作者控制篇章的篇幅十分有效。作者在多數作品裏力求以小見大,孕育深刻的思想立意。但也部分地存在著題材重復、內容單一、層次不深的迹象。許多雷同的描寫文字只是稍加改變一下描寫場景,就將一些中國古典文學中慣常用來描寫女性的辭藻移用到不同作品的主角身上,獨創意識似嫌欠缺一些。譬如有關女性描寫方面的語句,長袖善舞就多次出現在《傷逝》的第一自然段,《諾言》的第四自然段,《丁夫造橋》的第一自然段的第1句。 描寫女性體態、豔麗方面的辭彙,更有: 婀娜:婀娜嬌豔[3](P29),婀娜淩波 [3](P53),婀娜風騷[3](P28),婀娜玲瓏 [3](P70),婀娜豐滿[3](P83),輕盈婀娜[3](P92),婀娜生姿[3](P112),婀娜的背影 [3](P122),婀娜的女人 [3](P123),婀婀娜娜 [3](P155) 。 玲瓏:體態玲瓏[3](P35),玲瓏浮凸[3](P43),婀娜玲瓏 [3](P74),窈窕玲瓏 [3](P94),豐滿玲瓏[3](P97),玲瓏浮凸 [3](P120),玲瓏浮凸 [3](P122)。 豔 字:冷豔 [3](P27),冷妝藏豔色 [3](P92),嬌豔如彩虹[3](P96),嬌豔可人[3](P111),鮮豔的容顔 [3](P138)。 以如許辭彙不斷地描繪衆多的女性,就顯得單一、重復了。也讓作品粘上了過多的陰柔脂粉氣,小說變得似乎是畫像評論而非文字文學。反映女性的體態描寫,都採用由上而下的視角,根據作者對女主角善良或醜惡的評判,通過下筆對女性的描寫語句體現出來。 作者看重懸念藝術,但敍述表現手法較爲狹窄。應多嘗試其他方法,以使表現手段更豐富、深入。比如反諷手法在小說中痕迹較少,比較好的要數《假歪教授》。但是若能多加運用,表現效果將會更顯著。 在長篇小說《怒》中更能體現這種敍事手法的不足,雖然景色描寫的效果如詩如畫,比喻、插敍等手法的運用也能恰到好處,融入全篇,上下連貫,但是小說中各色人物形象的樹立幾乎都以彼此的對白爲主,敍述的筆調雖然能表現情感不一,但人物塑造的手法略顯單一。 作者的反差藝術手法,運用熟巧,可謂匠心獨具。小說的前文與結局表現了不同程度的落差,對情感藝術表現也蠻好,産生不錯的效果。這在微篇小說中表現得比較充分。如《戒賭輔導》、《英雪姑娘》、《傷逝》、《芙蓉》、《白頭偕老》、《緣分》 但對空筐式結構,雖有運用,程度不深,似有待提高。 總之,黃玉液的部分小說作品裏,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題材重復的現象。人物形象塑造中穿插了較多的作者觀念。對部分言情題材的藝術處理,思維形成定勢,不容易開掘出新的波瀾。
從黃玉液的長篇小說《怒海驚魂》、微篇小說集《溫柔的春風》中剖析澳洲華文小說的一個發展層面,可以體現澳華小說發展的某些趨向。從世界範圍來看,澳華小說創作已經成爲澳洲文學森林中的一座別致的花園。而且出現了將一個個湖塘、一條條溪流彙成浩蕩江河的端倪。古諺雲: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澳華文學薪傳華文文化的情結實屬難能可貴。但發揚、推廣華文文學的艱巨使命則十分不易。海外華文作家的文學創作,更多顧及的是延續民族文化而不像大中國範圍內的作家或執著於求新求異、與衆不同,或爲了關注於市場銷路的得失。
注 釋: [1] 錢超英.詩人之死一個時代的隱喻[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該書專門論述了從大陸到澳洲留學的留學生文學,資料詳實,但對從其他海外諸國曲折赴澳洲的非留學途徑的華人移民們的文學,則未涉及。 [2] 筆者對他的微篇小說集《養螞蟻的女人》的論述參見:姚朝文. 華文微篇小說學原理與創作[M]. 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 2002,216-224. [3] 心水. 溫柔的春風[C]. 墨爾本:豐彩公司, 2000. [4] 心水. 怒海驚魂[M]. 洛杉機: 新大陸詩刊社, 1994,封三. [5] 童慶炳 程正民. 文藝心理學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268. (作者簡介:姚朝文,男,中國廣東佛山大學文學藝術學院副教授,中華學研究所副所長,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究會理事)
On the Culture Meanings of Australian-Chinese Literature from Xinshuis works YAO Chao-wen(Chinese Department,Foshan University Foshan 528000,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trying to research the area of the Chinese short short stories and novels in Australia from Australian-Chinese writer Huang Yuye(Xinshui)s works. According to the writers early life in Vietnam and present life in Australia,the writer blends the exotic culture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o creat works. Because the writer has been abroad for many years and is lack of Chinese Cultural edification, it seems unitary on subject and language expressing. It figures out the tendency of Australian-Chinese novels development from these. Although it becomes a corner of forest and has unlimited potentiality of development, its a long way to take on a great sight. Also,this paper makes up some defects in Xinshuis works and tries to probe into the feeble parts of Australian-Chinese novels elemetarily. Keywords: Chinese in Australia;short short story;novel ;Chinese cul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