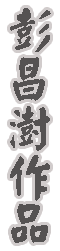|
|
|||
|
日 記
我的妻子蕪菁有寫日記的習慣,十多年未見其變。但其日記的內容,我從來不見其詳。結婚之前,每當我想看她日記時,她總是以嬌嗔阻攔,我也不能強她所難,只得退避三舍。婚後她對日記也是三緘其口諱莫如深,總是對我說,都是夫妻應當相互信任,要給她的心裡留點自言自語的空間,我也只得知難而退。日記放在她的梳妝盒裡,一把小巧的鎖將她所謂的自由空間封固住。
可是近一年以來,我與妻子的關係變得越來越淡漠而微妙,她寫在日記裡的內容也愈見其少。究其原因,是我與一個叫明麗的姑娘發生了不正當的關係,明麗是我們公司的財務,是我招進來的,我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當然也是最大的股東,公司的另一個股東是蕪菁的父親,我的岳父,一個癱瘓在床風燭殘年頻頻向人世揮手的老人。當年我的岳父一定要把自己加入股東名錄,我想也是基於對我的不放心,但在蕪菁的堅持下,岳父作為實際的出資人也僅是占了一小部分股份。這幾年,在我的努力之下,公司運營步入正軌,業務蒸蒸日上,而岳父的身體卻每況愈下,加上我與蕪菁的女兒也慢慢長大,岳父覺得對我這個家庭的監管也該結束了。
明麗是個妖嬈的姑娘,年青多彩多姿,尤其愛撒嬌,嬌撒得自然而流暢,顯不出一絲的矯揉造作,讓男人特別中老年男人渾身酥軟調動起憐香惜玉兒女情長的情懷。明麗到了公司六個月之內,我與她還相安無事,因為我一直是本能地在抵禦,抵禦香艷情色對我良知的侵蝕,我也一直在猶豫與彷徨,但最後我放棄了無畏的抵抗走進她發出濃香的閨房。我本以為明麗只是少不更事逢場作戲玩玩刺激然後在青春記憶裡留下些韻事,但沒有想到她居然義正詞嚴地向我提出了名份的要求。有時我想風流情事都是些濫俗的事情,既然濫俗就要付出代價,我怎麼能獨善吾身呢?
我本以為我與明麗的事情蕪菁是一無所知的,在公司我想也不會有人知道這事情,但不曾想蕪菁是知道了,而且確乎知道了,她甚至還帶著女兒回了趟老家,不幾日,我的父親便從鄉下趕到城裡,父親暴跳如雷手執雞毛撣子打得我狼狽不堪,那時我用怨忿的眼神看著蕪菁,我的眼神大概起了些作用,芫菁有些羞愧不安起來。
我走近蕪菁的日記也就是近一個月的事情。那天女兒生病腹泄,蕪菁手忙腳亂抱起女兒就走,那串鑰匙落在書桌上,我手忙腳亂地打開梳妝台,取出那本日記,我的心跳得厲害,原來窺私與偷情都是那麼的心虛啊。
2010年4月8日,星期四,多雲。這個氣清風爽夜,我的心破碎了。我的丈夫,那個曾說會把心放在我與孩子身上的男人竟然與一個姑娘手拉手走進餐館,我在梧桐樹下掩面嗚咽,他們步態輕盈,離我咫尺之遙。我的心急速下墜,浸在北冰洋徹骨的水中。
2010年5月8日 星期六,晴。我帶著女兒乘車去老家,他的老家,女兒上了車就歡欣鼓舞,我在車上陷入混沌而迷濛的狀態,我甚至不知道為什麼要去老家,自己的事情自己解決不了,還要去麻煩他父親,一個步履蹣跚的老人,是不是太殘忍?但是我又有什麼辦法呢?那個一意孤行決絕的男人又怎麼能想得到往日的甜言蜜意與歡愉恩情呢?
2010年7月6日 星期一多雲。今天是女兒的生日,我與女兒坐在桌邊等他回來,但到了八點他也沒有回來,自周五起他就沒有回來過,打電話是秘書台。蠟燭已經燃上,照在女兒稚嫩的臉上,我忍辱負重的結果卻換不回女兒一個團圓的生日,我的淚水一再洶湧如往事。我要殺了他,我要這個負心人去死,我要給下藥,我要把他吃的藥換成天下最毒的藥,我要他去死,我的尊嚴,我的快樂,我的家庭,我的女兒……為什麼,為什麼?
八月初的一天,我對蕪菁說我要去出差,她默默幫我整理好行李,臨別時,我鄭重其事地對她說,我過幾天就回來,到時我們一起帶女兒去看望岳父,她的目光閃爍而游離。
黃昏時,我坐在四川一個小鎮的小酒店裡,一壺苞谷酒,一盤辣子雞,一個負心人。窗外的雨時而淅瀝,時而急驟。我掙扎於酒精的麻醉與對過去的告白中時,蕪菁打來電話,語氣急促地問我吃藥了沒有,我說沒有,她舒了一口氣說吃了也沒有關係,都是VC片,而這時,山巒崩摧,濁流排空,瞬間我就被壓在小酒店的斷垣之下,我想對蕪菁說,我已經與明麗分手了,我想回家。可是水流很快淹沒了我的呼吸。
2010.11.5 寄自上海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