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風冷雨
夜讀余光中的鄉愁
余光中教授出生於1928年重陽節,那年剛巧是龍年,所以他稱自己是龍的傳人。他在成長中,經歷了兩場戰爭;一場是抗日戰爭,一場是中國內戰。所以他童年的天空,只看見轟炸機戰鬥機,聽到的是槍聲和砲聲;沒有喜悅的音樂,沒有彩色的風箏!
他背負的鄉愁,不是我們這一代能感受到。他所說的鄉愁像一個鐘擺,在過去和未來之間擺動。一面在陽光中,一面在黑暗裡。一只眼睛,倒映著一座塔;一只眼睛,倒映著101摩天大廈。
他立著,是一匹狼;他飛著,是一頭鷹。他那種根植故土的情操,可以化萬里長城是哭牆,可以化千頃洞庭是淚壺。所以他說大陸是母親,臺灣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歐洲是外遇,無論漂泊到那裡,心仍然緊緊縈繞在那片厚土。「他那一代的中國人,吞吐的是大陸性龐龐沛沛的氣候,足印過處,是霜是雪,上面是昊昊的青天燦燦的白日,下面是整張的海棠葉」。在他的記憶裡,「不記得一生揮過多少柄蒲扇,撲過多少只流螢,拍死過多少只蚊子;不記得長長的夏日鯨飲過多少杯凉茶、酸梅湯、綠豆湯、杏仁冰?只記得絕不是冷氣和可口可樂」。余光中教授對自己的國家、民族,是一種強烈的、雄渾的、深沉的、冷澈的宣洩和感受。這種感受和宣洩,就是鄉愁。他像是一片寂寞的孤雲,走在大陸、臺灣、香港、歐洲之間。
夜深了,家人早已入睡。在凄風冷雨中,我走到後院杜鵑花棚下,高聲朗誦「當我死時」這首詩歌。這首詩歌是余光中教授早年流浪美國密西根時寫的,現在以這首詩來拜祭敬愛的余光中教授。
當我死時
當我死時,葬我,在長江與黃河
之間,枕我的頭顱,白髮蓋著黑土
在中國,最美最母親的國度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張大陸
聽兩側,安魂曲起自長江,黃河
兩管永生的音樂,滔滔,朝東
這是最縱容最寬闊的床
讓一顆心滿足地睡去,滿足地想
從前,一個中國的青年曾經
在冰凍的密西根向西瞭望
想望透黑夜看中國的黎明
用十七年未饜中國的眼睛
饕餮地圖,從西湖到太湖
到多鷓鴣的重慶,代替回鄉
1966.2.24於卡拉馬如
『敲打樂』詩集(台北藍星詩社1969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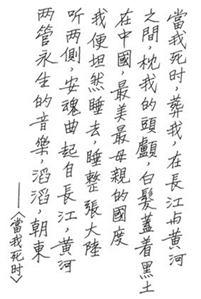
這是一首懷念國土的詩,也是一首鄉愁的詩,作者使用的地理意象是十分恰當的。自「長江」到「黃河」,到「西湖」,到「太湖」再到「重慶」,全詩充滿對中國泥土的戀棧。余光中教授在詩中並沒有要求死後葬在中國一個特定的地方,只想回到長江與黃河兩大河流之間的任何一處地方就滿足自己的心願。
現在,鄉愁已是一方矮矮的墳墓了,在飄零的風雨中,在飄零的蒼茫中,漸行漸遠的屹立著。讀您余光中教授!想您余光中教授!哭您余光中教授!永遠愛您!銘記在心!
2017.12.1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