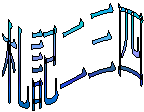|
|
|
我曾經寫過一首小詩:
在廣闊的世界上 我流浪,是因為我有著夢想 我羨慕那些一生都 生活在故鄉土地上的 人。一滴水就報一滴水的恩 平凡中,不用負擔太多 星空萬里下,我這樣說出故鄉 其實我多麼奢侈 其實記憶就在心中 像一盞燈,一輩子都是故鄉
然而那時,我一直理解不了故鄉對於一個人來說,到底意味著一些什麼?直到有一次我在英國著名作家毛姆——威廉•薩默塞特•毛姆的小說《月亮和六便士》中讀到了這樣一段話,大意是:有一些人,在出生的地方他們好像是過客,孩提時代就非常熟悉的濃蔭郁郁的小巷,同伙伴們遊戲其中的人煙稠密的街衢,對他們來說都不過是旅途中的一個驛站。這種人在自己的親友中落落寡歡,在他們惟一熟悉的環境裡也始終是獨處。也許正是這種在本鄉本土的“陌生感”才迫使他們遠遊異域,去尋找一所永遠的居處。說不定在他們內心深處,仍然隱伏著多少世代以前祖先們的習性和癖好,它們使這些漫遊者重新回到了祖先們在遠古就已離開的土地之上。有時候當他們偶然到達了某個地方,他們會神秘的感到,這裡正是自己夢寐以求的棲身之所,是他們一直 在苦苦尋找的精神的家園和心靈的故鄉,只有在這裡,他們的心才能夠安靜下來…… 是啊,無論歲月怎樣流逝,無論時代怎樣改變,人的情結,人的根,以及從故鄉那裡接承下來的文化等等,都將有一些是永久的,也無論你走到哪裡,流落何方,你都會憑著心靈中最敏感的那部分觸角而把自己的故鄉所特有的東西一一分辨出來:故鄉 的氣息,故鄉的色澤,故鄉的天空下炎涼的土地…… 所以,鄉愁對於一個遊子來說,就像一切人類的基本感情一 樣,是與生俱來的。 我願守著自己的那份獨特的情感,根性和夢想,守著自己心 靈的故鄉,惟如此我的詩篇才具有了人的知性。
二
千禧年之夜,我去一位朋友那兒,朋友病了,剛輸完液,使我驚訝的是她沒有別的想法,而是手捧一部毛姆的名著《刀鋒》,斜靠在床頭品讀和感受著由《刀鋒》所迸發出來的生命鋒韌。那 一刻我心有所動,我說:我會記住今夜的,記住《刀鋒》。 後來我忽然就記起來一句話,就是: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 無雲萬里天。但這樣的心境,我在以前是很難做到的。 我的老家在貴州遵義,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遵義會議”的那個遵義。我家離遵義會議會址有兩站地的路。小時候,常常步行於子尹路(即遵義會議會址門前的那條路),並沒有去感覺路 的兩旁那些木樓瓦房所帶著的明清遺韻,歷史的沉積。這或許正是中國人具有的通病:熟悉的地方沒有風景。 後來遠離遵義了,遠離子尹路了,一個人在北方生活,居無定所,才常常在靜靜的夜晚突然就想念起那些熟悉的一磚一瓦來,以及那些熟悉的一磚一瓦裡所蘊藏著的悠遠的故事,可到底蘊藏著一些什麼樣悠遠的故事呢?這時,應該說,更是一種深切 的嚮往了。 然而如今,那些帶有明清遺韻的建築統統被當作破爛危房一拆而盡了,這對於那些嚮往到遵義去瞻仰紅樓的人來說,無疑是 一種損失,於我卻是一種痛,心痛。 我原先的遵義,古古樸樸的遵義,沒有了。剩下的只是我的記憶。
三
我的童年是在幸福巷度過的。 幸福巷是一條小巷,背向街面,說是“幸福”,有些誇張了,即便陽光燦爛的好天,人在巷裡走,也並不感覺出幸福的味來,倒是那古樸的石板路給人一種江南小鎮的遐想,或許也有一位丁香一樣的姑娘,撐一把油紙傘,結著丁香一樣的愁怨在巷的另一盡頭,然而這頂多是一種美一種願望。幸福巷依舊是幸福巷。它名字的由來或許緣於巷的另一側有一座青樓,那便是毛澤東與張 聞天在遵義時的舊居了。 那時我家在小巷的一座四合院裡。院裡有好幾戶人家。孩子們也多,一吵一鬧間,總能鬧出很多童年玩的花樣。我們也常去 毛澤東舊居。但僅幾歲的我們是不太清楚毛澤東什麼的,只知道青樓的外面有一面青灰牆,老高老高的,就總趨使我們的好奇心。當然也有門。當然那會是不收門票的,何況我們又是近鄰的孩子,所以工作人員頂多只囑一句:上樓別亂跑,別亂摸。我們也聽話,就跟隨有來參觀的稀稀拉拉的三兩人一起,上樓挨窗挨門的走、看。屋裡光線挺暗,無非陳列著紅軍時期的一些馬燈、梭標、駁殼槍及文件一類什麼的。對於我們一幫小孩來說,這些物什絕然沒有什麼意義,也就匆匆走一遍覽一下了事。 九幾年的時候,我還去過一次幸福巷,下巷倒還保持著幽靜,上巷,也就是毛澤東舊居那一片已熱鬧的不行,青灰牆的外面成 了集市,我不禁忽生一片哀傷,也許我多愁善感罷。 那時,我的母親在一家什麼街道小廠做臨工。我母親是64年“四清”的時候被打倒下去的,直到79年才平反恢復工作。所以我們還肩負起了每天做家務的擔子。記得有一次,我們把米飯做糊了,母親回來後將我們一頓好揍。現在的孩子是絕然體會不到那種生活的了。然而我們也有把米飯做好的時候,做好的時候呢,我們就靜靜地坐在我們大院的院門口,一任夕陽從巷的另一側消 逝飄逸而去,靜靜地等候著我們的母親。 我知道,這種純淨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
2006年11月20日寄自貴州
|
|